Super User
本书的必要
罗思修博士(休·诺尔曼·罗斯Dr. Hugh Norman Ross)生于1945年,是一名加拿大籍天文学家。他的名声来自他所创办的据称是基督徒护教学的传道机构,“信仰的理由”(Reasons to Believe, RTB),总部设立在美国加州。该事工宣称其目的是为基督徒提供支持圣经的科学根据,并且回答怀疑者提出的反对基督教的论点。此事工负责安排他的繁忙的讲座日程,并且出版一个刊物,称为《事实与信仰》(Facts and Faith)。罗思修写了几本面向大众的,有关圣经、科学和护教学的书(其简化书名见第28页的“罗思修的书”列表)。
当然,基督徒应该支持罗思修所宣示的目标,就是让圣经和科学协调一致,不是吗?尤其是面对许多政治宣传,说科学与基督教是彼此对立的。罗思修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决反对者,并且宣称有不可否认的科学证据支持有创造者。另外,罗思修宣称他相信《创世记》是真实的历史,不是神话或隐喻,而且圣经是无误的神的话语。因此毫不奇怪,许多基督教领袖对他的思想给予高度肯定,而且导航会出版社(NavPress)也出版了他写的书。
可悲的是,有些人为罗思修的书写了肯定的评语,却没有透彻地阅读过这些作品,而是作为给朋友的恩惠。这岂止是不幸!这是不负责任地使用在基督徒公众中的名声和影响。有些著名的基督徒领袖,出于对编者和罗思修的牧师的友情,推荐了他写的书《创造与时间》(Creation and Time),却没有真正看过其内容。所以他们在创造方面的立场不一定与罗思修的书一致。其中一位在1998年一月之前撤回了他的支持。
罗思修也成为五旬节派(Pentecostal)的旗帜刊物《灵恩》(Charisma)2003年七月号的封面人物,该报导的作者是《灵恩》的资深撰稿人、新闻部主任薄安笛(安迪·布彻尔Andy Butcher)。1
然而,当我们认真研究罗思修的宣称,就发现很多时候他不让圣经自己说话,而是重新解释经文,以适应世俗的“科学”。所以,虽然罗思修声称他是“反对进化论”的,意思是说他不承认一类被造物可以变成另一类,但是对进化“科学”的其它部分他几乎全部接受,即使与《创世记》的清楚教导不一致的地方他也接受。虽然罗思修宣称他相信《创世记》是真实的历史,但他所理解的历史与经文的字面意义却相去甚远。他的观点常被称为“渐进创造论”(Progressive Creation)。在下页的表中,我将这种观点与国际创造事工(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CMI)的观点相对比;我们相信我们(CMI)的观点是基于对圣经的审慎解读,而且我们的解经学是前后一致的。罗斯更喜欢称自己为“长日创造论者”(Day-Age Creationist),清楚地反映在表中的第二行。我们在引论的附录中会评论罗思修自己是如何理解他与我们的区别的。
已经有人写过对罗思修著作的回应,如范碧波(马克·凡·比伯Mark Van Bebber)和邰乐宝(保罗·泰勒Paul S. Taylor)合著的对《创造与时间》一书的逐点回应。这是一部上乘之作,2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罗思修从来没有回应他们提出的主要论点,而且继续重复同样的错误。“信仰的理由”所能做的只是发表一位政治学家所写的无力的书评,基本上是攻击作者,而不是批评书中的内容。3
罗思修的有些书得到了公开的评论,4但是这些评论对罗思修的教导似乎没有起到任何影响,也就是说,他继续重复同样的错误。因此有必要写一本全面的书,以显明下页表中左边的立场与圣经根本不可调和,而且也没有真正的科学依据。
罗思修过分伸展了他的专长领域
虽然罗思修辩论的热情值得赞赏,但不幸的是,有时他发表的意见超出了他的专长领域。这对那些假定罗思修在一切他说话的领域都是专家的基督徒是无益的。
比如在与年轻地球论争辩的时候,罗思修博士有时要提到希伯来文语言的细节。但是这多次为他带来麻烦。他试图贬低一个圣经创造论者常常持有的观点,就是《约伯记40:15》起始记载的“比西莫特”(behemoth,和合本圣经解释性地翻译为“河马”)是一种蜥脚类恐龙(sauropod),因为他相信恐龙在6,500万年之前灭绝了。罗思修在《创世记问题》第一版48页说(在第二版中被纠正):“希伯来文的‘比西莫特’(behemoth)的复数形式‘比西马’(behema)”。然而,就连初学希伯来文的人都知道“-a”是一种常见的阴性单数,而“-ot”是阴性复数。
|
渐进创造论 |
圣经创造论 |
|
地球和宇宙的年龄都是数十亿年之久。 |
地球和宇宙的年龄都是约6,000年左右。 |
|
创世的“日”都是极长的时期。 |
创世的“日”都是正常的日/天。 |
|
太阳和星星都是在地球之前被造的,仅仅在第四“日”对一个假设存 在的地面观察者“出现”。 |
太阳和星星都是在第四日被造的,是在地球被造(第一日)之后。 |
|
第七“日”仍然在继续,据说这有“事实”支持,就是在最近的10000年里没有新物种出现。 |
第七日的长度也是24小时。有些群体之间出现了生殖隔离(不能交配繁殖),因此按照定义,新物种产生了。 |
|
早在人类存在以前,亿万年来,动物就在彼此相食,因为自然灾害而死亡,因为多种疾病而受苦。 |
起初的创造是“甚好”的,而死亡、苦难、和疾病最终都是亚当犯罪的后果,罪导致神咒诅了他所造之物。 |
|
神分别创造了几乎一切的物种(species)。 |
神创造了相对而言很少的“类”(kinds),而多样“物种”是被造的基因库(gene pool)发生不增加信息的多样化的结果,尤其是在大洪水之后。 |
|
神在60,000-10,000年以前创造了亚当【该范围使得亚当可能早于土人到达澳洲的时间,据“测定”是在40,000年前】。尼安德特人不属于人类,而是没有灵魂的类人猿。 |
神造约6,000年前创造了亚当。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直立人(Homo erectus)都是真正人类的化石,是亚当的后裔,很可能活在巴别塔之后不久。 |
|
化石的次序记载了不同的时期,各个时期存在过极为不同的被造物,是神在不同时期的创造活动的结果。 |
化石的“次序”大多反映了在世界范围的大洪水中和随后的局部灾难中不同的埋葬阶段,也反映了多种不同的生态系统。 |
|
挪亚的洪水局限在两河流域的的河谷内。 |
挪亚的洪水是全球范围的。 |
|
神必须超自然地干预才能造出不同的种族特征,帮助人们从巴别塔分散。 |
亚当和夏娃拥有今天一切不同种族(族群)中的遗传学信息,也可能发生不增加信息的变异。种族特征是因为小的族群在巴别塔之后彼此分离开来。 |
所以,罗思修把语法颠倒了:“比西马” (behema)是单数,而“比西莫特”(behemoth)按照语法是复数。这是一种修辞手法(figure of speech),被称为“强度复数”(intensity plural)或者“尊贵复数”(plural of majesty);“所指的事物是单一个体,但是因为这一名词强烈地代表了它的特征,所以使用复数形式。” 5意思是“野兽中的野兽”。上文下理说明这是神造的最大的野兽。《约伯记》40:17说:“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这显然不符合罗思修建议的河马(除非那“香柏树”是盆景)!
本书的范围
本书集中批评罗思修写的书,而不是他的广播录音以及网站,因为书是他的教导的不可否认的记录,而且可以认定是被反复校对过的。反过来,录音中有较大可能犯一时说话走嘴的失误,而网站的文章可以被经常改变其内涵和网址的。
然而有以下的特例:
- 罗思修博士与贺文德博士(肯特·贺文德Dr. Kent Hovind 6)在2000年十月的安科博秀(约翰·安可伯格秀John Ankerberg Show7)上的那次广为人知的辩论。我在创世网站上(creation.com/ross_hovind)祥细评论了这次事件。其中的一些要点与本书中的多个论点相关。
- 《伊甸园里的生与死:圣经里及科学上的证据支持在堕落前就有动物死亡》(Life and death in Eden: The Biblical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Animal Death before the Fall)是一套2001年的讲课录音带。这被描述为一次“圆桌会议”。参与者是罗思修和“信仰的理由”的同工:神学家桑普乐(肯尼斯·桑普拉斯Kenneth Samples)、生物学家冉法萨(法萨尔·拉纳Fazale Rana)、被称为平信徒护教家的哈梦洁(玛吉·哈尔门Marge Harmon)、还有作为主持人和神学家的彭可丽(克丽丝塔·蚌特拉格Krista Bontrager)。本书第6章指出了其中的错误。
- “RTB(信仰的理由)批评RATE(放射性同位素与地球年龄)计划”。8这是“信仰的理由”的广播节目,时间是2003年九月18日,西岸时间晚6-8点。主持人是彭可丽,录音室参与者包括罗思修、冉法萨和哈梦洁,通过电话参与者有文若哲(罗杰·韦恩斯Roger Wiens)。本书11-12章批判了其中的错误。
大约在本书第一版出版的时候,罗思修写了《日子的问题》(A Matter of Days)。其中没有任何新内容,但是他努力扮演蒙冤者的角色。我在创世网站上批评了这一点(见creation.com/matterofdays)。
我们遵守拉丁文的说法scriptura manent,意思是“成文者立”,隐含的意思包括“除非以同样的书面形式收回,否则可以一直被人批评”。所以,本书让罗思修为他写的书中的错误负责,除非他通过文字收回。如果他说他在某次讲话中口头收回了某个宣称,或者回答了某个要点,进而要求他的辩论对手去花许多时间去听他和助手的对话录音是不合理的。
本书的大纲
本书从圣经的权威这个主题(第一章)开始,原因是年轻地球论者与罗思修及其追随者(包括各式各样的神导进化论者【Theistic Evolutionist】和年老地球创造论者【Old Earth Creationists】)相比,其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权威二字。国际创造事工坚信神的话是无误的,因此圣经必须是我们的终极权威。这意味着必须用圣经来评判人提出来的、可能出错的各种理论,而不是用人的理论来评判圣经。我们认为罗思修把“科学”高抬到与圣经平等的地位,而且在实践中,把科学放在高于圣经的位置,通过重新解释圣经来适应他对科学的理解,然而他声称自己的做法是符合圣经的。所以本书第一章解释为何圣经是权威的,以及为何罗思修的作法是与圣经不一致的。这一章还指出,不信24小时创造日的福音派基督徒实际上承认经文是如此说的,但是不肯相信,因为他们被所谓的“科学”吓倒了,误以为科学所教导的结论与圣经不同。科学当然不应被忽略,但是它应该被放在服事圣经的从属地位,而不是掌管圣经的统治地位。
一旦确认了圣经的基础地位,下一步就是要决定它在所争论的领域有什么教导,然后就可以论证真正的科学如何可以显明或澄清一些圣经教导。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重新解释圣经,得出与圣经明显的含义和传统理解相反的结论。
于是,第二章论及创世周的“日”,指出“日”的长度是24小时。这一章驳斥了一些反对意见,也简要地反驳了其它的两种妥协观点:间隔论(Gap Theory)9和框架假说(Framework Hypothesis)。10我同时也说明了“字义”解经究竟是什么意思,指出罗思修对“字义”这个词的用法很不符合字义!
第三章总结教会历史上绝大多数解经家的压倒性意见,即创世日的长度是24小时。即使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也相信,在他们写作的时侯地球的年龄还不到6,000年。漫长时代的思想首先在“科学界”流行,后来保守派解经家也试图让圣经跟上科学,这才出现了对圣经的长年代解释。自由派人士反而维持着传统的解释,并不是为了捍卫圣经的权威性,而是为了指出圣经的“错误”。
第四章比较短,是为了表明《创世记》里的创造次序与长年代的信仰无法调和。这一章着重论述神在第3、5、6日所创造的各类动植物(包括恐龙),以及第4天所创造的天体。然后我们回应了罗思修对创世周中被造物类别的限制,以及他所提出的创造生物和天体的“次序”。事实上,一位早些时候影响很大的长日论提倡者杨德威(Davis Young)后来放弃了长日论,而采纳一个完全否认《创世记》有任何历史价值的观点,这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第五章应对大爆炸理论,该理论一直是罗思修解经学的基础。这一章分析了大爆炸理论的一些科学难题,指出关于星系、恒星和行星形成的进化理论有很多漏洞。因此,罗思修使用大爆炸和“弦理论”来护教是有问题的,而且不必要。本章提出了可以替代这些理论的另外的护教方式。最后,我们提供了可以替代它们的、合乎圣经的宇宙学模型。
第六章写的是关于罪与死亡的起源。这一章论述圣经的教导,就是罪与死亡是在堕落之后产生的。这里的死亡包括肉体的死,而不仅是“属灵的死”。有些经文明确地局限于人类的死(不涉及动物);但问题仍然存在,因为进化论者为现代人类化石所“鉴定”的年代比罗思修给亚当定的年代早。更何况脊椎动物的死亡也是在堕落之后,因为它们与人类一样,包括在“有灵的活物”(nephesh chayah)的范围之内。这可以从起初的素食看出来,而且动物最终都要恢复素食。圣经教导犯罪导致死亡,这一教导也是任何长年代妥协理论的丧钟。
第七章祥细阐述圣经创造模型,解释“受造类”的概念。本章也揭露了进化论者和罗思修所说的任何变异(variation)或“新种形成”(speciation)都是进化的误导性说法。一个关键的概念是遗传信息(genetic information)——从非生命变成动物再变成人类的进化11需要增加信息,而变异和新种形成只是信息重组(sorting)或信息损失的结果。这也反驳了罗思修所谓的创造论者相信超速进化(super-rapid evolution)的指控。
第八章论证《创世记》中的大洪水是全球性的,并解释为什么这是对经文的唯一正确的理解。本章驳斥了罗思修看似基于圣经的论证,以及他所谓的科学论证。事实上,地质记录如果被解释成近期灾难性过程的结果,这看上去似乎更合理。罗思修相信《创世记》洪水是一次局限于两河流域的地方性洪水,但这显然行不通,因为这不符合《创世记》的描述,况且两河流域的地理也不能维持大洪水的水位达一年之久。这一章还论证了方舟的稳定性,以及在方舟上容纳所有陆栖脊椎动物类别的可行性。罗思修的论点,就是关于在全球性洪水情况下方舟需要容纳的货物,基本上与过去非信徒提出过的论点是完全一样的,本章显示这是稻草人式的论证12。罗思修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他对我们在前一章讨论过的受造类别的错误认识,而后者又是因为他相信创世的第七天仍然在继续。
第九章简述了按照圣经记载的人类历史,从大约6,000年前创造亚当和夏娃开始。这数字是按照《创世记》5章和11章里的家谱计算出来的。我们论证了这些家谱是没有空缺的;而且因为耶稣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 马可福音10:6),说明人类被造是在宇宙被造之后不久。然后亚当堕落,把死亡带入世界;他的后裔继续落入邪恶的深渊,被神用大洪水审判。堕落和大洪水都在前面的章节里讲过。挪亚和他的家人通过方舟被拯救;他的后裔违背了神要人类遍满全地的命令,所以他们的语言在巴别城被神变乱。人类被分成不同的群体(population)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种族(race),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不同的族群(people group),这是基因库被分割的自然结果。然而,因为罗思修错误地理解了在同一类别之内的变化,他误以为神在巴别城的干预包括直接创造出人群之间不同的 “种族”特征。巴别之后,有些群体与文明分离,所以不得不生活在洞穴里并使用石器工具。有些被隔离的群体演变出不同的特征,结果就形成了我们所称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直立人(Homo erectus)。罗思修认为尼安德特人比亚当还早,不是真正的人类,而是没有灵魂的类人猿(hominids)。罗思修为亚当订出的错误年代意味着澳大利亚土著人(Aborigines)也可能不是亚当的后裔,也就是说按照他的标准不属于人类。
第十章比较短,是为了驳斥罗思修关于数十亿年地球历史的所谓“基于圣经”的论述。这一章指出,如果神想要讲地球有长久的历史,圣经就会这样教导了(但是没有)。
第十一章解释了那些通过随时间变化的过程来“测定年代”的方法背后的哲学,并与更好的方法对比,就是相信可靠的目击者的见证。然后这一章还显示,即使接受均变论/进化论的假设,地球上和太阳系里仍然有一些过程指向一个年轻的地球,其“年龄” 远远低于罗思修声称的几十亿年。
第十二章驳斥了一些支持年老地球论的所谓的科学证据。比如,被用来反对近期创造的一些地质学上的理由,如纹泥冲积层(varve)和化石森林(fossil forest),如果在近期灾变的框架下解释反而更合理。这一章也指出了放射性测年法所依赖的一些可疑的假设。事实上,如果放射性测年法给出彼此冲突的年代,或者得出的年龄与已知的岩石年龄不符合,就连进化论学者也会经常质疑这些假设。
注:因为本书是写给大众的,所以把一些技术性的(technical,专业性强的)和边缘性的(peripheral,非核心的)段落放在了深色方框里。
为什么写这样一本“负面的”书
有必要说明一下本书为什么需要采取这样一种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写下的,而且其目的不是为了攻击某个人。我们的任务是为了给信仰和圣经的权威辩护。我们很久以来就相信(并且解释了),在福音派圈子里,对圣经权威最危险的攻击不是进化论,而是“渐进创造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透彻地证明这一点。在圣经直白的文字上进行妥协,这种立场一旦广泛流传,就会带来极大的伤害,因为这是打着维护圣经的名义来进行的。这个议题之所以极端重要,是因为它牵扯到如何处理神自己的话语。希望读者理解,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也不是对不同的(隐含的意思是“合理的”)解经观点的吹毛求疵。我们应该像庇哩亚人学习,如同保罗在《使徒行传17:11》所赞扬的,在一切事上都查验圣经,把圣经当作判断对错的标准。
圣经根基
斥责假教师
揭露错误教导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也降低了教导源头的可信性,因此有些人说国际创造事工在对罗思修教导的分析“太个人化了”。如果这些批评者能具体指出他们发现哪些材料太个人化了,或者如何能揭露罗思修的教导的错误而不伤害感情,那就好了。要想揭示一个人的错误,而不伤害他的感情,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因为名誉、骄傲等等类似的事情与之相关。但是,因为罗思修博士公开地讲了如此谬误和贬低圣经可信性的话,我们对他的回应也必须是公开的。本书主要是针对他的教导,而不是他个人,重点是议题。然而,以下有阴影背景的部分显示出圣经里有尖锐批评的先例,远远比我和国际创造事工所做的强烈得多。
|
耶稣经常斥责他的对手。比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27节说: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太23:27和合本) 他拣选的使徒们常常责备假教师—使徒保罗甚至斥责了使徒彼得,当后者的伪善的错误影响到带坏其他人的时候(加2:11 始)。而且,保罗命令提摩太去驳斥错误(提后4:2);《哥林多后书》十章4-5节还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 有时错误的信仰被嘲笑,如列王纪上十八章27节里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所做的,为了更大的善,就要揭露他们的破坏性的影响。 圣经的文字游戏(word play)有时圣经里的文字游戏是故意嘲笑一些个人和体系,就是那些建立自己来反对神的。《创世记》十一章9节说: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 (创11:9 ,和合本) 有些怀疑者指控圣经犯了错误,因为“巴别”(bab-ili)在阿卡德文里的意思是“诸神之门”,而“混乱”的希伯来文是balal。但是这里完全没有错误—因为这个文字游戏是故意的!当巴别塔的反叛者自以为是在建立通天塔,但是神让他们的可怜的行动被后代按照正确的角度认识—人们记住这是语言变乱的时候。 另一个可能的例子是尼布甲尼撒的名字Nebuchadnezzar。一些怀疑者声称这是一个错误,而“正确的”拼法是Nabuchadrezzar。的确这是正常的希伯来文音译,来自阿卡德文的nabu-kudurru-usur,意思是“拿布保护头生子”,来自巴比伦的诸神之一拿布Nabu。有一个解释这个不同拼法的理论是:这是正常的希伯来文的语言实践,把r变成n。13但是范瑟暮(van Selms)提出了另一个理论,就是旧约的-nezzar拼法有可能是反对尼布甲尼撒的犹太人故意含有贬意地提到他的七年吃草如牛的动物行为。14也就是说nabu-kudanu-usur,意思是“拿布保护骡子”。15 挑战-回击的范式(Challenge-riposte Paradigm)一些善意的基督徒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没有爱心”(见下一段),就像一些怀疑论者试图抵制基督徒的反对一样!当遇到类似以上的例子时,这些基督徒试图避开这些范例的力量,声称:“耶稣是神,所以他有权柄和道德权利来说这些话。使徒们,还有以利亚在羞辱巴力的先知时,也拥有这些。但是我们没有。” 但这是不看历史背景。现代西方文化被“政治正确运动”(political correctness)掌控,充满了“受害者文化”,让我们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冒犯任何被自由派指定的“受害者阶级”的成员。但是古代的公众论坛,包括一些现代的,都经常是在挑战-回击的范式下运作的。在新约的文化背景下,“挑战-回击的范式是一个中心现象,是人必须在公众当中遵行的。” 16 辩论双方的目的是在交流中试图贬低对方的名誉或社会地位“作为要么同等量级、要么升级加码的回应(如此给予反向挑战)”17。不光是为自己辩护,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在这种文化下必须进行反击。 我们在福音书中看见数不清的例子,耶稣拒绝为自己辩护,而是掉转辩论的方向,一般是通过反问,有必要时也会羞辱对方。比如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23-27节》、《马可福音十一章27-33节》、和《路加福音二十章1-8节》,耶稣进入圣殿,祭司长和长老们质问他,要求知道他行事的权柄是来自哪里,耶稣的回应是反问关于施洗约翰(的权柄来源)。当他们拒绝回答他时,他也拒绝回答他们;这是一种羞辱。 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15-22节》、《马可福音十二章13-17节》,和《路加福音二十章20-26节》,希律党人和法利赛人一同密谋来问耶稣关于交税的事,试图把他拉入陷阱,显得要么是不忠于他的犹太民族,要么是对罗马谋反。耶稣有一次提出反问,关于钱币的(像和)拥有者。他的结束名句,“把凯撒的归给凯撒,把神的归给神”是再一次攻击他的对手的伪善和不忠。 另一个例子是《马太福音》十二章5节: 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 (太12:5 ,和合本) 多数人都不注意耶稣的问题“你们没有念过吗?”是对他的法利赛人对手的极大的羞辱。很显然他们念过经文,而且是被公认的圣经专家。所以这个问题在他们说起来最懂行的领域里贬低了他们的权柄。这就像问罗思修是否理解最基本的天文学一样。这基本上像是说他们是愚蠢的,不能理解显然的事,不肯恰当地做功课一样。但是再一次,在挑战-回击的范式之内,这是在公共论坛理当做的事。这是对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名誉进行的挑战给出回应,因为他们因他的门徒们的行为而挑战了耶稣。耶稣就把挑战升级加码,说他们对圣经无知,在他们最引以为骄傲的地方攻击他们。 有时耶稣可以特别地尖刻,设想你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犹太人,如果碰到死尸就会把你划入不洁净的另类长达一周之久(民19:11)。再设想你是一个犹太人宗教领袖,你的名声是维护和遵从律法的。然而耶稣说你不光是一般地接触死尸,而且是一个被死尸充满的坟墓!(太23:27) 还有许多其它地方,在那里耶稣“显示出高超的回击的技巧,并因此揭示出他自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和有权威的先知。” 18 |
“爱你的敌人”(《马太福音》五章44节)
圣经在这里用的“爱”的原文字是动词ἀγαπάω (agapaō),与名词ἀγάπη (agapē,“爱加倍”) 相关。这个词“与情绪和感觉无关,而是与具体的行动和实际的关怀有关”。19新约一般用“爱加倍”对应“联系和从属于一个群体的价值观”,而 “与眷恋的感情、喜爱的情绪、和温暖的感觉几乎毫无关系”。20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爱那些正在被、或即将被错误的教导领入偏路的人,所以很清楚“爱加倍”不排斥证伪或驳斥真理的敌人,而不把他们当作个人的敌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加倍”基本上等同于“刚强管教的爱”(tough love)。
这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要把神的旨意没有一样不考虑在内(使徒行传20:27)。人们会发现,如果国际创造事工要求与罗思修博士公开辩论的建议(见下文)得以实施,国际创造事工的同工对罗思修博士不会表现任何敌意或缺乏爱心。这从来就不是一个个人关系的问题,而且(按照以上解释的)爱被放在首位。
躲避那些分裂教会的人?
《罗马书》十六章17节写到:“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有些人使用这节经文来攻击年轻地球论。但是他们却不提这段经文的背景:保罗说造成“离间”(διχοστασία, dichostasia)和使人“跌倒”(σκάνδαλον, skandalon)的是那些“背乎所学之道的人”(违背你们所学的教义的人) 。正如我们所揭示的,那些对圣经直截了当的教导进行妥协的人才是“背乎所学之道”,就是违背使徒们的教导、违背教会两千年来的一贯理解。有意思的是,宗教改革家,如马丁路德,他重新恢复了圣经的权威、以及得救是唯独本乎恩典和因着信心的教义,然而他也被人攻击是“分裂教会”。
双重标准?
有时不得不诧异,为什么有人抱怨年轻地球论者的风格,却从来不批评罗思修博士攻击年轻地球论,而那似乎就是他的事工“信仰的理由”唯一“存在的理由”。难道那不也是“分裂教会”吗?比如,罗思修竟然把年轻地球论与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定罪的异端作恶意的类比:
就像割礼的问题分裂了第一世纪的教会一样,我认为创世时间的问题分裂了本世纪的教会。就像割礼扭曲了福音和拦阻了福音的传播一样,年轻地球论也做了同样的事。(《宇宙与时间》,162页)
罗思修还对乌雪大主教(Archbishop Ussher)21的一流的学问进行了末流的攻击(见本书英文版125页【中文版125页】),尽管后者的赞赏者包括牛顿爵士。22
最近,《灵恩杂志》(Charismata)引用了罗思修的话(经过他的首肯),说年轻地球论“鼓励某种形式的诺斯底派(灵智派Gnosticism)。” 23罗思修的理由是:年轻地球论“相信只有圣经是可信的,而不是物理的实在。”无论如何,他是在把年轻地球论与一个货真价实的异端相比较,那是一世纪教会与之艰苦争战并且最终击败了的,而《灵恩杂志》竟然为之叫好!在此之前,罗思修还和车理深(格里森·阿彻,Gleason Archer)24一起说过类似的话,是在《创世记争论:对创世日的三个观点》一书中他负责写的那一部分当中。25这是写在罗思修和车理深联合指控年轻地球论者否认物理实在之后,强把我们没说的话放在我们口中,说我们提倡一种“类似诺斯底派的神学”。这甚至被写在这一部分的副标题里:“诺斯底派的因素”。
虽然相信年轻地球论/年轻宇宙论的创造论者自以为他们真心寻求为神话语的真确性辩护、并领人归向基督,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立场导致这些神学倾向。我们认为他们虽然会否认这个诺斯底派的观点,就是‘在物质(matter)里面没有生命、真理和实质(substance)’,但是很不幸,那正是他们的观点所走的方向。按照圣经,这是一个危险的方向,因为神说一切被造物都是”好“的,而且因为在堕落之后,我们都在物质的领域内犯了罪。更重要的是:物质里没有生命和真理的说法已经被我们的主变成人这个事实所证伪---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却给自己加上了物质,好拯救我们脱离罪。否认物质里面有生命、真理和实质,至少是否认圣经关于创世、罪、基督和救恩的教义。最终这个观点否认圣经本身。26
这是一个更加煽风点火的说法,隐含说年轻地球论几乎就是否认圣经和基督。一些批评年轻地球论的人容许罗思修的这种煽动性说法,却极力反对年轻地球论者在回应中使用任何表现出严厉的口气。这说明他们使用双重标准。27
这一指控无论如何都是是荒谬的:
- 首先,年轻地球论者相信物质世界是可靠的,但是不一定相信关于物质世界的人为的理论----尤其是关于过去在其中所发生的事。
- 第二,诺斯底派相信物质是邪恶的,因为我们的世界是被一个“造物匠”(Demiurge)所创造的,而真神不会让物质玷污自己。年轻地球论者当然相信真神创造了物质。而且我们不信物质是邪恶的,而是本来 “甚好”的整个受造界受了咒诅。
- 第三,诺斯底派(Gnostic)这个词的来源是希腊文的γνώσις(gnosis),意思是“知识”。他们相信一种秘密的知识,只有内部人士才知道;却把圣经当作给大众的普通知识。然而,如果有任何人像诺斯底派的话,那应该是罗思修。是他在教导如果我们想理解圣经,仅仅使用语法工具书和关于历史背景的知识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采用只有内部人士(科学家)才知道的知识(“科学”),那是连圣经最初的读者也不知道的!
以下是我们收到的另外一些问题,以及我们的回答:
- 为什么你们不在中立的论坛上做辩论,比如在安科博或道伯勋(James Dobson)的节目上?28
如果存在“中立的论坛”这个稀有物种的话,我们希望它可以为子孙后代永久保存。安科博和道伯勋在创世问题上根本不是中立的,而是强烈支持罗思修。安科博的偏向在他主持的罗思修与贺文德(2000年十月播放)的辩论中一览无余。29那基本上是罗思修和安科博的联合团队反对贺文德。道伯勋常常邀请罗思修到他的节目上作客,但是他的节目制作者却说“创世记答疑”(Answers in Genesis, AiG)的主席韩慕肯(Ken Ham)是“分裂教会的教条主义”,因此不肯请他到节目上作客。安科博也从来不与国际创造事工联络,尽管这是全世界年轻地球论的领袖组织之一。
无论如何,我不理解辩论为何有这样强的吸引力。国际创造事工常常回应罗思修的公开声称,但是罗思修根本不理会年轻地球论者说了什么,而是错误地表达我们的论点(译者注:作“稻草人式的论证”)。重要的是双方的立场是什么,而不一定要面对面地说。辩论常常强调个人性格,而不是实质主题。
- 为什么不让神来对付他?
有人用大拉比迦玛列(Rabban Gamaliel)在《使徒行传》五章38-39节所说的话来支持他们的论点。迦玛列教导与他持相同立场的非基督徒犹太人如何对待犹太基督徒: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 (徒5:38-39,和合本)
但是我们要记住,圣经里所报导的(reported)并不都是圣经所赞成的(endorsed)。这里,路加并没有表达支持这种作法,而仅仅是准确地报导。前面引用斥责假教师的那些经文才是常态。很明显,把迦玛列的劝告当作普遍定律是愚蠢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如人这样说怎么样?“如果希特勒真的在杀害犹太人和侵占独立的国家,那么神就会对付他。”邪教又如何?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会怎么会很兴旺?
人其实可以从关于神主权的教义反过来论证,即神已经在对付罗思修博士,就是通过国际创造事工来揭露他的的错误。
有趣的是,这样的批评有逻辑问题,它会自我驳斥(self-refuting),就是反击提问的人自己!如果我们写文章反对罗思修是错误的,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这些提问者难道不应该不理我们,而让神来对付我们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有一种责任,就是当一个主内的弟兄犯了明显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应该去纠正。当你看见这个弟兄在带领其他人走向误区,甚至离经叛道时,更是责无旁贷!
揭露谬误会彰显真理
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受神重用的领导人一直都是努力驳斥异端。在神的主权计划里,谬误一直推动着正统的教会来澄清关键的圣经教义。早期教会中一个最危险的谬误是亚流派(Arianism),它否认耶稣是神,教导说他是一个被造物。伟大的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主要是为了对付这个异端被写下的,而这个信经至今仍然被基督教界的所有流派所接受,作为对基督的神性的最清楚的声明。比如,它说耶稣是“从真神所出之真神,是生非造,是与圣父同体。”今天的亚流派异端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导就有优秀的著作来驳斥,如罗德荣(Ron Rhodes)的《按照经文与耶和华见证人论理》(Reasoning from the Scripture with the Jehovah’s Witness)。30这本书也是展现关键教义的圣经根基的非凡之作。它包括核心教义,如基督的神性和身体复活,以及三位一体;也包括并非基要、但是重要的教义,如不得救者在死后受到永恒的有意识的惩罚。
我希望《驳斥妥协》一书也能作为对圣经的权威的强有力的辩护,包括圣经所教导的近期内的创世和全球性的洪水。有了这方面的强力根基,其余的经文也就得到巩固----特别是死亡是来自于罪,而罪的补救是福音,通过最后的亚当,即耶稣基督的牺牲和死里复活。
人可以相信亿万年历史而仍然是基督徒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从一开始就讲明。不管一些反对者如何说,国际创造事工(就像绝大多数的年轻地球论者一样)从来就很明确,人不需要相信六日创造论才能得救。圣经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不是藉着行为(弗2:8);使人得救的信心就是相信基督的神性(罗10:9-13,引用珥2:32证明基督就是主耶和华)以及他为我们的罪受死、被埋葬和从死里复活(林前15:1-4)。
我们认识一些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相信以上的核心教义,尽管他们不相信创造是在24小时一日的六日里完成的。范碧波和邰乐宝在批驳罗思修的书里明说了:“我们相信罗思修博士是得救了的,而且他愿意为主耶稣而活的动机是真诚的。” 31国际创造事工多年来销售这本书,为的是批驳罗思修的观点,并没有附带“不完全赞同作者意见”之类的话(disclaimer),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怀疑罗思修的得救。
事实上,国际创造事工的(澳洲分部)创办主席任舒强教授(约翰·任德-舒特Prof. John Rendle-Short, 1919-2010)曾经是一名得救了的神导进化论者(theistic evolutionist)长达40年(在国际创造事工诞生之前)。还有许多同样的人,包括他的父亲舒仁雅医生(亚瑟·任德·舒特Dr. Arthur Rendle Short),一名出色的英国外科医生和护教学家。舒仁雅在关于堕落前的罪和死亡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内心争战,32因为那是福音信息的根基(哥林多前书15:21-22,45, )。所幸的是,他在神学上并不连贯;我们在第6章将会指出有关的神学冲突;尽管如此,他持守了基要的信息。
不幸的是,布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的前同工滕普敦(查理·滕普敦Charles Templeton)后来就背道了,33还有持异端信仰的席邦主教(Bishop Spong),34他们都是神学上连贯的,因此就把福音和其基础一起丢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创造事工发表的好几篇文章都得出同样的结论:是的,人可以是基督徒而不信年轻地球论;但是那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在本书中会详细演示,主要涉及圣经的权威性和和可理解性,以及罪作为世界上人类和动物死亡和痛苦的终极原因。35
另一次耶路撒冷会议?
《灵恩杂志》2003年六月号论罗思修的文章说:
罗思修提议开第二次耶路撒冷会议来解决创世问题,仿效《使徒行传》的模式。那时早期教会领袖们开了一次峰会来解决一个大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外邦人信徒是否必须遵守犹太人的习俗和律法。他相信创世的争论是教会面对的最大问题,比妇女的角色问题还重要,“因为它影响到传福音”。36
这个提议是荒诞的,因为耶路撒冷会议牵涉到使徒们(徒15:6),所以雅各在《使徒行传十五章13节》之后的决议是有使徒权柄的。耶稣把“捆绑和释放”的权柄给了彼得,然后给了使徒们(太16:20)。在犹太人的框架下理解:“捆绑”的意思是禁止某事,而“释放”的意思是允许某事。今天无人有这等水平的权柄。
需要有这样权柄的原因是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所以教会需要被使徒们指导。现在圣经的正典已经封闭,而使徒们也不在世,所以圣经是教会唯一的指导(提后3:15-17)。
本书中一贯使用的参考书名的简化名
罗思修的书
- BtC—《宇宙之外》(科州科罗拉多泉城:导航会出版社,1996)。Beyond the Cosmos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1996). 这本书解释了多重维度的数学概念——他相信神是高维度的存在。这种说法假定高度猜测性的“弦理论”(String Theory)是正确的。罗思修还相信后者终于为一些理论问题提供了可能的解释,比如三位一体、神同时听见千百万人的祷告,还有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宇宙之外》
- C&tC—《造物主和宇宙》(科州科罗拉多泉城:导航会出版社,1995)。The Creator and the Cosmos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1996). 这本书是为了对非信徒传福音而写成的,据说展示了宇宙的起源和细调如何指向神的存在。
- C&T—《创世与时间》(科州科罗拉多泉城:导航会出版社,1994)。Creation and Time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1994). 这本书是写给基督徒读者的,试图在年轻地球论和年老地球论两种创造论者之间寻求停火。但是,在一开始挥舞白旗之后不久,他就在随后的章节中对年轻地球论者开火。
- FoG—《神的指纹》(加州橙县:应许出版社,1989,1991)。The Fingerprint of God (Orange CA: Promise Publishing, 1989, 1991).
- G1—《从科学的角度看创世记第一章》(加州母山市:博士影音公司,1983)。Genesis 1: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Sierra Madre, CA: Wiseman Productions, 1983).
- GQ—《创世记问题》(科州科罗拉多泉城:导航会出版社,1998,硬皮装订版)。The Genesis Question (Colorado Springs, CO: NavPress, 1998, hardcover). 本书将使用其2001年的第二版(软皮装订)的页数。这本书是对《创世记》1-11章的纵览,对象是基督徒;目的是为他的年老地球论辩护,试图驳倒年轻地球论。
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的书和杂志
- CAB—白藤(编),柯琦璞、夏法天和魏兰德(著),《创造论答疑》(佐治亚州粉泉市:创世图书出版社及网站,2009)。Don Batten, ed., David Catchpoole, Jonathan Sarfati, and Carl Wieland, The Creation Answers Book (Power Springs GA: Creation Book Publishers, creationbookpublishers.com, 2009).
- Creation—《创世》杂志。以前叫《从无到有》(Ex Nihilo)。所有的引用文章都使用改名后的杂志名。
- CRSQ—《创世研究协会季刊》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 C&C—柯力道,《创造与改变:按照不断改变的科学范式的光照来看创世记1:1–2:4》英国罗斯郡:良师书社【基督徒焦点出版社】,1997)。Douglas F. Kelly, Creation and Change: Genesis 1:1 –2:4 in the Light of Changing Scientific Paradigms (Ross-shire, UK: Mentor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1997).
- RE—夏法天,《驳斥进化论》(佐治亚州粉泉市:创造图书出版社及网站,1999)Jonathan Sarfati, Refuting Evolution (Powder Springs, GA:Creation Book Publishers, creationbookpublishers.com, 1999).
- RE2—夏法天,《驳斥进化论2》(佐治亚州粉泉市:创造图书出版社及网站,2002)Jonathan Sarfati, Refuting Evolution (Powder Springs, GA:Creation Book Publishers, creationbookpublishers.com, 2002).
- ST—《星光与时间》(阿肯色州绿林市:主人出版社,1994)。Russel Humphreys, Starlight and Time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1994).
- Journal of Creation—《创世专刊》,从前叫《从无到有创世技术性杂志》Creation Ex Nihilo Technical Journal,简称TJ。本书中一切引用都会用改名后的刊名。
- VB&T—范碧波和邰乐宝,《创造与时间:对渐进创造论者罗思修的读书报告》(亚利桑那州平顶山市:伊甸影音公司,1994年)。Mark van Bebber and Paul S. Taylor, Creation and Time: A Report on the Progressive Creationist Book by Hugh Ross, (Mesa, AZ: Eden Productions, 1994).
许多《创世》杂志和《创世专刊》上的文章(英文)都在国际创造事工的创世网站(creation.com)上可以找到。这些书当中的多数也可以在网站的书店上找到。
标准的神学书刊
- BDAG—“鲍大哥”,鲍尔、党科、安特和金里奇,《新约圣经和其他早期基督教文学的希腊文-英文辞典》(伊利诺州芝加哥市: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Walter Bauer, Frederick W. Danker, William F. Arndt, and F. Wilbur Gingrich,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3rd ed.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BDB—“不得不”,布朗、德里弗和布里格,《旧约的希伯来文和英文辞典》(麻州皮博迪市:亨德里克森出版社,1996)Francis Brown, Samuel R. Driver, and Charles A. Briggs, A Hebrew and English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Peabody, MA: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96).
- EQ—《福音季刊》Evangelical Quarterly.
- HALOT—“哈洛特”,寇勒和鲍嘉华(编),李察逊(译),《旧约的希伯来文和亚兰文辞典》(荷兰莱顿市:布利尔出版社,2002)。Ludwig Koehler and Walter Baumgartner, ed., M. E. J. Richardson, trans., Hebrew-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Leiden: Brill, 2002).
- JETS—《福音派神学协会季刊》Journal of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 Keil and Delitzsch—凯尔和德利施,《旧约注释》(密西根州大瀑布市:爱德曼出版公司,无日期)。Carl F. Keil and Franz Delitzsch,Commentaries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Wm Eerdmans Publishing Co., n.d.). 原作于19世纪德国,是德文。英译本被爱德曼出版公司多次重印。
- Leupold—廖颇得,《创世记释意》(密西根州大瀑布市:贝克尔书社,1942)。Herbert C. Leupold, Exposition of Genesi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42).
- TWOT—哈利来、车理深和吴特奇,《旧约神学辞典》(芝加哥:穆迪出版社,1980)。R. Laird Harris, Gleason L. Archer, and Bruce K. Waltke,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Chicago, IL: Moody, 1980).
- WTJ—《西敏寺神学季刊》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 当然还有OT对应旧约圣经Old Testament,和NT对应新约圣经New Testament.
科学术语
- 我们将在全书一贯使用标准的国际公制(SI)的标志和化学元素的符号。
- Ga = giga-annum = 十亿(109)年;Ma = mega-annum = 百万(106)年;Ka = kilo-annum = 千(103)年。
本章附录
以下是对罗思修最近出版的一个小册子(也在他的网站上)所做的注释。37他在里面给出了他对“年轻地球论者”和“年老地球论者”的理解。他把前者称为“历法日创造论者”(Calendar-Day Creationist),比如国际创造事工的;把后者称为“时期日创造论者”(Day-Age Creationist),比如他自己。因为这是从他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并用他自己的话谈事,所以我们不会被人说是把他没说的话放在他口里。然而,就如以下要揭示的,这里和他其它的著作一样,都有许多对别人的话的错误描述。这仅仅是一个总结—我们会注明在本书中何处会仔细解释。
CDC = 历法日(正常日/常日)创造论者,38即接受《创世记》一章里的日是正常长度的日,比如国际创造事工(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CMI)和创造科学研究院(Cre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RI),通常被称为“年轻地球创造论者”(Young Earth Creationist, YEC)。
DAC = 时期日(长期日/长日)创造论者,39如罗思修自己和许多其他的“渐进创造论者”一样,通常被称为“年老地球创造论者”(Old Earth Creationist, OEC),虽然这个术语也应包括“间隔论者”(Gap Theorist)。
罗思修博士的评论作为引文,前边有空格。注意在以CDC开始的段落里,被表达的是罗思修说我们所信的,不一定真正是我们所信的。
十项主要不同点
1.CDC(常日论):自然主义的生物进化会发生,可以在目(order)和科(family)以内产生新的属(genus)和种(species)。40
这是误导性的说法,因为我们不会把在一个类(kind)之内的分化(speciation)描述为“生物进化”,因为没有任何新的信息产生。然而,新物种的出现是不可否认的—罗思修似乎不理解,一个新的、不与其他群体交配生殖(繁殖隔离)的群体按照定义就是一个新物种。而且,没有任何圣经或科学的原因不许受造类内部发生足够大的遗传学变化,以至于在“属”或“科” (其实这些都是人为的分类)内产生新类型。这些都会在第七章里仔细解释。
1.DAC(长日论):自然主义的生物进化在一切层次都不会发生,除非在那些特殊的物种,即其总数超过千万亿(1015),增代时间不超过3个月,身体大小不超过1厘米。
这是一个奇妙的宣称—人不得不质问这位天文学家说这种生物学废话的资料来源是哪里。这种物种不变的观点远远超出圣经经文所说的,而且被实验科学所证伪—见第七章。
2.CDC(常日论):物理定律在亚当犯罪之前是大不相同的。
2.DAC(长日论):物理定律在亚当犯罪前后是完全相同的。
人不禁要问罗思修认为堕落是否造成了任何变化?(见第六章详解)。然而我们相信虽然神除去了一些超自然的维护,万有引力、热力学和电磁学定律都是从创世开始就一直在运作。国际创造事工有文字记录,一直就否认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从堕落才开始的。41
3.CDC(常日论):得救的人类将被恢复到乐园里。
3.DAC(长日论):得救的人类将被从乐园送到全新的天地里。
这也是误导性的,而且罗思修还做了煽动性的指控,说那些相信“恢复”的人是“邪教”。我们有经文记录说将会有“新天新地”(启示录21:1),而且现在基督徒就是新创造(哥林多后书5:17)。我们确认新天地讲比原来的乐园更好,因为将没有犯罪的可能性。然而我们指出,许多有关未来新天地的经文与描述洪水前的世界的经文相似。比如,素食的狮子和狼(以赛亚书11:6-9; 65:25),没有太阳却有光类似创世周的前三天(启示录2:7;22:2,14,19)。虽然我的书在末世问题上不采取特定的立场,罗思修是一名前千禧年派信徒(premillennialist),42相信有千禧年国度,其中有素食的前肉食动物(《创世记问题》98-99页)。前千派的神学家,如赖睿察(查尔斯·莱利Charles Ryrie),相信千禧年是《使徒行传》3:21 “万物复兴的时候 ”(见《赖睿察圣经研读本》Ryrie Study Bible)。持前千派末世论的历法日创造论者(常日论者)会同意罗思修的观点,即千禧年不是最后的状态,而且会有一个全新的创造。
表达我们与罗思修的区别的一个更准确的说法是:罗思修完全否认在堕落前曾有过一个没有死亡的乐园。这在他提出的最后一点区别中得到了更清楚的说明,见下。
4.CDC(常日论):《创世记》第一章记录的是物质的创造…
当然了!不光国际创造事工如此相信,而且神自己也这样说:在宣告十诫的第四个诫命时,神说他用六天创造了天地,并在第七天安息(出埃及记20:8-11)。
4.DAC(长日论):人需要综合圣经里的十个(或更多的)对创世的记载,这是非常重要的。
罗思修在说什么?圣经从来不自相矛盾,而且圣经里没有一处对《创世记》一章和《出埃及记》20:8-11表示否定的经文。
5.CDC(常日论):宇宙和星星是永恒的。
5.DAC(长日论):宇宙和星星是有时间局限的。
我们在什么地方说过宇宙和星星是永恒的了?这个声称是完全没有根基的,而且是完全不真实的。【译者注:这是“稻草人式的论证”。见本章注12】。
6.CDC(常日论):天文学家在欺骗公众。
6.DAC(长日论):天文学家在告诉我们真理。
哪位天文学家?天文学终身教授傅丹霓博士(丹尼·福克纳Dr. Danny Faulkner)就相信历法日创造论(常日论)。我们一般地会指出:世俗的天文学家不是故意地欺骗公众,而是在和我们看同样的数据,但却是透过错误的“眼镜”。
7.CDC(常日论):诸天仅仅揭示神的存在。
7.DAC(长日论):诸天也揭示神的超越的(transcendent)特质,以及他的许多个人属性。
很难理解罗思修在这里想什么。我们常引用《罗马书》一章20节,然而,我们不承认被造物启示了足够的信息,以至人可以得救;我们也不承认可能出错的人类对被造物的解释可以超越圣经中的宣示。请看第一章里对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的讨论。
8. CDC(常日论):按字义对《创世记》一章只有一个解释。
8.DAC(长日论):按字义对《创世记》一章可有多种解释。
这只能在对“字义”这个词有好多种“字义解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字义”的字义解释是:“接受字词的通常或首要的含意,使用普通的语法规则,不用灵意、隐喻或神秘主义解释”。“日”这个字的通常和正常解释是地球自转的一个周期;而且当它与一个数字、晚上和(或)早晨结合使用时,这个解释就是没有歧义的。这会在第二章里讨论。
9.CDC(常日论):《创世记》一章不能与公认的自然界的记录相协调。
9.DAC(长日论):《创世记》一章可以与公认的自然的记录相协调。
我们实际上说的是:“《创世记》一章不可能与对自然现象的均变论解释相协调。”这在第一章里会再次被讨论。
10.CDC(常日论):高级动物在亚当之前的死亡与神的品格和为人类的罪献上血祭的教义相矛盾。圣经没有为植物和低等动物赋予生命的特性和死亡的概念。
我们所说的是,植物从来没有被圣经称为有灵的活物(来自《创世记》里的希伯来文nephesh hayim),所以它们的生命与动物有质的区别。在堕落前的世界里(创1:29-30)和恢复后的世界里(赛11:6-9; 65:25),动物都是吃植物,因此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六章里讲这些。
10.DAC(长日论):高级动物在亚当之前的死亡与一个爱和仁慈的造物主并无矛盾。
请把这一点告诉那些身体被捕食者撕碎的动物吧,也请告诉那些被疾病折磨的动物(经常与折磨人类疾病相同,如癌症)。告诉它们说,这仍是一个“甚好”的世界,而不是犯罪后被咒诅的世界。
… 这与为人类的罪献上血祭的教义根本没有冲突。圣经的确为植物和低等动物赋予了生命的特性,并与死亡相联系。
如上所说,这是错误的。见《年老地球论的神》,43这本小册子论证,任何相信数十亿年历史的妥协理论都意味着,死亡和苦难从来就是神所创造的世界的一部分。而这是与圣经不一致的。
十项主要相同点
这十条我都同意,然而我怀疑我们的理解与罗思修的是否一致。
- 圣经必须首先被按字义(literal)解释,除非上文下理说明这个部分应该采用其它方式。
我同意这个论断,但是更喜欢用“平白”(plain)这个词,就是说“按照作者 的本意。”也就是说,在字义背景下作字义解释、在诗歌背景下作诗意解释。罗思修大概不会反对以上的话,而“字义”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说法,但是希望以上说法不要被神导进化论者丑化。问题在于罗思修对“字义”这个词有奇怪的理解,如前所示。
- 圣经在全部的学术领域里都是无误的。
当然!不过,虽然我不怀疑罗思修公开地和真诚地为圣经的无误性辩护,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他把世俗的“学术领域”放在了圣经之上。我们之间主要的区别大抵还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即圣经超越一切的权威性、明晰性和完备性。但是罗思修说“神的启示不是单单局限于神的话。事实上大自然可以被看作是圣经的第67本书”(《宇宙与时间》,56页)。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罗思修事实上教导的是“圣经加科学”(Scriptura et scientia)。在实践中,罗思修对圣经进行不自然的重新解释,以适应所谓的“自然界的事实”(实际上是进化论和均变论对自然界的解释),也就是“圣经顺从科学”(Scriptura sub scientia)。
- 宇宙是被超越地(transcendentally)和超自然地(supernaturally)创造的。
是的!但是哀哉,罗思修相信神使用了“大爆炸”来创造宇宙。大爆炸在本质上是无神论;它的多数的提倡者都认为宇宙自己创造了自己。而且大爆炸理论中的时间次序是与圣经的平白字义相违背的。
- 自然主义(naturalism)不能解释生命的起源。
同意!见问答:“生命的起源”,creation.com/origin.
- 自然主义不能完整地解释生命的历史;同样,神导进化论(theistic evolution)也不能。
没有争议。
- 自然主义不能完全解释地球的地质历史。
然而,罗思修对自然主义作了许多的让步,因为他不允许灾难性的、全球性的挪亚大洪水发挥作用,但这正是造成许多地层和化石的原因。
- 自然主义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和太阳系的天体物理历史。
这是真的。但是再一次,罗思修对自然主义作了极大的让步,尤其是同意自然主义的大爆炸理论,以及数十亿年的星系演变史。
- 《创世记》第一章按照时间次序描述事实。它记载了神在六日内造一个“甚好”的被造界。
我同意这些字句,但是如上所述,罗思修认为,这些字句的意思不是字面上所说的!他所描述的堕落前的被造界根本不可能是“甚好”的。因为其中有我们在今天世界上看见的一切可怕的死亡、挣扎、苦难、疾病和弱肉强食。而且对罗思修而言,“六日”有非常不一样的含意。
- 亚当和夏娃是字义上的一对夫妇,是神在仅仅数千年前造的。
是的,我们同意亚当是从尘土中被造的,而夏娃是从亚当被造的,没有动物作祖先。但是关于“数千年”,国际创造事工认定是六千年,是按照《创世记》5和11章里面含有年代的家谱直接推导出来的。罗思修却认为比那长好几倍,添加进去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巨大间隔。
- 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
我同意,但是我们会把被称为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和直立人(Homo erectus)的个体也包括在内,而罗思修却认为他们是没有灵魂的类人猿。
结论
罗思修在这里,如同在别处,对相信历法日(正常日,常日)创造论的机构做了误导性的指控,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的立场作辩护。然而,我们已经在多处显明他经常错误地描绘我们所信的,而且他自己的论证并不符合圣经。重要的是,不要被罗思修使用的所谓“科学共识”领入歧途,而是要永远站在神的话语的权威之上,也就是说,让神的话来教导我们,而不是把外来的思想强加在经文里。
- Andy Butcher, “He Sees God in the Stars”, Charismata (June 2003): 38-44. Jonathan Sarfati, “Shame on Charismata!”, creation.com/rosspc, May 29, 2003.
- Mark van Bebber and Paul S. Taylor, Creation and Time: A Report on the Progressive Creationist Book by Hugh Ross, (Mesa AZ: Eden Productions, 1994).
- M. Clark, A Review of Mark van Bebber and Paul S. Taylor’s “A Report on the Progressive Creationist Book by Hugh Ross” , , 23 May 2003.译者注:英文版本书此处在第一版列出了资料来源,但是第二版略去了。创世网站上http://creation.com/ refuting-compromise-refutation-of-hugh-ross-introductory-chapter-and-reviews#r3列出了克拉克的评论的网站地址。但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显然“信仰的理由”已经撤回了那篇文章。
- Jonathan. D. Sarfati, “Expos of NavPress’s New Hugh Ross Book: The Genesis Question”, Journal of Creation 13 (2):22–30 (1999); creation.com.org/ross_GQ.Danny Faulkner, “The Dubious Apologetics of Hugh Ross”, Journal of Creation 13 (2):52–60 (1999); creation.com.org/ross_apol.
- Bruce. K. Waltke and M. O’Connor,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Hebrew Syntax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 1990), 122.
- 译者注:贺文德博士是一名圣经创造论的普及者和辩论家,他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市(Pensacola,FL)建立了创造科学传道事工(Creation Science Evangelism)和恐龙博物馆(Dinosaur Venture Land)。然而因为他与国税局的冲突,被判入狱十年(2006-2016)。这教导基督徒要智慧地选择打什么仗(弗2:2)。
- 译者注:安科博是一名美国基督徒影音制作者。安科博秀邀请不同背景的基督徒领袖座谈或辩论,在世界范围的基督徒媒体上播放。
- 译者注:“RATE(速率)计划”代表“放射性同位素与地球的年龄”计划(“Radioisotope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Project)。这是创造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of Creation Research)组织一些科学家研究放射性测年法的计划。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些支持年轻地球论的不可否认的证据。
- 译者注:间隔论者认为在创世记1:1和1:2之间有一个极长的间隔,但是六日是正常日,不是神创造天地,而是神重造秩序的日子。他们也信“年老地球论”,但是与“渐进创造论”对六日的解释不同。
- 译者注:框架假说认为创世周的前三天和后三天有对应:前三天分开领域,后三天填充领域。而且因为这似乎是文学的(literary)设计,所以六日不是字义的(literal)或顺序的(sequential)。
- 译者注:英文from goo to you through the zoo的字义翻译是“从原始汤,通过动物园,进化到你”。其中借助同音字的幽默只能在英文中欣赏。我们给出技术上准确的中文翻译。
- 译者注:稻草人式的论证(straw man argument)是一个逻辑佯谬(logical fallacy),就是不攻击对方真正的观点,而是造出一个类似对方观点却不是对方观点的“稻草人”来攻击。
- Alan R. Millard, “Daniel 1-6 and History”, Evangelical Quarterly 49:67-73 (1977).
- 译者注:lycanthrophy从英文字根翻译是“狼人”,意思是人因为发狂而像狼(拉丁文lycos)一样行为,其含意可以扩展到像任何其他动物的行为,包括尼布甲尼撒的七年吃草如牛。不过,一个更合乎尼布甲尼撒的行为的英文词汇似乎是boanthrophy,字义是“牛人”,即人因为发狂而像牛(bovine)一样行为。
- John E. Goldinggay, Daniel,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vol. 30 (Dallas, TX: Word Books, 1989), 3, 4.译者注:作者给出了引用文章的书,但是没有给出页数和被引用文章的来源。我们补充了页数、并把资料列在如下:范瑟暮,“尼布甲尼撒的名字”,《在旧约的世界旅行:为毕克教授65岁生日的祝贺集书》,范福斯编著(荷兰阿森市:范国库出版社,1974), 223-229页,引用在225页。Adriaan van Selms, “The Name of Nebuchadnezzar”, in Travels in the World of the Old Testament, Studies Presented to Professor M. A. Bee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ed. M. S. Heerma van Voss (Assen: Van Gorcum, 1974), 223-9, esp. 225.
- Bruce J. Malina and Richard L. Rohrbaugh, Social Science Commentary on the Synoptics (Philadelphia, PA: Fortress 1993), 42.
- 同上注。
- 同上注。.
- David Hill, The Gospel of Matthew, New Century Bible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reprint edition, 1981), 130.
- Bruce, J. Malina and Jerome H. Neyrey, Portraits of Paul: An Archaeology of Ancient Personality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6). 译者注:英文版在这里没有给出引用的页数。
- 译者注:乌雪大主教(Archbishop James Ussher, 1581-1656)是爱尔兰的圣公会大主教(1625-56)。他写的著名的《世界年史》(Annals of the World)一书把创世的时间定在4004 B.C.。
- 译者注: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 1642-1727)是英国著名的科学家,牛顿力学三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光学色散的发现者。他也是一名基督徒,是圣经预言和年代学的资深研究者。
- 同本章注1。
- 译者注:车理深博士(Dr. Gleason L Archer)是著名的保守派旧约研究学者。他精通大约20种古代语言,并且激情地为圣经的权威辩护,驳斥高等批判等理论。他写的《旧约引论综览》(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是最好的同类著作之一。然而在创世日问题上,他采用了妥协的时期日观点。
- David, G. Hagopian, ed. The Genesis Debate: Three Views on the Days of Creation (Mission Viejo, CA: Crux Press, 2001).Andrew S. Kulikovsky, “Sizing the Day: Review of Hagopian”, Journal of Creation 16 (1): 41-44 (2002); creation/com/ Gen_Debate.
- Archer and Ross, in Hagopian ed. The Genesis Debate, 130-131.
- 译者注:英文版的there is one sauce for goose and another for the gander的字译是“用一种调味汁给母鹅肉,却用另一种调味汁给公鹅肉”,意思是使用双重标准,表现出内心偏向。我们给出解释性的翻译。
- 译者注:关于安科博秀,见注7。道伯勋的节目是“聚焦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美国基督教组织;他们的节目在全美基督教电台上播放。道伯勋已经退休;他的组织和节目还在。
- 夏法天对这个辩论进行了详细的评注,见” Jonathan Sarfati, “Ross–Hovind Debate, John Ankerberg Show, October 2000”, creation.com/ross_hovind.
- Ron Rhodes, Reasoning form the Scripture with the Jehovah’s Witnesses (Eugene, OR: Harvest House Publishers, 1993).
- Van Bebber and Taylor, A Report on the Book, 9. 【译者注:英文版没有给出引用的页数,译者查到和补上】。
- 见舒仁雅的自传:Arthur Rendle Short, Green Eye of the Storm (Edinburgh, UK: Banner of Truth, 1998). 请注意:舒仁雅医生的姓不是复合的(Arthur Rendle Short),而任舒强教授把父亲的中名和姓合成自己的姓(John Rendle-Short)。
- Carl Wieland, “Death of an Apostate”, Creation 25 (1):6 (Dec 2002 –Feb 2003); creation.com/death-of-an-apostate.
- Michael Bott and Jonathan Sarfati, “What Is Wrong with Bishop Spong? Laymen Rethink the Scholarship of Bishop John Shelby Spong”, Apologia 4 (1): 3-27 (1995); creation.com/spong.
- Duane Gish, “Is It Possible to Be a Christian and an Evolutionist? A Leading Creationist Answers an Often-asked Question”, Creation 11 (4): 21-23; creation.com/evochristian.Russel Grigg, “Do I Have to Believe in a Literal Creation to Be a Christian?” Creation 23 (3): 20-22 (June-August 2001); creation.com/must_believe. 文中说:“短的回答是‘不’,但是长的回答是‘不,但是…’”。
- 同本章注1.
- Jonathan Sarfati, “Ten Major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Calendar-Day and Day-Age Creationists? According to Dr Hugh Ross”, creation.com/ross_YvO.
- 译者注:在中文里还可以再简化:“历法日” = “正常日” = “常日”。
- 译者注:在中文里还可以再简化:“时期日” = “长期日” = “长日”。
- 译者注:按照林奈(Carolus Linnaeus)所定义的生物分类学的主要单位是:界(kingdom)、门(phylum)、纲(class)、目(order)、科(family)、属(genus)、种(species)。
- Jonathan Sarfati, “Arguments Creationists Should NOT Use”, Creation 24 (2):20–24 (March–May2002); creation. com/dont_use.
- 译者注:在系统神学的末世论(eschatology)教义中,有三种主要立场。前千禧年派(Premillennialism,前千派)相信启示录里的一千年应该被字义解释;基督先再来(启示录19章),然后建立千禧年国度(启示录20章)。无千禧年派(Amilllennialism,无千派)认为那一千年不应按字义解释;没有字义上的千禧年;教会时代就是灵意的千禧年,因为神的属灵国度已经降临。后千禧年派(Postmillennialism,后千派)相信教会将把世界基督化,建立神的国度;然后基督将再来接受它,奖励基督徒的工作。创造论主要研究圣经的开头(《创世记》),末世论主要研究圣经的结尾(启示录)。所以创造论者不一定有相同的末世论立场。个人观点在书中不须显明,好让读者群成为最大。如果对圣经从头到尾一致采用字义解经方法,结果是同时持有历法日创造论和前千派末世论。
- 夏法天,“为何有死亡和苦难?”(小册子)。Jonathan Sarfati, “Why is there Death and Suffering?”
圣经作为终极权威,显示地球不可能有数十亿年的历史。圣经中的六日创世、第六日造人和亚当犯罪导致人和动物的死亡等教导都与数十亿年历史的信念冲突。对于过去的事情,科学所能提供的帮助是很有限的,所以科学不能用来证明或反驳圣经。但即便接受进化论者或年老地球论者的均变假设,还是有许多的“年龄”标志指向一个远远少于数十亿年的地球。把一点说明还是有用的。
测定年龄
圣经创造论者相信,唯一能够为地球年龄下结论的是《创世记》记录的目击见证。在法庭上,一个能证明嫌犯不在现场的可靠见证可以推翻所有的旁证。没有比全知的创造主更可靠的目击证人了。创造论者也指出,在谈到过去的事情时,“科学方法”因为需要许多的假设, 所以是有限的。用科学的旁证来否定圣经直接明了的意思是愚蠢的。可悲的是,如第一章所说,许多基督徒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比如渐进创造论者和神导进化论者。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创造论者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科学证据的论文,这一章会对其中的多项证据做最新的详细阐述。这些论文的要点就是用对手的公理来推翻他的信仰体系(参哥林多后书10:4-5)。这是逻辑学家熟知的归谬法,即通过推出一个荒诞的结论来证明其出发点的错误。这是基督徒可以很有效地使用的技巧,而且耶稣本人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以及许多其他逻辑论证法1。许多反对基督教的陈述在表
- “不存在真理”--那么这句话本身也不真。
- “我们永远不可能确知任何事情”--那我们又何以确定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 “一个陈述,只有当它是逻辑的必然结果或者能被实践检验时,才有意义” (曾经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的验证标准)--这个陈述本身既不是逻辑的必然结果,也不能被实践检验,所以按照它自己的标准,是毫无意义的。
- “道德没有绝对的,所以我们应该容忍别人的道德标准”--但是“应该”意味着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即容忍是好的。
- “我们的思想只不过是大脑里的原子按着既定化学定律的运动”--然而无神论者却宣称这个观点是他们自由地根据证据思考的结果!
进化论者依赖一个称为均变论的原则:“现在是明白过去的钥匙”。这正是《彼得后书》3:4所预言的“好讥诮的人”的特征:“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得启示了持均变论的好讥诮人一个巨大的缺陷:他们“故意忘记”世界是神特别创造的,也忘记覆盖全球的(而且形成化石的)大洪水。本章里所引述的论文表明,根据进化论者的均变论假设会推导出与他们上亿年的信念相反的结论。他们如果想要否认这些论文的结论,就必须放弃他们自己的假设。这就是本章的宗旨。
四个要点
- 无神论者没有一个终极的理由去相信自然界的统一性。而没有自然界统一性的信念就不可能有科学。世界的有序性是不可能被证明的,因为所有可能的证明都必须以有序为前提。基督徒的依据就是圣经里创造万有的神--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希伯来书13:8)。3
- 无神论者相信,事物在过去是严格地均变的,但这一信条根本没有逻辑基础。因为过去是没法观察、也没法重复实验的。
- 因为无神论者有均变论的信念,所以基督徒有理由去论证均变论会导致与漫长年代的信念相悖的结论。
- 基督徒不应该曲解圣经去迎合这些在根本上是无神论的理论。
世界年轻的一些证据
如前所述,我们不是要用科学来证明圣经所记载的年代。下面的陈述,不管是支持“年老”地球还是“年轻”地球,都有可能因为新的数据或前提的改变而被修正。鉴此,我们要论证的是,即或接受漫长年代论者的均变前提,科学绝对支持地球的年龄远远小于数十亿年。但罗斯却试图“在井里下毒”。在《上帝的指纹》(The Fingerprint of God, 简称FoG)第155页,罗斯有一个标题“地球年轻的伪证据”, 指控年轻地球的倡导者们是“被误导的”或“误导人的”。他写道:
“所有这些年轻的‘证据’都有一个或多个问题,例如:
- 错误的假设
- 错误的数据
- 对原理、定律和方程式的错误运用
- 不了解反对的证据”
这是在运用一个被称为“摔大象”的辩论技巧。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辩方抛出一些总结性的结论,给人证据确凿的印象。但这些结论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就是这背后一堆复杂的理念都是正确的。而且这些结论不考虑反对的数据, 因为通常他们已经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己方的论点。但我们应该挑战这些“摔大象”的人,要他们给出具体的实例,并质疑他们的基本假设。
前文已经指出他们的基本假设的错误,下面将给出一些具体的实例,就是一些不支持亿万年历史的年龄指标。对每一个指标我先扼要总结,然后给出详细的描述。可以看出,在罗斯所提到的几个论点上,他自己反而犯了他指控年轻地球论者所犯的错误。
1. 地球磁场的衰减
鉴于地球磁场强度的快速衰减4,地磁年龄不可能超过1万年。在大洪水发生的那一年里,地磁方向发生了多次快速翻转,在其后的一段短时间里又继续波动,进一步加速了地磁能量的下降。
地球磁场的来源
像铁这样的材料是由许多微小的磁畴所组成的,每一个磁畴就像一个小型的磁铁。一个磁畴又是由更微小的原子组成的,这些原子本身就是一些微型磁铁,在一个磁畴里他们的磁化方向是一致的。但大部分的铁块并不是磁铁,因为通常情况下,不同磁畴的磁场相互抵消了。不过,在磁铁,比如指南针里面,大多数的磁畴是对齐的,这样整个材料就有了磁场。
地核主要是由铁和镍组成的,它的磁场是否也是像指南针一样形成的呢?不是的,当温度高于“居里温度”时,磁畴就被打乱了。地核最冷的地方是3400-4700ºC 5,远高于铁的居里温度(750ºC)6,也远高于任何已知材料的居里温度。
但是在1820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H.C. Orsted)发现持续的电流可以产生磁场。没有这个发现就没有现代科技社会离不开的电动机。那么地球的磁场是由电流产生的吗?电机需要电源,当电源被切断时,电流通常立刻就衰竭了(除非在超导体里)7。 没有电源,地球里面怎么会有电流呢?
答案来自伟大的创造论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他在1831年发现,变化的磁场可以产生电压,这就是发电机的基本原理8。想象地球在被造之后,地核有一个很强的电流,这就产生一个很强的磁场。没有电源,这个电流就会衰减,这个磁场也会跟着衰减。衰减就是变化,这个变化就产生一个电流,比原来的电流小,但朝同一个方向9。所以,地球有一个衰减的电流,产生一个衰减的磁场,而它又产生一个衰减的电流……如果磁场足够强,电流就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消失,这是当某些电器的电源被切断时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这个衰减的速率是可以精确计算的10。(电的能量不会消失, 而是转变成了热量,这个过程是在1840年由创造论物理学家焦耳(James Joule)发现的11。)
电流衰减的后果
已过世的创造论物理学教授托马斯·巴恩斯博士(Thomas Barnes)在1970年代注意到,自1835年开始有地磁测量数据以来,其主要组分12一直在以每世纪5%的速率衰减13(考古测量也显示地磁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比现在强40%14)。巴恩斯著有一本备受推崇的电磁学教科书15。他提议地球磁场是由地球的金属核里自然衰减的电流产生的。这完全符合观察到的衰减率,也符合根据推测中的地核组分的实验结果16。巴恩斯算出电流不可能已经衰减了一万年以上,否则它的初始强度可以把地球熔化。所以地球的年龄一定小于一万年。
进化论者的回应
电流衰减的模型显然不符合进化论者所需要的数十亿年时间。所以他们首选的模型是一个自我维持的发电机。据说地球的自转和对流现象使得地球外核的铁镍熔浆不断地环绕内核流动。又据说该液态金属浆内正负电荷的流动不均匀,这样就会形成电流,从而产生磁场。
| 尽管已经研究了40-50年,科学家们还没有得到一个可行的分析模型,还有很多问题17。加里·格拉兹麦尔博士(Gary Glatzmeier)以前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现在加州大学任职,提出了一个地球发电机的数值模型18,甚至展示了磁极翻转的行为19。但这是基于计算机模拟的结果,用了大量复杂的模拟代码,里面很容易有隐藏的问题,这类问题需要很多年才能被发现。而且模型需要初始参数。格拉兹麦尔的模型里地磁场的环状部分强度为150高斯,不现实地高(实际测量结果显示该组分的强度不到这个值的十分之一)。再者,模拟程序里假设地球外核的金属熔浆有非常高的导电率,约400,000-600,000 mho/m。实验室测量模拟地核材料的导电率只有30,000mho/m20。这意味着电流衰减实际上要快得多,这个液态发电机模型必须发更多的电。还不清楚格拉兹麦尔的模拟是否能顾及地磁的能量,或者它是否支持汉弗莱斯博士(Humphreys)的模型(参下面的“创造论者的回应”)。 |
对巴恩斯的年轻地球论述的主要批评,是有证据显明地磁极化方向曾有多次的翻转,即南北极对换。火山灰和熔岩里常见磁铁矿颗粒,当火山灰流和熔岩冷却到磁铁矿的居里温度(570ºC)以下时,里面的磁畴会部分地与当时地磁的方向对齐。当这些岩石完全冷凝后,磁铁矿的极化方向就被固定了。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地球磁场历史的永久记录。尽管进化论者并没有一个对磁极翻转的完好解释,但他们坚称巴恩斯博士简单的衰减假设是无效的。再者,在进化论的模型里,每一次翻转需要至少数千年的时间。而且根据他们的定年假设,他们相信在每次磁极翻转之间有亿万年的时间,所以地球是古老的。
虽然罗斯知识丰富,他却奇怪地宣称地磁翻转足以驳倒创造论者对地球磁场的整个论述:21
“论点B【地球磁场衰减过快,不支持年老地球】所忽略的是地磁场并不是稳步地衰减,而是遵循‘正弦曲线’模式。那就是说,地磁场衰减,然后增强,再衰减,再增强……这个曲线模式的证据来自世界各地远古的地质层。这些岩层显示地球磁场的极化方向每50万年翻转一次,翻转的过程本身需要大致1万年。”
创造论者的回应
物理学家汉弗莱斯博士(Russell Humphreys)相信巴恩斯博士的想法是对的,他也接受地球磁极翻转是真实的。他修改了巴恩斯的模型,加入了液态导体的特殊效应,来模拟地球外核的金属熔浆。如果熔浆向上流动(因为对流,热的液态上升,冷的液体下沉),这就有可能使磁场快速翻转22。 地质物理学家约翰·鲍姆加特纳(John Baumgardner)提出大洪水期间发生过地壳板块的下沉23。

汉弗莱斯提出这些下沉的板块可以急剧地冷却地球外核,推动上下对流24。这意味着大多数的翻转是在大洪水的时候发生的,每一到两个星期翻转一次。洪水之后,残留的对流运动还会使地磁场发生大规模的波动。
对主前1000年到主后1000年之间的地质考古材料的测量结果支持这一理论。测量结果显示,地表磁场强度(B)逐渐增强,到基督在世的时候达到最高,然后缓慢下降,到主后1000年左右开始呈指数衰减(参上图)。但是翻转和波动并不能止住磁场能量(E)的流失。能量衰减得比磁场强度更快,而且一直不断地减少。注意,磁场能量E是B2 在体积上的积分,这就是为什么磁场强度可以在洪水中和洪水后上下波动,但总能量却一直在递减。汉弗莱斯的模型也能解释为什么太阳的磁极每11年翻转一次。太阳乃是一个巨大的充满了炙热涌动着的导电气体的球体。发电机模型的理论家们很难解释太阳磁场如何能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不仅翻转极化方向,而且能再生并维持其强大的磁场。但如果太阳不过几千年,问题就不存在了。汉弗莱斯博士还提出了一个对他的模型的检验:应该可以在已知是在几天或几周内冷却的岩层里面找到地磁翻转的记录。比如,他预测在薄的火山熔岩里,外表会先冷凝,记录下地球磁场是朝一个方向;而熔岩内部则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冷凝,记录下地磁朝另一个方向。
他发表这个预测三年之后,该领域的研究先驱罗伯特·科(Robert Coe)和麦克·普雷沃(Michel Prévot)发现了一个肯定是在15天之内冷凝的熔岩薄层,里面连贯地记录了90度的磁极翻转25。这绝非侥幸,8年后,他们又报告了一个更迅速的翻转26。 这对他们和进化论界的其他人士是一个令人咂舌的消息,而对汉弗莱斯的模型却是一个强大的佐证。
汉弗莱斯给罗斯写了一封信(1991年6月9日),里面提到他在国际创造论大会(ICC)上发表的关于地磁翻转的几篇论文,而罗斯在他的回信(1991年7月17日)里面称已收到这些材料。但在那之后十年的时间里他继续批评巴恩斯的模型,而忽视汉弗莱斯对这个模型的改进。
对其他质疑者的回应
我们已经看到,罗斯错误地以为地磁翻转可以抵挡这个对古老地球信念的威胁。但还有其他持怀疑态度者提出的批评也是很重要而且需要解答的。
指数衰减?
有些持怀疑态度者,比如 “基督弟兄会”异端(否认基督的神性)的阿兰·海沃德(Alan Hayward ,“信仰的理由”有卖他的书,而且曾经在其网站上称赞他的“扎实的神学”),宣称指数衰减是错的,而应该是线性衰减。指数衰减和线性衰减曲线都有两个拟合参数:
- 指数衰减(i = Iet/τ)需要参数I和τ。
- 线性衰减(y = mx + c)需要参数m和c。
在现有数据有限的范围内,两个拟合很相似,没有大的区别。因为拟合的结果都不错,没有统计学上的理由要求必选其中一个。
不过,在回归分析里面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做法,就是当有良好的理论支持时,要用有意义的方程式来描述物理现象。这里就是如此。在由电阻和电感组成的电路里面,电源被切断之后,电流总是呈指数衰减27 。线性衰减看起来不错,但在电路的真实世界里却是荒诞的。事实上,在自然界里,线性衰减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而指数衰减却有电磁理论的坚实根基。
托马斯·巴恩斯首先指出地磁衰减是进化论者的难题。他是电磁学的专家。前面已经提到,他撰写了几本在这方面很受推崇的教科书 (他是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的名誉教授)。大部分批评他模型的人对电磁学的了解远不及他。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即使我们接受怀疑者提出的线性衰减,推算出来的地球年龄上限仍有9千万年,这对进化论和罗斯的大爆炸神学来说还是太年轻了。
最后一点是,如果真的是线性衰减,那我们离地磁完全消失就不远了!
地磁场的多极组分
一些怀疑者宣称:
“……仅仅是偶极子部分的强度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内‘衰减’了…… 非偶极子部分的强度(约占总场的15%)在同一时间里增加了,以至于磁场总强度几乎没变。巴恩斯假设场强在历史上一直递减,这当然不能与古地磁波动和翻转的证据调和。”28
这里的“权威”原来不过是一个反基督教的图书管理员所编纂的一本反创造论的辞典。就我所知,编者没有受过任何科学训练!所用的推理可能是从持无神论/不可知论的地质年代学者布伦特·∙达尔林普(Brent Dalrymple)那里抄袭来的,而达尔林普也没有电磁学方面的资格。汉弗莱斯在2001年7月这样回答这个“权威”: 29
“达尔文教的祝祷:‘地球磁场的非偶极子部分会拯救我们!’那确实是进化论者的陈词滥调。汤姆·巴恩斯在1970年代写的论文里已经讨论过。我在我的论文结尾也讨论过。30
超过90%的地磁场是偶极子(两极,北极和南极),其余的是非偶极子,或多极子,如四极子(两个北极和两个南极),八极子(四个北极和四个南极),等等。只要想象几根磁铁沿不同的方向绑在一起形成的磁场就可以了。
在1970年代,进化论者宣称,从偶极子部分的磁场里面消失的巨大能量(单位是焦耳或尔格)并没有变成热量,而是以某种方式储存在非偶极子部分里,以后再重生为一个相反方向的偶极子场。有的论文显示一些非偶极子部分的平均磁场强度(单位是特斯拉或高斯)略有增加。31
但是磁场强度并不是能量。要得到一个组分的总能量,我们必需把每一点的场强平方,乘以该点附近的体积和一个常数,然后把这样得到的空间各部的能量累积起来。非偶极子场的强度随着离地心的距离增加而递减,其递减的速度远高过偶极子场,所以非偶极子部分并不能比偶极子部分贡献更多的能量。这意味着一些非偶极子磁场强度的少许增加不能弥补偶极子部分每年流失的大量能量。
我很怀疑那里提到的论文是否真能证明进化论者的论点,即‘非偶极子能量的增加弥补了偶极子能量的流失’。不仅我前面的简单估算不支持这个论点,而且我1990年在ICC发表的论文里提出的翻转理论也不支持【如下所示,汉弗莱斯博士不再怀疑了--他(或任何去核对那些数字的人)现在都确知进化论者的宣称是错误的】。我的论文说到有些能量进到了非偶极子部分,但并不足以弥补偶极子部分的能量流失。我提出的翻转过程并不是高效的,会有很多能量转变成热能。在我的论文‘地球磁场还年轻’(Earth’s Magnetic Field Is Young)里的倒数第二小节(‘地磁场的能量一直都在递减’)讨论了这一点。32
我使用了权威性的《国际地磁实地考察数据参考》作为更进一步的证据。里面有代表整个二十世纪地球磁场变化的2500个数据。基本底线是:
在数据记录最准确的1970年到2000年,地磁场的总能量(偶极子和非偶极子)稳步递减了1.41 ± 0.16%。按照这个速率,地磁场每1500年(精确到一百年左右 )会流失至少一半的能量。这支持地磁一直在流失能量的创造论模型。这个流失从6000年前神创造了地磁时就开始,即使是在洪水中地磁两极翻转的时候能量也在流失。
另一方面,进化论者却没有一个能运作的、能用数学分析的磁极翻转理论。他们宣称使磁极翻转的不论什么机制都是100%高效的, 他们期望将来的偶极子场能量会与上一次偶极子场强的最高点(大约在基督在世的时候)一致。就是说,他们对上亿年磁场历史的信仰迫使他们相信每一次循环都是像凤凰一样从上一次循环的灰烬里重生,没有一点损失。
换言之,达尔文教要求他们必须相信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有形态的能量都会退化成热能--不适用于行星的磁场。听起来有点耳熟吗?”
在2002年,汉弗莱斯发表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33 ,更详细<地解释上述论点。摘要如下:
“用地球磁场各部分能量的流失来论证年轻的地球,本文又弥补了一个漏洞。进化论者依据的1967的年数据并不明确,但他们宣称小部分(‘非偶极子’)的能量增加弥补了主要部分(‘偶极子’)的能量流失。然而似乎没有人使用最新的、更准确的数据来检验这一宣称。我用《国际地磁实地考察数据参考》(IGRF)从1970年至2000年的数据,证明偶极子部分的地磁场稳步地流失了2350 ± 50 亿兆焦耳的能量,而非偶极子部分的能量只增加了 1290 ± 80 亿兆焦耳。在那30年间,地磁场可观察到的部分净流失的能量是 1.41 ± 0.16%。按照这个比率,地磁场会每1465 ± 166年流失一半的能量。结合我在1990年提出的解释大洪水期间地球磁场方向翻转和洪水之后强度波动的理论,这些新的数据支持创造论者的模型:自从神在6000年前创世以来,地磁场的能量就在不断地、迅速地流失。”
2. 岩石中的氦气
进化论者设想氦气是由岩石中某些放射性元素的阿尔法衰变产生的。氦原子非常小而且是惰性的,可以很快地从岩石里扩散出来。然而在一些岩石里面还存在大量的氦气,说明氦原子还没有足够的时间逸出--肯定没有上亿年。这是一个很强的证据,表明核衰变的速率曾经非常快。
氦元素是首先在太阳的光谱里探测到(希腊文 ἥλιος hēlios) ,后来才在地球上探测到的。太阳里的氦被普遍认为是由核聚变产生的。核聚变最有可能是太阳的能量来源34。它按照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式:E = mc2 35,把质量转换成巨大的能量。
在太阳里,最轻的氢原子聚合形成氦,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地球上,氦主要是由放射性元素的阿尔法衰变产生的。伟大的新西兰科学家恩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 ,1871-1937)发现阿尔法粒子就是氦的原子核。岩石里的放射性元素,如铀、镭和钍,就是这样产生氦气,然后氦原子扩散到空气中。
科学家可以测量氦气在岩石里扩散的速度。岩石越热,扩散越快。岩石在地里越深就越热。创造论物理学家罗伯特·金特里(Robert Gentry)当时正在研究用深处的花岗岩来储存核电站放射性废料的安全性。安全储存的要求是放射性元素不能太快地从岩石里通过。花岗岩里有一些叫做锆石的晶体常常会含有放射性元素。这样它们就会产生氦气,而产生的氦气应该会扩散掉。但金特里发现即使在很深很热的锆石(197ºC)里面也有太多的氦气--如果已经有了数十亿年的时间让氦气扩散,就不会残留着这么多。但如果氦气只有几千年的时间扩散的话,剩下这么多氦气就不稀奇了36。
核衰变曾经加快的证据
汉弗莱斯带领一个叫RATE (放射性同位素和地球的年龄) 的项目小组进一步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提出核衰变率的加快也许可以解释这么高的氦气余留量。37 这是基于几个对锆石(ZrSiO4晶体)的观察 :
- 根据目前的衰变率,衰变肯定已经持续了15亿年。
- 大量的(高达58%)氦气还留在那里。
- 然而新的RATE实验结果(也被其它实验室新发表的数据证实)表明,氦气扩散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完全扩散掉只需要大约10万年的时间。事实上根据氦气的扩散速度可以算出这些“几十亿年”的锆石的年龄只有5,680 ± 2,000年.
所以产生这些氦气的核衰变必定是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发生的。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氦气产生并积累呢?最好的答案似乎是在创造周或洪水年里,或更可能在这两段时间里,曾发生过加速的衰变。
当然,如果核衰变曾经加速过,那么放射性定年法的一个关键假设就不成立了。这个假设就是核衰变率是一成不变的。在第12章我们会看到这远非核衰变加速的唯一证据。
罗斯失败的反击
在2003年9月的一次广播节目里38 。罗斯和他的几个同仁向RATE项目发起反击。罗斯显然还没有读过这个项目的一些报告,他邀请的“外界专家”,罗杰·威恩斯(Roger Wiens),不得不几次批评“信仰的理由”的职员不懂这项工作。但甚至威恩斯也还没有读过其中的一些论文。
为了逃避锆石里的氦气的意义,罗斯宣称氦气太“滑”了,很难跟踪,应该很快就从矿物里逃掉。不过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如此,大部分放射产生的氦气还在锆石里面。为了避免这些锆石还年轻的结论,罗斯无理地假定锆石初始就有比现在高10万倍的氦气含量(宇宙大爆炸产生的,而不是放射产生的),所以快速的流失也可以进行了数十亿年的时间。他没有解释地球上的锆石何以含有宇宙大爆炸所产生的滑溜气体。罗斯不理会RATE发现的一个证据,那就是在锆石周围的矿物里面并不存在大量的氦气。最后,他还自相矛盾地提议氦气是通过某种方式从外面扩散到锆石里面的。这与大爆炸解释的扩散方向完全相反。不过,汉弗莱斯等已经表明了氦气是从锆石里面扩散到周围的矿物的。这也是符合基本的扩散规律的,即物质从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扩散。39
3. 海水中的盐分
盐分进入海洋的速度远快过从海里逃逸的速度40 。目前海水盐分的浓度不支持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几十亿年的时间。即使接受对进化论者非常有利的假设,海洋的年龄也不可能超过6200万年,远远低于进化论者相信的几十亿年。6200万年只是年龄的上限,而不是实际的年龄。
海洋是地球上的生命所必需的,它使地球的气候相当温和。不过,尽管海洋里有13.7亿立方公里的水,人却没法直接饮用,因为它太咸了。对化学家来说,“盐”是指金属和非金属的化合物,它包括一大类化学物质。通常的食盐是金属钠和非金属氯的化合物,即氯化钠。盐是由带电荷的原子,也就是离子组成,离子相互吸引形成相当硬的晶体。当盐在水里溶解时,这些离子就分散开了。钠离子和氯离子是海水中的主要离子,但不是仅有的离子。海水丰富的盐分对人类有益,因为海洋为我们的工业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矿物质。
海洋有多古老?
有许多过程把盐分带进海洋(参见下面“钠的输入”),而这些盐分不那么容易离开海洋。所以咸度一直不断地在递增。我们可以找出海里现在有多少盐,盐进入海的速度和离开海的速度。然后,假定我们知道这些速度在过去如何变化,海水里原初有多少盐分,我们就可以算出海洋的最高年龄。
其实这是牛顿的同事哈雷爵士(Edmond Halley,哈雷彗星的发现者,1656-1742)首先提出的。41更近期的地质学家、物理学家和放射疗法的先锋约翰·乔利(John Joly ,1857-1933)估计海洋的年龄最大为8到9千万年。42 但这对进化论者来说是太年轻了。他们相信生命是几十亿年前在海洋里进化出来的。(当然,不管他们说多大的年龄,罗斯和他的跟随者都坚决支持)
最近,地质学家史蒂夫·奥斯汀(Steve Austin)博士和物理学家汉弗莱斯博士分析了世俗地质科学机构关于海洋钠离子的数量及其输入和输出的数据。43 输入越慢,或输出越快,计算出来的海洋年龄就越大。
每公斤的海水含有大约10.8克的钠离子。这意味着海洋里总共有1.47 x 1016 (1.47亿亿)吨的钠离子。
钠的输入
地上的水可以溶解地表上露出的盐,风化许多矿物,尤其是粘土和长石,把其中的钠元素淋溶出来。河流把这些钠元素带进海洋。有的盐是由地下水直接带进海洋的,这叫海底地下水排放(SGWD),这样的水通常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海底沉积物会释放出大量的钠元素,海底温泉(热液喷口)也同样。火山灰也贡献部分的钠元素。
奥斯汀和汉弗莱斯算出现在每年有大约有4.57亿吨的钠元素进入海洋。即使接受对进化论者最有利的输入假设,过去可能的最低输入量也有每年3.56亿吨。
(事实上更新的研究发现盐分进入海洋的速度比奥斯汀和汉弗莱斯设想的快很多。这意味着海洋的最高可能年龄比他们算的要短44。以前以为SGWD只是地表水流(主要是河流)的很小部分【0.01-10%】。但新研究测量了沿海水里镭的放射性,证明SGWD可达到河流水量的40%。45)
钠的输出
住在海边的人常常会遇到车生锈的问题。这是由盐雾引起的。小滴的海水从海里飞出来,水蒸发之后,留下盐的晶体。这是把盐从海里除去的一个主要方式。另一个主要方式是离子交换--粘土可以吸收钠离子,而把钙离子释放到海水里。海底沉积物里的细孔也可以吸收部分的钠。有一些叫做沸石的矿物,它们的晶体结构里面有比较大的缝穴,可以从海洋里面吸收钠。
不过钠输出的速度远小于输入。奥斯汀和汉弗莱斯算出,现在每年大约有1.22亿吨的钠从海里出来。即使接受对进化论者最有利的钠输出速度假设,最高可能的数量只有每年2.06亿吨。
海洋年龄的估计
接受对进化论者最有利的假设,奥斯汀和汉弗莱斯算出海洋年龄的最高限度是6.2千万年。需要强调这不是真正的年龄,而是一个最高的限度。就是说,这个证据与任何低于6.2千万的年龄符合,包括圣经记载的6千年。奥斯汀和汉弗莱斯的计算假设整个地质时期里输入速度是所有可能值里最低的,而输出速度是所有可能值里最高的。另一个对年代久远论者有利的假设是起初的海水里面没有盐分。如果我们采用更实际的假设,算出的最高年龄限度会小很多。
至少,神起初造的海可能就是咸的,让咸水鱼类可以舒适地生活。挪亚大洪水应该从地上的岩石里溶解了大量的钠。当洪水退去时,这些钠就进到了海洋里。最后,比预期高的SGWD会进一步降低最高年龄限度。
4. 缺少“古老”的超新星遗迹
超新星是一个巨大的恒星爆炸。爆炸非常明亮,其亮度在短时间内可以超过整个星系。按照物理方程式算出,超新星遗迹(SNRs)应该在随后的几十万年间持续膨胀。然而在我们的银河系和它的卫星星系麦哲伦星云里找不到非常古老、膨胀了很多的(第三期)SNRs,而只有少数中等年龄的(第二期)SNR46。如果这些星系还没有存在很久,该现象就正是我们所预期的。
超新星47,即激烈爆炸的恒星,是神创造的茫茫宇宙里最明亮最强大的天体之一。平均来说,像我们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应该每25年就会产生一颗超新星。一颗常规恒星是一个巨大的、气态的球,其质量大约是地球的一百万倍。它可以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因为它的核所产生的能量会向外施加巨大的压力,以平衡它的质量所带来的向内的引力。
不过,当一颗恒星的核燃料用完之后,就没有力量来平衡重力了。如果这颗恒星的质量远大过我们的太阳,它的大部分物质就会快速坍陷--历时大约两秒钟。这会释放出非常巨大的能量。一颗超新星在短暂的时间里可以亮过它所在星系里几十亿颗的恒星。这样的坍陷非常剧烈,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被挤到一起,形成一个由中子组成的核心。这个核心的密度非常大,一汤匙这样的物质在地球上可以重达500亿吨。它不能再压缩,所以恒星余下的材料坍陷下去时就好像碰到一堵墙。这些材料就被中子核高速反弹出去,发出极亮的光。剩下的核只有20公里的直径,被称为中子星。因为它的自转速度很快,而且有很强的磁场,它会发出强大的无线电波束。这些波束会周期性地扫过地球上的天文观测站,我们便观察到规律性的无线电脉冲;所以,这样的天体就被称为脉冲星,而这个巨大的、膨胀的恒星碎渣云则被称为超新星遗迹(SNR)。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金牛星座的蟹状星云。产生它的超新星爆炸发生在1054年,它的亮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有几周的时间白天都能看到它。运用物理定律(和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天文学家们可以预测这个星云的演变。
根据他们的模型,这个SNR在12万年之后其直径会达到100秒差距(1秒差距=3.26光年=31万亿公里)。如果宇宙年龄有上百亿年,我们应该可以观察到许多这么大的SNR。但是如果宇宙年龄只有6千年,就不会有足够的时间让SNR膨胀到这么大。所以观察到特定大小SNR的数量是对宇宙年龄的一个绝佳的检验。从下面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出,观察到的脉冲星的数量符合宇宙只有几千年,而如果宇宙已经存在上亿年,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困惑。读者如果不愿意细看计算的过程,可以直接跳到下面的超新星遗迹表,思考它的含义。
一个广为接受的超新星膨胀模型有三期(参见图示)。

1)第一期从恒星碎渣以每秒7千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展开始。在这些碎渣扩展了300年之后,冲击波形成,第一期就结束了。到这时,它的直径达到大约7秒差距。这是一个巨无霸,是我们太阳系的25,000倍。太阳系“仅仅”是大约8光时大(大约86亿公里)。
因为第一期应该持续约300年,而每25年就应该有一颗超新星爆发,那我们的星系现在就应该有大约300/25=12颗第一期SNR。我们不能期望可以观察到所有的超新星--天文学家算出只有19%的SNR可以看见48,即12颗里面的大约2颗。在这里,宇宙是像圣经所提示的只有几千年历史,还是像进化论坚持的上百亿年,都没有差别。事实上,我们观察到5颗第一期的SNR,在误差范围之内与计算结果符合。
2)第二期的SNR,也叫绝热期49 或谢多夫期,会发射非常强的无线电波。理论预测它会持续膨胀大约12万年,直径达到100秒差距。这之后它开始失去热能,进入第三期。如果宇宙是上百亿年古老,我们可以预测(请记得每25年就有一颗超新星爆发,再考虑到第一阶段需要300年)在我们的银河系应该有大约(120,000-300)/25=4800颗第二期的SNR。但是如果宇宙只存在了大约7,000年,那就只有足够的时间形成大约(7,000-300)/25=270颗。天文学家算出47%的二期SNR应该可以看见。所以进化论/均变论预测大约2,260颗第二期的SNR ,而圣经创造论预测大约125颗。实际观察到的第二期SNR的数目可以很好地检验哪一个理论更符合事实。
事实上在我们的银河系里观察到了200颗直径从6到106秒差距的第二期SNR!这与圣经创造论的预测大致符合,但与进化论的预测却大相径庭。进化论者承认这个失踪的超新星遗迹是个“问题”,但给不出答案。
3)第三期,或恒温50 期,理论上讲主要是发射热能。这一期理论上是在12万年之后开始,会延续一百万年到六百万年。当SNR的直径达到大约420秒差距,与另外一个相似的SNR碰撞时,它的生命就结束了。或者当它膨胀到直径为大约560秒差距时,就与宇宙空间的“真空”无法区别了。
一个对进化论很有利的假设是第三期从大约12万年、直径大约100秒差距开始,持续到一百万年、200秒差距。这样,如果宇宙是上百亿年古老,我们的银河系里就应该有大约(1,000,000-120,000)/25=35000颗第三期SNR。这里面大约14%的应该可以观察得到,即大约5,000颗。不过,如果宇宙只有大约7,000年,应该就没有一颗SNR有足够的时间达到第三期。按照现在接受的模型,绝对应该一颗也观察不到。这是又一个对宇宙是年老还是年轻的检验。
事实上,在我们的银河系里没有观察到一颗直径在100-200秒差距的第三期SNR!实际观察结果再次符合圣经模型,而与进化论模型冲突!
结论
|
超新星遗迹阶段 |
预测在我们的银河系观察到的SNR数量,假设宇宙年龄为: |
实际观察到的SNR数量 observed |
|
|
上百亿年 |
7,000 年 |
|
|
|
第一期 |
2 |
2 |
5 |
|
第二期 |
2,260 |
125 |
200 |
|
第三期 |
5,000 |
0 |
0 |
如上表所示,宇宙年轻的模型符合观察到的低SNR数目。如果宇宙真的有数十亿年的年龄,我们就必须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的银河系里应该有的SNR,其中97%都失踪了。失踪的总数超过7,000颗。有一些进化论天文学家,在努力寻找解决这个差距的方法时,作出如此评论,“这两个异常需要解释。为什么大量预期的遗迹还没有被探测到?E0/n51值与我们估计的银河系的值有这么大的差别,这合理吗?”他们提到“失踪的遗迹之谜” 52,进而宣称:
“如果我们假设,由于用的遗迹数量很小(4),N(D)-D53 的估计值是错误的,这两个反常就消失了…… 看起来,有了以上的解释,就没有必要假定与银河系里的情况很不一样的E0/n 值,这样失踪的遗迹之谜就被解开了。不过,还是有必要假定麦哲伦星云中超出预期数目(~3)的小直径遗迹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波动而已;根据现有的证据,这似乎是最有可能的解释。”
所以他们的解决方案纯属臆测,而且假定以前的估计是有问题的。但这里不应该有什么谜,遗迹的数量低指明神造天地是不久以前的事情。54
5. 彗星
彗星55在它的轨迹上运行时,每次从太阳附近经过都会损失很多质量。在数十亿年之后,它们早已完全蒸发了。进化论者提出特设的彗星源不断地供应彗星。但是对提出的柯伊伯带区域的观察并没有证实其为彗星源。奥尔特星云则完全缺乏观察证据。这两个观念还有科学上的其他难题。罗斯发表的解释认为彗星起源于星际空间,但这个理论很久以前就已经被世俗的天文学者们遗弃了。
彗星是什么?
彗星是以很扁的椭圆轨迹绕太阳运行的“脏雪球”(或“脏冰山” 56)。它们通常有数公里宽,但哈雷彗星有大约10公里宽,海尔-波普彗星有40公里宽,是所有已知彗星里最大的。它们是由灰尘和“冰”组成的。这“冰”不仅仅是冻结的水,也包括冻结的氨,甲烷和二氧化碳。
彗星怎样发光——古老地球论的难题
当彗星从太阳的附近经过时,其中的一些冰蒸发形成一个一万到十万公里宽的彗发。太阳风(从太阳辐射出来的带电粒子)吹出一条背离太阳的、由离子(带电原子)构成的彗尾。太阳辐射推开灰尘形成第二条彗尾,背离太阳但向彗星经过的轨道弯曲。彗发和彗尾的密度非常低,比地上的实验室里能达到的最好的真空还要低。1910年,地球从哈雷彗星的一条彗尾穿过,几乎注意不到。但彗尾可以很强烈地反射太阳光。当彗星同时靠近太阳和地球时,景象非常壮观。它们看起来象长着长发的星星,由此得名(英文名Comet来源于希腊文κοµήτη,意思是长着长发)。
彗星每一次靠近太阳时都损失物质,这意味着它们在逐渐地毁灭。事实上,已经观察到许多彗星的亮度后来减弱了。哈雷彗星也不如过去明亮。不过它最近一次经过时的可怜表现主要是因为观察的条件差。当它最亮时,就是在近日点(靠太阳最近的地方)时,地球正好在太阳的另外一边,被挡住了看不见。当它从太阳后面出来时,离地球已经很远了。
另外,彗星也会被行星捕获,就像苏梅克–列维(Shoemaker- Levy)彗星在1994年掉进木星。有时彗星也会被抛出太阳系。彗星不太可能直接撞到地球,但如果发生就会是灾难性的,因为彗星有巨大的动能。有的进化论者相信彗星引发了物种的大规模灭绝。1908年在西伯利亚通古斯加上空发生的神秘大爆炸夷平了2,100平方公里的森林。有人认为它是彗星引起的。因为那里无人居住,所以也无人员伤亡。
进化论者的难题是,根据观察到的彗星质量的损失速度和其最高的运行周期,彗星不可能从据称的数十亿年前太阳系形成时就开始运行了。57
两类彗星
彗星分两类:短周期(200年以下)彗星,如哈雷彗星(76年),和长周期(200年以上)彗星。但这两类彗星的大小和成分似乎基本一样。短周期彗星运行的方向、平面通常和行星一样;而长周期彗星则可以在任何平面、朝任何方向运行。哈雷彗星是个例外,是朝与行星相反的方向运行,而且运行的平面有很大的斜度。有的天文学者提议它曾经是长周期的,但一颗行星的强大引力使它的轨迹急剧缩小,周期急剧缩短。所以长周期彗星和哈雷型的彗星被归为一类,称为“近似各向同性彗星”(NIC)。
如果太阳系天体可能的最大远日点(离太阳最远的距离)是50,000AU(AU = 天文单位,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1.5亿公里),那么一个稳定轨道的最长周期大约为4百万年。这是一个慷慨的估计,因为这个距离是太阳离最近恒星距离的20%,其它恒星已经有可能把彗星从太阳系夺走。58然而,即便一颗彗星的轨道有如此之长,如果太阳系有46亿年的历史,它也有足够的时间绕太阳运行1200次。但用不了这么多次,彗星早已被太阳消灭,所以彗星绝对不可能有那么古老。这个问题对短周期彗星来说就更严重。
进化论者的空洞解释
进化论者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用假想的彗星源来不断提供新的彗星。
奥尔特星云
最有名的假想彗星源是奥尔特星云,以1950年提出该假想的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Jan Hendrik Oort, 1900-1992)命名。他提出围绕太阳有一个球形的彗星云,一直延伸到离太阳3光年的地方。它是长周期彗星的发源地。从附近经过的恒星、气态星云、和星际潮汐应该可以把彗星从奥尔特星云撞到通往太阳系内部的轨道上。但这里有几个问题:
- 没有观察结果的支持59。所以,奥尔特星云是否能被认为是科学理论还是问题。它实际上是在接受数十亿年教条的前提下,为了解释长周期彗星的存在而临时编造出来的一个机制。
- 碰撞早已把大部分的彗星毁灭。经典的奥尔特星云应该是由太阳系进化起源(星云假想)的剩余物质组成的,其中的彗核总共有40个地球的质量。但更新的研究显示碰撞应该已经毁灭了大部分的彗核物质,只留下总共一个地球的质量。即使使用一些可疑的假设,也只剩下最多3.5个地球的质量60。
- “衰退问题”。 这个模型预测的NIC数量是实际观察数量的大约100倍。所以进化论天文学者们提出一个“人为的衰退函数” 61。最近的一个提议是彗星在我们有机会观察之前就被破坏了62。提出一个没有被观察到过的彗星源不断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提供彗星,然后找借口解释为何它没有按它应该的速度来输出彗星,这似乎是陷入绝境的表现。
柯伊伯带和离散盘
柯伊伯带应该是一个大约处于30-50AU(在海王星轨道以外)的环形彗星库,假想为短周期彗星的来源。它是以在1951年首先提出该假想的荷兰天文学家柯伊伯(Gerald Kuiper,1905-1973)命名的。柯伊伯有时被尊为现代行星科学之父。
为了消除进化论的困境,柯伊伯带里必须有数十亿的彗核。但是天文学家们找到的远远达不到这个数目--到2003年一月为止只找到651颗63。而且,迄今发现的柯伊伯带天体(KBO)都比彗星大很多。典型的彗核直径在10公里左右,但最近发现的KBO的直径估计都在100公里以上。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天体是“夸欧尔Quaoar”(2002 LM60),直径1,300公里,绕太阳运行的轨迹几乎是圆形的64。注意,一颗直径比彗星只大10倍的KBO,其质量就是彗星的约1,000倍。所以,实际上还没有在这假想的柯伊伯带附近发现彗星本身。可以说,这还不是答案65。因此,许多天文学家把这些天体称为海王星外天体。这是很客观地描述它们的位置在海王星以外,而没有像柯伊伯希望的把它们假定为彗星源。
再者,最近的观察表示柯伊伯带太稳定了,不可能成为彗星的储存库,所以现在认为短周期彗星的源头是“离散盘”。这是在更远的地方,那些天体(离散盘天体,SDO)的椭圆轨迹是很扁的,离太阳最近的距离为30-35 AU,最远距离超过100 AU。不过,这有同样的问题:天体数量太少,也太大。比如,一个叫Eris的SDO直径为2,400公里,甚至比冥王星还大。另一个叫Sedna的SDO也比夸欧尔大。
罗斯的观点:星际起源
罗斯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宣称彗星起源于星际空间(C&T:116-117)。但这在他写那本书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过时了。 这尤其令人吃惊,因为罗斯一贯宣称自己是一个很懂行的天文学家,认为基督徒应该接受天文学家的共识,任凭这些共识废除对圣经的根据文法和历史的解释。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天文学家接受这个观点,因为这样的彗星轨迹是双曲线型的,其速度超出了太阳的逃逸速度。而且这并没有被观察到过,虽然罗斯宣称有(C&T:116)。所以,尽管这样的说法过去曾经有人提议过,但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天文学家接受了。不然,为何需要奥尔特星云和柯伊伯带这样的假想?这是罗斯的书中根本没有提到的。创造论天文学家丹尼·福柯纳(Danny Faulkner)博士正确地认为罗斯“犯的很多错令人质疑他的能力”,这是其中之一。66
6. 月球的远去
月球正在以每年4 cm的速度远离67地球,过去更快。即使月球一开始的时候是挨着地球的,也只需要13.7亿年就到达它现在的位置。这是月球年龄的最高限度,而不是它的实际年龄。这对进化而言还是太年轻了(远比放射性“测定”的月球岩石年龄小)。
潮汐的摩擦作用正在减慢地球的自转,使得日的长度每世纪增加0.002秒。这意味着地球在损失角动量68。角动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地球所损失的角动量必须加给月球。这样,月球就正在缓慢地以每年4 cm的速度远离地球。而且,这个速度在过去更快,因为它是地月距离的一个很陡的函数(六次方的反比)69。 月球离地球的距离不可能低于洛希极限(18400公里)。因为地心引力对月球的潮汐作用(对月球不同部分产生不同的作用力)会把月球撕碎。
但是即使月球是从挨着地球开始远去,也只需要13.7亿年就到达它现在的位置70。注意,这里是年龄的最高限度,而不是真实的年龄。但这对进化而言实在太年轻了(远比放射性“测定”的月球岩石年龄小)。有人假想现在地月之间的潮汐作用是超常的大,借此来化解这个难题。如果在“正常”的时候,相互作用小的话,我们就因为使用了现在非常大的作用而低估了月球的年龄。 因为潮汐相互作用主要是依靠摩擦,所以取决于海洋和海底之间的接触。因此进化论者寄希望于过去的大陆布局使得海底接触面小,借以减小潮汐作用。
但是唯一接近直接测量月球远去的是测量潮汐周期造成的沉积层。它是由“细粒度层和粗粒度层随着潮汐每日和每月的涨落交替组成的泥床” 71。这里当然已经假定了进化论的时间尺度和它对潮汐周期沉积层的解读,所以这是又一个以其矛攻其盾的例子。这个数据不确定性很高,但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月球远去的速度是典型的,而不是超常的快。跨越过去9亿年(根据进化论的定年法)的岩石纹层展示强大的证据,说明这段时间里月球远去的平均速度与现在的速度非常接近。72天体生物学家克莱拉夫( Kara Krelove)论证说:
“通过测量潮汐周期沉积层得知,潮汐的幅度在那一段时间里是相对恒定的,这个事实可以提供一些边界限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为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从早期生物时间尺度推导出来的数据和基于对月球远去的现代观察结果得出的预测数据。如果潮汐幅度在9亿年的时间里保持相对恒定或只有很小的增加,我们被迫得到下面的结论:在那一段时间里或那一段时间开始之前的不久,月球不可能曾经靠近地球。否则必然会有潮汐幅度和时程的剧变。这样的“巨潮”至少在过去十亿年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要求或暗示它发生的模型都必须被重新审视……
基于这个记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月球至少在元古宙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从那时到现在潮汐基本没变(没有超出我们根据现代的模式来合理地解读它的范围)73。”
不过,她接受地球的进化论年龄,而且认定这些数据要求:
“……月球形成至少是在35亿年前,更可能是45亿年前,跟地球的年龄相差无几。”74
然而,这些数据这样解读更好:即我们今天观察到的月球远去的速度在过去“9亿年”(根据进化论的定年法)里基本没变。她似乎忽略了“9亿年前”月球远去曲线明显地“变陡”。所以月球远去的数据看起来确实是反对45亿年年龄的一个很好的证据。
7. 恐龙红血球和血红蛋白
在(尚未石化的)恐龙骨骼里找到红细胞和血红蛋白75。在显微镜下可见红色的小球,并可测到血红蛋白的化学标记。恐龙骨骼中还发现了带弹性的血管和胶原蛋白。但这些结构可保存的时间都不可能超过几千年,绝对没有6500万年(据称恐龙在6500万年前绝迹)。
玛丽亚·施韦策(Mary Schweitzer)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恐龙”杰克·何恩讷(Jack Horner)的学生。有一天,她正在蒙大拿州立大学用显微镜观察一块霸王龙骨头的薄切片。她描述说:
“实验室里充满了惊诧的耳语,因为我把显微镜聚焦在了一些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血管里的东西:小小的圆形物体,红色半透明,中心发暗。一个同事看了一眼后就大叫,‘你找到红细胞了。你找到红细胞了!’”76
施韦策的反应绝好地表现了一个人的偏见如何决定他怎样解读证据:
“这看起来跟一块现代骨头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我当然不敢相信。我对实验室的技术员说:‘这骨头毕竟是6500万年前的。红细胞怎么可能保存那么久?’”77
她给何恩讷看这个样品,他问道, “你觉得这些是红细胞吗?”她回答,“不是”,然后何恩讷说,“那就证明它们不是。”施韦策承认,“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能证明。”78
为了确定这不只是表明上看起来像红细胞,施韦策和她本校及怀俄明州立大学的几位化学家对这些样品做了血红蛋白测定。血红蛋白是血液里携带氧气分子的红色蛋白质。血红蛋白里的活性部分被称为血红素单元,由一个铁原子结合一个卟啉环组成。铁原子可以与氧分子松散地结合。血红素单元有特征性吸收谱(只吸收某些波长的光线)和拉曼光谱(由激光激发的分子震动产生),还有在磁场里的特异性行为(核磁共振和电子自旋共振)79。样品表现了所有这些特征,所以施韦策说,“我们觉得称这些恐龙组织里含有血红素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血红蛋白不仅仅是血红素而已--它还有四条肽链。别的蛋白质也含有血红素单元,例如所有生物(包括微生物)都有的细胞色素。为了排除污染的可能性,施韦策把样品寄给一位免疫学专家。他把从霸王龙骨头里提取的东西注射到大鼠身体里面。大鼠的免疫系统产生了抗体,而这些抗体结合在某些蛋白质的片段上了。血红素本身太小,是不能产生免疫反应的。然后免疫学家过滤大鼠的血液,只保留抗体,制成抗血清。实验显示,这种抗血清可以与现代生物的血红蛋白结合,包括鸟类、鳄鱼和哺乳类。一个对比样品,就是在大鼠被注射霸王龙的物质之前提取的血清,没有与现代生物的血红蛋白反应。
这意味着霸王龙的样品里含有足够的血红蛋白可以让老鼠的免疫系统产生专门针对血红蛋白的抗体。这个特定的免疫反应显示霸王龙骨头里面还存留着相当大量的血红蛋白。
血红素存留6500万年已经非常不可能了,何况更脆弱的血红蛋白。施韦策得出下面的结论:
“到现在为止,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证据都支持这个观点,即我们的霸王龙骨切片里保存有血红素和血红蛋白片段。但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我们才能信心充足地说,‘是的,这根霸王龙骨里有血。’”
施韦策后来宣称:
“我们相信当初的血红蛋白【含数百个氨基酸分子】里可能有三四个氨基酸还和血红素联在以起,可能就是这几个氨基酸触发了免疫反应。”80
不过这已经超出了她的领域。国际创造事工(CMI)的皮埃尔·究斯炯(Pierre Jerlström)博士是分子生物学的专家。他的博士论文包括用单克隆抗体识别蛋白质的技术。他对这个宣称深表怀疑,认为即使带着血红素,三四个氨基酸是不足以被对血红蛋白敏感的抗体识别出来的81。
血红蛋白不是唯一在恐龙或相同时代的化石里完好保存的蛋白质。骨钙素蛋白已在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的鸭嘴龙骨骼里鉴定出来。82这是骨骼中特有的蛋白质,所以不可能来自外来微生物的污染。
后来施韦策用EDTA溶解硬骨,发现还剩下一些柔软有伸缩性的血管。她还在霸王龙骨里发现了胶原蛋白,紧接着又在鸭嘴龙骨里发现了胶原蛋白。鸭嘴龙的定年比霸王龙更早(8000万年)。然而对胶原蛋白稳定性的分析显示,即使在最适合保存的条件下,在结冰点它最多可以保存二百七十万年。在 10°C,限度是18万年,在 20°C是1万5千年83。而恐龙应该是生活在温暖的气候中的。
几千万年之后,还有多少DNA、组织和微生物?
以上是生物材料保存下来的最有名例子。但这绝不是唯一的:
- 玉兰树叶的DNA。 从一块据称1700-2000万年的玉兰树叶化石中提取出DNA。84,85进化论者的难题是:DNA 分解非常快,甚至比蛋白质还快,如果这化石真的有几千万年,根本不可能提取出DNA。86
- 冰冻的细菌。 冰冻在南极的、经“鉴定”有800万年的细菌,已经在实验室里复活。87,88
- 琥珀里的细菌。有人宣称已经让休眠在1.2亿年的琥珀里的细菌“复活”。 89,90
- 盐里的细菌。2000年《自然》杂志(Nature)刊登了一篇论文,宣称已经复活了2.5亿年前的盐晶里的细菌。这些盐晶是从墨西哥一个600米深的地下矿窑里挖掘出来的。91,92
- 贝壳里的韧带. 在英国威尔特郡的斯温顿附近,伍顿巴西特的“集镇”旁有一些泥浆泉,不断“涌出”一些据说有1.65亿年的化石93。一位进化论古生物学家解释说:“一些双壳贝类的贝壳还带有原来的韧带,然而它们已经有上亿年了”。 94还有许多“闪闪发光的珍珠母贝壳”。
- 鲵蝾化石里的肌肉组织. 这件据称有1800万年的化石“有机地”保存了三维的肌肉组织。95里面有许多微观细节,包括“充满血液”的循环管道。研究人员评论这些组织展示“自从最初石化后只有非常轻微的变质……这是化石记录里保存得最完好的软组织。”96,97

- 乌贼墨汁化石和墨囊化石。一个石化的乌贼墨囊经“鉴定”有1.5亿年。它里面的墨汁被用来画了一只乌贼和写下它的拉丁文名称。一位进化论地质学家承认,“其结构和现代乌贼的墨汁相仿,所以我们可以用它写字。 它们可以像活的动物一样被解剖,你可以看见肌肉的纤维和细胞”。 98,99
总之,施韦策的问题,血细胞怎么可能保存6500万年,可以有另一个问法,“我现在可以看见血细胞和血管,检测到化学特征和磁场特征。而且我们观察到蛋白质和DNA降解得非常快,不可能保存几万年。那么它们怎么可能有6500万年之久呢?”
8. 放射晕
花岗岩里的钋放射晕强烈地提示,这些放射晕是快速形成的。成熟的铀放射晕有力地表明,从前曾有过放射性衰变的加速。煤化木材里双重的(球星或椭圆形)的钋放射晕,则提示虽然煤层之间“鉴定”出亿万年的时间差距,但里面的很多木材是在同一次大洪水灾难里被拔起并压缩的。再者,这些木材里的铀放射晕中心还有很多剩余的铀,挑战着这些煤层“已经确认的”亿万年的历史。罗斯仅曾试图回应快速形成的论点,并且也只是引用了一位业余地质学者在一个人本主义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把该作者都承认是猜想的形成方式定为教条。
放射晕是在某些矿物晶体里的球形微观结构,其直径通常为几十个微米(一微米是一百万分之一米)。放射晕常见于花岗岩里一种叫黑云母的云母矿中,但也有人在一颗钻石里发现了放射晕100。放射晕的形成是由于它的中央有一个含一种或多种发射性同位素的微小的放射芯。这些同位素放射出阿尔法粒子,从放射芯向四面八方扩散,使矿物变色。阿尔法粒子最终从矿物里的其它原子夺得两个电子,颜色的改变在那里也最强烈,这就是放射晕的外缘。

一种同位素放射出的阿尔法粒子会有一个特定的能量,这意味着阿尔法粒子在矿物里的扩散也有一个特定的距离。因此,阿尔法粒子所造成的球形变色区域具有该元素特征性的半径。再者,有的放射性同位素呈链式衰变,衰变链上的某些同位素也会放射阿尔法粒子,所以会形成多个同心球体。从截面上看,这些球形放射晕显示为一系列的同心圆。
例如,在 238U 的衰变链里有15种同位素,其中有八种放射阿尔法粒子(包括238U 本身),形成八个圆。在钋的同位素里面,218Po 形成三个圆,214Po 形成两个,而210Po 只形成一个。参见下面四种放射晕的示意图。101
快速形成
罗伯特·金特里(Robert Gentry)博士在很多年里是全世界领先的放射晕研究者。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是在田纳西州声望很高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ies )度过的,而且他在高影响度的科技期刊里发表了许多论文。102
他指出,有几种钋同位素的半衰期非常短:218Po (3.1 分钟)、214Po (164 微秒) 及210Po (138 天)。它们形成了一些“孤儿”放射晕,中间没有母元素238U 造成的直径较小的圆圈。
因为放射性元素经过10个半衰期之后,就只剩下千分之一(1/210),20个半衰期之后就只剩下百万分之一(1/220), 这意味着形成这些放射晕的时间不会超过大约20个半衰期。对于这些钋同位素来说,这一段时间就很短。而且放射晕必须是在固体里面形成的,因为在液体里面这些小小的球形印记会立即消散。那么这里有一个两难,一旦岩石凝固,钋就不能再进入放射芯的位置,尤其是在其衰变的短时间里。金特里检查了含放射晕的晶体是否有缝隙可以让矿物进到放射芯,把这个因素排除了。
但是金特里犯了一个错误,他直截了当地把它的意义说了出来:那就是,这些放射晕是底层花岗岩被快速创造的初步证据。那之后,论文发表的门就被关闭了,而且他的聘任合约也被终止了。103
对他的工作的批评有很多,但都不值一提。罗斯自然试图把金特里的证据打折扣(C&T:108-110)。 例如,罗斯引入“地质学家”魏克斐尔德(Jeffrey Richard Wakefield)作为一个权威(C&T:109)。但他却没有提到魏克斐尔德只是一位业余的地质学家,他是一位消防队员。罗斯只是在他的书最后的索引里引用魏克斐尔德,而引用的文章之一不是出自科学文献,而是出自无神论者资助的反创造论期刊《创造/进化》(Creation/Evolution) 104 。而且罗斯忽略了金特里详细的回应105 。
罗斯还宣称:
“还有两位地质学家,奥德穆(Leroy Odom)和林克(William Rink), 最近也发表论文回应金特里的钋衰变假说106 。他们首先指出有三种解释不了的放射晕。对其中一种,巨型晕,奥德穆和林克用另外一个叫空穴扩散的地质过程来解释。(我比较犹豫提起这种理论,因为它太复杂,很难用几句话就给不是学地质或固体物理的人解释清楚。我请你去找其他的地质学家或固体物理学家确证这项研究)。”
这一段里有很多以科学为名的虚张声势。我读过固体物理的研究生(不像罗斯),也问了受过地质学训练的同事,我们都不同意罗斯说的!他继续说道:
“空穴扩散产生放射晕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这更支持年老的地球,而不是瞬间创造。既然三种“神秘的”放射晕之一现在已经可以用正常的(地球年代久远的)、已知的物理过程来解释,作者们推断最终可以同样解释剩下的两种,包括金特里的钋218晕。”
尽管罗斯这样教条地宣称,他引用的作者并不认为他们已经驳斥了金特里。奥德穆私下写信给金特里,说 (黑体是另加的):
“发表在《科学》上的论文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我们并不是在做这个工作。论文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我们并没有证明什么--仅仅是提出另一个解释而已。我们本来在论文标题后面放了一个问号,但显然编辑把它去掉了。”
罗斯也没有告诉他的读者奥德穆最多也只是解释了一种晕,而且还不是金特里用来作为证据的一种!它跟金特里的关键论证,钋放射晕,一点关系也没有。
迅速衰变的证据
对放射晕证明花岗岩迅速被造的论点,有一些批评似乎比较切实。一个主要的批评是在非底层花岗岩里也发现了放射晕,例如,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石头山的花岗岩里107 。这意味着放射晕不是原初创造的产物。不过,下面将要论证,放射晕虽然不能证明迅速创造,它们仍然是岩石迅速形成的证据。
再者,似乎只有238U衰变链中的短寿命同位素形成了放射晕,而235U 或232Th衰变链里相同的同位素却没有形成放射晕。这可以引出一个问题,为何神没有直接使用另外两个衰变链里的短寿命同位素制造放射晕呢?当然,这是把沉默当成论据,但这确实是与一些只与238U 衰变链相关的物理过程一致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进化论者就再没有“微小的谜”了--远非如此!RATE(放射性同位素和地球的年龄)项目的创造论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分析了他们鉴定为大洪水期间形成的花岗岩里的放射晕,108 例如,石头山花岗岩、库玛花岗闪长岩、和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另外四个花岗岩体。他们不可能是在创世周形成的,因为很清楚他们是由大洪水积淀的含化石的沉积岩熔化形成的,而且挤进了其他大洪水积淀的岩层里。
这些岩石里都有黑云母颗粒,其中有很多放射晕。主要是 210Po放射晕--数量经常是214Po 或 238U放射晕的4至10倍--而218Po晕则很少见。但是库玛花岗闪长岩和澳大利亚东南部的另外四种花岗岩里238U放射晕的数量超过所有的Po放射晕。其中两种花岗岩里面214Po放射晕和210Po放射晕的数量相当。库玛花岗闪长岩里还有许多深色的、完全成型的Th放射晕。
U和Th的半衰期特别地长--分别为45.1亿年和141亿年。所以按照现在的衰变率,大量深色的、完全成型的U和Th放射晕表示从它们形成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亿年的放射性衰变了。但是这些岩石又显示是在大洪水那一年才迅速形成的,这表示在大洪水年里至少有1亿年(按现在的衰变率)的放射性衰变发生。那时地质过程在以灾难性的速度运作。不过,在后来形成的岩石里面却找不到这样的深色晕,尽管根据均变论的定年法应该还有完全足够的时间。如果这些岩石根本没有这么老,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所需的衰变发生,这就可以解释了。
在大洪水岩石里观察到的放射晕是与大洪水那年放射性衰变突然加速一致的。这严重地破坏了放射性定年法(参下一章)。再者,这样的加速衰变应该在大洪水期间释放出大量的热,热能进而开启并驱动了在大洪水期间全球板块的运动。大量的地质变化就是这样灾难性地成就的,包括沉积岩层的区域性变形和地壳地幔岩石的熔化,形成了花岗岩和其他类型的岩浆。
钋放射晕仍然指向迅速形成!
虽然这些放射晕不可能是原始的,但是因为半衰期很短,它们一定是很快形成的。的确,钋一定是在它衰变之前就与它的母元素铀分开,并被传输和集中到放射芯。很可能钋和它的直接前体在附近的锆石里由铀衰变产生之后就被热水传输了一段很短的距离。这些放射芯是由晶格缺陷中的离子选择性地浓集钋同位素而形成的。浓集的钋在衰变时就形成了放射晕。因为热水是在花岗岩浆结晶过程中产生的,这个结晶过程也一定是非常快的,仅仅几天而已。因为这些水很快就把热量带走了。109
煤化木里的放射晕指向近期发生的大灾难!
金特里分析了从科罗拉多高原的铀矿里找到的、部分煤化的木材。 它们来自三个不同的地质构造里富铀的沉积岩110 。放射性“定年”给出的年龄是0.35至2.45亿年。因为我们已经接受这些木材不是原始的,那些对金特里其他工作的批评对这里的论述完全无效(如上所述,他的论点只需要修正,而不是放弃)。这里找到的主要放射晕是由210Po 产生的,只有一个圆。这些木材被富铀的溶液浸透,里面一些微点选择性地吸引钋原子。钋衰变之后形成放射晕 。
这里展示了在富铀和易渗透的环境里会发生什么情形--只有210Po放射晕形成。其他的钋放射晕没有形成,因为它们衰变太快,还没有时间在煤里扩散。这让我们可以推断渗透的时间:如果远超过一年,210Po应该在它集中到放射芯之前就衰变掉了;但一定超过一个小时,否则218Po放射晕就应该形成了。这也说明在花岗岩里其他钋放射晕的形成是特别迅速的。
圆形和椭圆形的钋双晕指向迅速的挤压
有许多放射晕是椭圆形的。这意味着它们形成之后被从一个方向挤压了。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放射晕(如右图)有同心的一个圆和一个椭圆。这意味着在挤压之后,还有剩余的钋形成了第二个晕。换言之,渗透和挤压一共只能有几年的时间。即使我们接受某些晕是由210Pb 经过210Bi衰变为210Po产生的, 这也只允许22年的时间内完成渗透和挤压。

这些双晕指向一个灾难性的大洪水。洪水大面积地把大树连根拔起,堆积在一起,浸泡在富铀的水里。然后它们被大量沉淀的泥沙掩埋。泥沙将这些放射晕快速压缩。
再者,从三个不同的地质构造里都发现了这样的双晕。这些地质结构据称跨越了2亿年的时间。但这些完全相同的系列事件提示,它们是在同一次灾难中沉积下来的,然后在同一个地质运动中发生了变形。这与圣经里记载的全球性大洪水一致。
放射晕里的238U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发生衰变
金特里使用了最先进的离子探针技术来分析这些煤化木里238U放射晕的放射芯。结果显示有很多铀,但只有极少的铅。238U 和在它衰变链终点上的206Pb 的比例为64000。如果衰变率一直没变,就表示这些铀只存在了几千年的时间,否则会有更多的铀衰变为铅。注意,这里的论述使用了常规放射定年的假设,来证伪亿万年的观点--用进化论者的武器来摧毁他们自己的论点。从三个地质构造中都得出类似的结果,表示它们实际上年龄相当,而不是相差2亿年。
9. 大陆的侵蚀
大陆正在被迅速地侵蚀111。如果有几十亿年的时间,它们早就被完全冲走了。这个问题在山区尤其严重,然而还有大片的平原几乎没有被侵蚀的迹象。罗斯提出地壳的隆起平衡了侵蚀现象,试图以此来回应大陆侵蚀的问题。但这不能解释为何存在被“鉴定”为非常古老的侵蚀面。
水在一直不断地侵蚀着陆地。它溶解许多的矿物质,使泥土和岩石松动,并把它们运送到海洋里。侵蚀的速度可以通过测量河流入海口的水流量和泥沙含量来估算。还有沿着河底滚动或被推着走的沉积物,这些比较难测量。考虑到罕见的灾难性事件,侵蚀率肯定更高。
不管怎样,沉积学家们根据他们对河流沉积的测量,已经计算出陆地消失的速度。他们表明,有的河流每1000年会将其流域的地面降低1米以上,但也有的在1000年内只冲掉1毫米深。全球的陆地平均高度每1000年降低大约60毫米(表11.1),这个数值的根据是每年有2400万吨的沉积物进入海洋。
|
表11.1 世界部分主要河流的侵蚀率:平均每1,000年其流域地面降低的程度,单位为毫米 |
|
|
河流 |
每千年地表降低的毫米数 |
|
渭河 |
1,350 |
|
黄河 |
900 |
|
恒河 |
562 |
|
阿尔卑斯莱茵河和罗讷河 |
340 |
|
圣胡安河(美国) |
340 |
|
伊洛瓦底江 |
280 |
|
底格里斯河 |
260 |
|
伊泽尔河 |
240 |
|
台伯河 |
190 |
|
印度河 |
180 |
|
长江 |
170 |
|
波河 |
120 |
|
加龙河和科罗拉多河 |
100 |
|
亚马逊河 |
71 |
|
阿迪杰河 |
65 |
|
萨凡纳河 |
33 |
|
波托马克 |
15 |
|
尼罗河 |
13 |
|
塞恩河 |
7 |
|
康涅狄格河 |
1 |
大陆为何还存在?
前面提到的速度听起来不算什么,但经过所谓的数十亿年时间,累加起来就很大了。在25亿年的时间里, 93英里(150公里)高的陆地都会被侵蚀掉。所以,如果陆地的侵蚀已经发生了数十亿年的时间,地球上应该没有陆地了。比方说,如果侵蚀速度保持在平均值,北美洲在一千万年内就被削平了112。注意这是最高限度,而不是实际年龄,但它远远小于所谓的25亿年的陆地年龄。
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许多河流侵蚀其流域的速度远高于平均值(表11.1)113。即使使用最慢的每一千年1毫米,由于大陆的平均高度为623米,所有的陆地也应该早就消失了。再者,过去的气候更潮湿,我们现在测量到的侵蚀速度应该比过去慢。
山脉
对于古老的山脉来说,进化论者面对的问题更尖锐。一般地,山区由于坡陡沟深,侵蚀的速度最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墨西哥和喜马拉雅山区,典型的侵蚀速度是每一千年1米114。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座火山上,侵蚀速度曾经高达每一千年19米115。
平原
对于一些所谓的古老平原,存在一个相反的问题。这些平原覆盖很大的面积,但看起来却像是全新的。难以相信平原可以存在亿万年的时间而看不见任何被侵蚀的迹象,也看不出平原上边曾被别的地层覆盖的迹象。例如,南澳大利亚的袋鼠岛有大约140公里长,60公里宽,非常平坦。但根据所含的化石和放射性定年法,它却被“鉴定”为1.6亿年116。在1.6亿年的时间里暴露在风雨中,地表应该形成一些沟壑,但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沟壑。
罗斯的回应:
罗斯试图回应这个论证,但只是谈到大陆的侵蚀,而没有提到山脉和平原的问题。他写道(C&T104):
“这个论证只看到等式的一边。问题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熔岩流、三角洲和大陆架的形成(由侵蚀的泥沙形成)、珊瑚礁的形成、以及板块碰撞产生的地壳上升在以大致相同的速度发生,有的时候甚至会远高于侵蚀的速度。例如,喜马拉雅山的高度正在以每年9毫米的速度增加,这是地壳上升的结果。自夏威夷1959年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以来,熔岩流已经给它增加了几个平方英里的面积。”
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用上升来平衡侵蚀,意味着在25亿年的时间里,山脉应该被侵蚀然后又生成了许多次。如果真是这样,在山区应该找不到古老的沉积层,因为它们已经被侵蚀掉然后重新形成许多次了。然而,很稀奇的是,从年轻到古老的、不同年龄的(根据进化论的定年法)沉积层在山区都存在。尽管相信古老地球论的地质学家们不顾“常理”地坚持这些年龄,所谓的古老侵蚀面对常规的定年法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著名的地貌学家推戴尔( C. Rowl Twidale)写道:
“如果现代地貌的某些部分确实如实地考察的证据所显示的那么古老,那么它们不仅否定了常识和日常观察,而且对普遍的理论也有重大影响。”117
创造论气象学家麦克尔∙奥尔德(Michael Oard)写了一篇对推戴尔论文的回应,交给同一家期刊,但不出意料地被回绝了,就是因为它挑战年老地球/进化论的范式。118
总结
这一章不是要用科学来“证明”圣经的时间尺度。事实上,所有关于事物年龄的科学论证都只能是尝试性的。本章的要点在于,即使接受均变论的假设,也有许多物理过程指向一个“年轻的年龄”。所以,这是把进化论者的武器拿来对付他们自己。当罗斯试图反驳这些“地球年轻”的论证时,他忽略了其最细致、最新的阐述,或者歪曲之。
参考与注释
- 例如,耶稣在《马太福音》12:27对法利赛人的回应,“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祂是说如果祂的对手的假设是对的,这会反弹他们自己。进一步的讨论请参考J. Sarfati, “Loving God with All Your Mind: Logic and Creation”, J.Creation 12(2)142–151 (1998); creation.com/logic.
- 也参考G. Koukl, “Arguments That Commit Suicide, Stand to Reason”, www.str.org, July/August 2001.
- 鉴于日常重复的经验,他们对均变的相信并非无理,但哲学上这不是一个牢固的根基。二十世纪领军的逻辑学家伯特兰•罗素提到一只面对感恩节的火鸡安慰自己说,因为到现在为止它的头都还没有被砍掉,所以可以安全地假定这永远不会发生。
- J. Sarfati,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Evidence That the Earth Is Young”, Creation 20(2):15–19 (March– May 1998); creation.com/magfield.
- “The Earth: Its Properties,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7:600, 15th ed., 1992.
- “居里点”,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3:800, 15th ed., 1992, 以皮埃尔•居里(1859-1906)命名。他后来与夫人玛丽一起因对放射性的研究工作获得诺贝尔奖。
- 这是因为电阻的存在。电子在流动过程中与原子碰撞,开始随机运动,不再形成电流。在超导体里,电阻为零,所以电流可以无限保持。但是超导是一个低温现象,从来没有在接近地核温度的条件下被观察到。
- 参见 A. Lamont, 21 Great Scientists who Believed the Bible (Australia: Cre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1995), p. 88–97.
- 这是楞次定律(H.F.E. Lenz,1804-1864)的效果,即感应电流的方向与感应源的方向相反。在这里,感应源是衰减的电流,所以感应电流的方向是要减慢衰减。
- 衰减是指数性的,一个起始电流为I,电阻为R,电感为L的简单电路,在t时间的电流为i = Ie-t/τ, 其中是时间常数L/R,即电流衰减为起始值的1/e (~37%)所需要的时间。对一个半径为a,电导率为τ,磁导率为μ 的球体,τ = σ μ a2π
- A. Lamont, 21 Great Scientists who Believed the Bible (Australia: Creation Science Foundation, 1995), p. 132–141.
- 技术上更具体地讲,“主要部分”是磁场的“偶极子”(两极,北极和南极)部分,占观察到的磁场的90%以上。偶极子部分磁场的产生源称为“偶记矩”,其强度在以每世纪5%的比率衰减。磁场剩下的10%请参考下面标题为【地磁场的多极子部分】的小节。
- K.L. McDonald and R.H. Gunst, “An Analysis of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from 1835 to 1965”, ESSA Technical Report, IER 46-IES 1,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67.
- R.T. Merrill and M.W. McElhinney,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3), p. 101–106.
- T.G. Barnes, Foundations of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 3rd edition (El Paso, TX: Barnes, 1977).
- F.D. Stacey, “Electrical Resistivity of the Earth’s Cor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3:204–206 (1967).
- 海底电流测量结果成为最流行的发电机模型的难题。— L.J. Lanzerotti et al., “Measurements of the Large-scale Direct-current Earth Potential and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the Geomagnetic Dynamo”, Science 229:47–49 (July 5, 1986)。另外,实测的磁场衰减率足以产生现在磁场强度所需要的电流,意思是没有证据支持一个现在正在工作的自维持发电机,即使曾经有过。
- G.A. Glatzmaier and P.H. Roberts, “A Three-Dimensional Convective Dynamo Solution with Rotating and Finitely Conducting Inner Core and Mantle”, Phys. Earth Planet. Inter. 91:63–75 (1995).
- G.A. Glatzmaier and P.H. Roberts, “A Three-Dimensional Self-Consistent Computer Simulation of a Geomagnetic Field Reversal”, Nature 377:203-209 (1995).
- R. Humphreys, “Can Evolutionists Now Explain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CRSQ 33(3):184–185 (December 1996).
- FoG:156; 重复出现在 H. Ross, “Biblical Evidence for Long Creation Days”, www.reasons.org, December 2, 2002.
- R. Humphreys, “Reversals of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During the Genesis Flood”, in R.E. Walsh et al.,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2:113–126 (1986). 运动的导电液体会带动磁力线,这会激发新的电流,产生新的相反方向的磁通量。也参见对他的访谈,记录在Creation 15(3):20–23 (1993).
- J. Baumgardner, papers in “Forum on Catastrophic Plate Tectonics”, J.Creation 16(1):57–85 (2002); creation. com/cpt_forum.
- R. Humphreys, discussion of J. Baumgardner,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Large-scale Tectonic Changes Accompanying the Flood”, in R.E. Walsh et al.,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2:29 (1986).
- R.S. Coe and M. Prévot, “Evidence Suggesting Extremely Rapid Field Variation During a Geomagnetic Reversal”,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92(3/4):292–298 (April 1989). See also the reports by Ph.D. geologist Andrew Snelling, Creation 13(3):46–50, 13(4):44–48 (1991).
- R.S. Coe, M. Prévot, and P. Camps, “New Evidence for Extraordinarily Rapid Change of the Geomagnetic Field During a Reversal”, Nature 374(6564):687–692 (1995); see also A. Snelling, J.Creation 9(2):138–139 (1995).
- See note 10. 参注10.
- R. Ecker, Dictionary of Science and Creationism (Buffalo, NY: Prometheus Books, 1990), p. 105.
- J. Sarfati,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Evidence That the Earth Is Young”, Creation 20(2):15–19 (March– May 1998); creation.com/magfield.
- R. Humphreys, “Physical Mechanism for Reversals of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During the Flood”, in R.E. Walsh and C.L. Brooks,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2:129–142 (1990).
- Barraclough, Geophy. J. Roy. Astr. Soc. 43:645–659 (1975).
- R. Humphreys,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Is Young”, Impact 242 (August 1993); www.icr.org/article/ earths-magnetic-field-young/.
- R. Humphreys,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Is Still Losing Energy”, CRSQ 39(1)1–11 (March 2002); www. creationresearch.org/crsq/articles/39/39_1/GeoMag.htm.
- 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提出引力坍缩是太阳的能量来源。这能持续的时间远远达不到数十亿年。不过,标准物理证明太阳的核心温度足以使核聚变发生,而且产生的中微子已经被我们探测到。但中微子数量不足,所以以前曾提议太阳2/3的能量来自引力坍缩。这样说的一个前提,是当时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假定中微子的静止质量为零,不会振荡。不过,现在似乎有决定性的证据表明中微子可以振荡,那么标准的粒子模型就错了。参见J. Lisle, “Missing Neutrinos Found! No Longer an ‘Age’ Indicator”, J.Creation 16(3):123–125 (2002).
- 四个氢原子(原子量为1.008)转化成一个氦原子(原子量为4.0039)损失0.0281个原子质量单位(1 AMU = 1.66 x 10–27 kg),释放出4.2 x 10–12 焦耳的能量。
- R.V. Gentry, G.L. Glish, and E.H. McBay, “Differential Helium Retention in Zircons: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Waste Containment”,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9(10):1129–30 (October 1982). See also Gentry’s book: Creation’s Tiny Mystery, 3rd edition (Knoxville TN: Earth Science Associates, 1992), p. 169–170, 263–264.
- R. Humphreys, “Nuclear Decay: Evidence for a Young World”, Impact 352 (October 2002); see also creation. com/helium-evidence-for-a-young-world-continues-to-confound-critics, 29 November 2008. D.R. Humphreys, S.A. Austin, J.R. Baumgardner, and A.A. Snelling, “Helium Diffusion Rates Support Accelerated Nuclear Decay”, in R.L. Ivey Jr., editor,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p. 175–196,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August, 2003); www.icr.org/article/helium-diffusion- nuclear-decay/.
- RTB对RATE项目的批评,“信仰的理由”广播电台,2003年9月18日,太平洋时间晚6点到8点。主持人:Krista Bontrager; 现场参与人: 罗斯,拉那(Fazale Rana), 和 哈门(Marg Harmon); 电话接入: 罗杰•威恩斯(Roger Wiens)。
- 也参见 L. Vardiman, “Ross Criticizes RATE without Doing His Homework”, creation.com/ross-criticizes- rate-without-doing-his-homework, October 2, 2003. R. Humphreys, creation.com/helium-evidence-for-a-young-world-continues-to-confound-critics.
- J. Sarfati, “Salty Seas: Evidence for a Young Earth”, Creation 21(1):16–17 (December 1998–February 1999); creation.com/salty.
- E. Halley, “A Short Account of the Cause of the Saltness [sic] of the Ocean, and of the Several Lakes That Emit No Rivers; with a Proposal, by Help Thereof, to Discov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9:296–300 (1715); cited in S.A. Austin and D.R. Humphreys, “The Sea’s Missing Salt: A Dilemma for Evolutionists”, in R.E. Walsh and C.L. Brooks,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Vol. II, p. 17–33 (1990).
- J. Joly, “An Estimate of the Geological Age of the Earth”, Scientific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Dublin Society, New Series, 7(3) (1899); reprinted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June 30, 1899), p. 247– 288; cited in S.A. Austin and D.R. Humphreys, “The Sea’s Missing Salt: A Dilemma for Evolutionists”, in R.E. Walsh and C.L. Brooks,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Vol. II, p. 17–33 (1990).
- S.A. Austin and D.R. Humphreys, “The Sea’s Missing Salt: A Dilemma for Evolutionists”, in R.E. Walsh and C.L. Brooks,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Vol. II, p. 17–33 (1990). 因篇幅的限制,如果需要更多细节,请参考这篇论文。
- W.S. Moore”,Large Groundwater Inputs to Coastal Waters Revealed by 226Ra Enrichments”, Nature 380(6575):612–614 (April 18, 1996); perspective by T.M. Church, “An Underground Route for the Water Cycle”, same issue, p. 579–580.
- 同上,580页,Church评论到,“有大量SGWD进入近海的结论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海洋化学质量平衡的理解。”
- From J. Sarfati, “Exploding Stars Point to a Young Universe: Where Are All the Supernova Remnants?” Creation 19(3):46–48 (June–August 1997); creation.com/SNR. This is based on a paper by K. Davies, “Distribution of Supernova Remnants in the Galaxy”, in R.E. Walsh, 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1994): p. 175–184. See also Davies, K., The Cygnus Loop—a case study, J. Creation 20(3):92-94, 2006.
- See the article “Supernov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1:401, 5th edition (1992).
- K. Davies, “Distribution of Supernova Remnants in the Galaxy”, in R.E. Walsh, 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1994) has detailed observational limitation formulae.
- “绝热”意思是“与外界没有热交换。”在第二期里,SNR几乎没有热量损失。
- “恒温”意思是“温度保持不变”。在第三期,SNR应该保持在同一个温度,把多余的热量辐射出去。
- 超新星爆炸的能量和星际空间里的氢原子数量之比。
- D.H. Clark and J.L. Caswell, “A Study of Galactic Supernova Remnants, Based on Molonglo–Parkes Observational Data”,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174:267–306 (1976).
- D=SNR直径,N(D)=直径小于D的SNR数量。
- 这与第五章里讨论的拉塞尔•汉弗莱斯白洞宇宙学是符合的。他在这里有解释: creation.com/spiral 。
- J. Sarfati, “Comets: Portents of Doom or Indicators of Youth?” Creation 25(3):36–40 (June–August 2003).
- Frank Whipple的模型,例如,F.L. Whipple, “Background of Modern Comet Theory”, Nature 263:15 (September 2, 1976). 他更正式的表述是“脏冰彗核”。 G. Kuiper, “Present Status of the Icy Conglomerate Model”, in J. Klinger, D. Benest, A. Dollfus, and R. Smoluchowski, editors, Ices in the Solar System (Dordrecht, 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1984), p. 343–366.
- C. Wieland, “Halley’s Comet: Beacon of Creation”, Creation 8(2):6–10 (March 1986); creation.com/halley. The most thorough article is D. Faulkner, “Comets and the Age of the Solar System”, J.Creation 11(3):264–273 (1997); creation.com/comet.
- 这是出自开普勒的行星运行第三定律,a3 = p2,a是以AU为单位的轨迹半长轴,p是以年为单位的周期。
- C. Sagan and A. Druyan, Comets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85), p. 175.
- S.A. Stern and P.R. Weissman, “Rapid Collisional Evolution of Comets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Oort Cloud”, Nature 409(6820):589–591 (2001). D. Faulkner, “More Problems for the ‘Oort Comet Cloud,’ ” J.Creation 15(2):11 (2001); creation.com/oort.
- M.E. Bailey, “Where Have All the Comets Gone?” Science 296(5576):2251–2253 (June 21, 2002), perspective on Levison, following footnote.
- H.F. Levison et al., “The Mass Disruption of Oort Cloud Comets”, Science 296(5576):2212–2215 (June 21, 2002).
- J.M. Parker, editor, Distant EKOs: The Kuiper Belt Electronic Newsletter 27 (January 2003); www.boulder.swri. edu/ekonews/issues/past/n027/html/index.html.
- “夸欧尔”这个名字来自通瓦人( San Gabrielino的印地安人)的创世神话。 夸欧尔是在2002年6月被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大学的楚基罗(Chad Trujillo) 和 布郎(Mike Brown)发现的。
- J. Lisle, “The Short-period Comets ‘Problem’ (for Evolutionists): Have Recent ‘Kuiper Belt’ Discoveries Solved the Evolutionary/Long-age Dilemma?” J.Creation 16(2):15–17 (2002); creation.com/kuiper.
- D. Faulkner, “The Dubious Apologetics of Hugh Ross”, J.Creation 13(2):52–60 (1999); creation.com/ross_apol. 福柯纳博士写信之后,过了几年,罗斯在他的广播节目里采访了他。罗斯的网站上引用了几篇关于奥尔特星云和柯伊伯带的论文。
- D. DeYoung, “The Earth-Moon System”, in R.E. Walsh and C.L. Brooks,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2:79–84 (1990); J. Sarfati, “The Moon: The Light That Rules the Night”, Creation 20(4):36–39 (September–November 1998); creation.com/moon.
- 角动量=mvr,是质量、速度和距离的积, 在一个孤立系统里是守恒的(不变的)。
- 这是因为潮汐力是与距离的三次方成反比的。所以月球远去速度dR/dt = k/R6,其中k是个常数,等于(目前速度:0.04m/年)x(目前距离:384,400,000m)6=1.29x1050m7 /年。
- 对前注的微分方程积分可以得到从Ri 到Rf 的时间为t = 1/ 7k(Rf 7 - Ri 7)。对Rf =目前距离,Ri =洛希极限,t=1.37 x 109 年。如果Ri = 0, 地球和月球是挨着的,结果也差不多,因为当月亮很近时,远去速度非常高(潮汐作用非常大)。
- K.J. Krelove, The Earth-Moon Tidal System, Marine Geology honors paper,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May 2000; www.personal.psu.edu/users/k/j/kjk176/Earth-Moon.htm, accessed December 12, 2002.
- C.P. Sonett, E.P. Kvale, A. Zakharian, M.A. Chan, and T.M. Demko, “Late Proterozoic and Paleozoic Tides, Retreat of the Moon, and Rotation of the Earth”, Science 273:100–104 (1996).
- 参见注70。
- 同上。
- C. Wieland, “Sensational Dinosaur Blood Report!” Creation 19(4):42–43 (September–November 1997); creation.com/dino_blood, based on research by M. Schweitzer and T. Staedter, “The Real Jurassic Park”, Earth (June 1997): p. 55–57.
- M. Schweitzer and T. Staedter, “The Real Jurassic Park”, Earth (June 1997): p. 55–57.
- M. Schweitzer, Montana State University Museum of the Rockies, cited on p. 160 of V. Morell, “Dino DNA: The Hunt and the Hype”, Science 261(5118):160–162 (July 9, 1993).
- 参见注75。
- H.M. Schweitzer et al., “Heme Compounds in Dinosaur Trabecular Bone”, PNAS 94:6291–6296 (June 1997); www.pnas.org/cgi/reprint/94/12/6291.pdf.
- 施韦策给J. DeBaum的信, 2002.
- C. Wieland, “Evolutionist Questions CMI Report: Have Red Blood Cells Really Been Found in T. rex Fossils?” creation.com/RBC (March 25, 2002). See also “Schweitzer’s Dangerous Discovery”, creation.com/schweit, 19 July 2006.
- Muyzer et al., Geology 20:871–874 (1992).
- Christina Nielsen-Marsh, Biomolecules in fossil remains: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endurance, The Biochemist 24(3):12–14, June 2002; www.biochemist.org/bio/02403/0012/024030012.pdf.; Shaun Doyle, The Real Jurassic Park, Creation 30(3):12–15, 2008; creation.com/real-jurassic-park.
- Golenberg, E.M., et al., Chloroplast DNA sequence from a Miocene Magnolia species, Nature 344:656–658, 12 April 1990; commentary by Karl J. Niklas, Turning over an old leaf, same issue, p. 587.
- Wieland, C., ‘Oldest’ DNA—an exciting find! Creation 13(2):22–23, 1991; creation.com/oldestdna.
- 如一位古老地球进化论者、拉筹伯大学(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遗传学研究员凯尔(Benjamin Kear )所说:“问题是,当我们讨论古代的DNA时,一般是指最多几千年。DNA非常非常快就变质了。……” ABC国家电台的“科学秀”,2009年12月5日首次播出,www.abc.net.au.
- Bidle, K.D. et al., Fossil genes and microbes in the oldest ice on Eart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33):13455–13460, 2007.
- Catchpoole, D., ‘Sleeping Beauty’ bacteria, Creation 28(1):23, 2005; creation.com/sleeping. See also Catchpoole, D., More ‘Sleeping Beauty’ bacteria, creation.com/moresleep.
- Greenblatt, C.L. et al., Diversity of microorganisms isolated from amber, Microbial Ecology 38:58–68, 1999.
- Catchpoole, D., Amber needed water (and lots of it), Creation 31(2):20–22, 2009.
- Vreeland, R.H., Rosenzweig, W.D., Powers, D.W., Isolation of a 250 million-year-old halotolerant bacterium from a primary salt crystal, Nature 407(6806):897–900, 2000.
- Salty saga, Creation 23(4):15, 2001; creation.com/saltysaga.
- Snelling, A. A., ‘165 million year’ surprise, Creation 19(2):14–17, March–May 1997; creation.com/ ligaments165ma.
- Nuttall, N., Mud springs a surprise after 165 million years, The Times, London, p. 7, 2 May 1996.
- McNamara, M. et al., Organic preservation of fossil musculature with ultracellular detail,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14 October 2009 | doi: 10.1098/rspb.2009.1378.
- ‘Ancient muscle tissue extracted from 18 million year old fossil’, www.physorg.com, 5 November 2009.
- Wieland, C., Best ever find of soft tissue (muscle and blood) in a fossil, creation.com/muscle-and-blood-in- fossil, 11 November 2009.
- 英国地质调查局的魏尔比(Phil Wilby)博士,引用于“发现侏罗纪时代的乌贼墨汁”,BBC新闻,news.bc.co.uk/2/hi/uk_news/england/wiltshire/8208838.stm, 2009年8月19日。
- Wieland, C., Fossil squid ink that still writes! creation.com/fossil-squid-ink, 15 September 2009; Creation 32(1):9, 2010.
- M. Armitage, “Internal Radiohalos in a Diamond”, J.Creation 9(1):93–101 (1995).
- R.V. Gentry, Creation’s Tiny Mystery (Knoxville, TN: Earth Science Associates, 1988), p. 278.
- R.V. Gentry, “Radioactive Halos”, Annual Review of Nuclear Science 23:347–362 (1973). R.V. Gentry, “Spectacle Halos”, Nature 258:269–270 (1975). R.V. Gentry, “Radiohalos in a Radiochronological and Cosmological Perspective”, Science 184:62–66 (1974). R.V. Gentry et al., “Radiohalos in Coalified Wood: New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Time of Uranium Introduction and Coalification”, Science 194:315–318 (1976).
- R.V. Gentry, Creation’s Tiny Mystery (Knoxville, TN: Earth Science Associates, 1988).
- J.R. Wakefi “Gentry’s Tiny Mystery — Unsupported by Geology”, Creation/Evolution XXII:13–33 (1988).
- See Gentry, Creation’s Tiny Mystery, second edition, which replies to Wakefield.
- A.L. Odom and W.J. Rink, “Giant Radiation-induced Color Halos in Quartz: Solution to a Riddle”, Science 246:107–109 (1989).
- M. Armitage, “New Record of Polonium Radiohalos, Stone Mountain Granite, Georgia”, J.Creation15(1):82–84 (2001). T. Walker, “New Radiohalo Find Challenges Primordial Granite Claim”, J.Creation 15(1):14–16 (2001) [perspective on Armitage, previous footnote].
- A. Snelling, “Polonium Radiohalos: The Model for Their Formation Tested and Verified”, ICR Impact 386 (August 2005); www.icr.org/article/polonium-radiohalos-model-for-their-formation-test/.
- A. Snelling, “Radiohalos — Significant and Exciting Research Results”, ICR Impact 353 (November 2002); www.icr.org/.
- A recent popular-level article is S. Taylor, A. McIntosh, and T. Walker, “The Collapse of ‘Geologic Time’: Tiny Halos in Coalified Wood Tell a Story That Demolishes ‘Long Ages,’ ” Creation 23(4):30–34 (September– November 2001); creation.com/radiohalo. R.V. Gentry et al., “Radiohalos in Coalified Wood: New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Time of Uranium Introduction and Coalification”, Science 194:315–318 (1976).
- T. Walker, “Eroding Ages”, Creation 22(2):18–21 (March–May 2000); creation.com/erosion.
- Ariel Roth,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1998), p. 271, quotes Dott and Batten, Evolution of the Earth (New York: McGraw-Hill, 1988), p. 155, and a number of others.
- From Ariel Roth,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1998), p. 264.
- Ariel Roth,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1998), p. 266.
- C.D. Ollier and M.J.F. Brown, “Erosion of a Young Volcano in New Guinea”, Zeitschrift für Geomorphologie 15:12–28 (1971), cited by Ariel Roth, Origins: Linking Science and Scripture (Hagerstown, MD: Review and Herald Publishing, 1998), p. 272.
- 参见注112.
- C.R. Twidale, “Antiquity of Landforms: An ‘Extremely Unlikely’ Concept Vindicated”, Australian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s 45:657–668 (1998).
- M. Oard, “Antiquity of Landforms: Objective Evidence That Dating Methods Are Wrong”, J.Creation14(1):35–39 (2000)
过去数十年间不断涌现新证据,把人类恢复到神造的宇宙的中心。天文学家已经确认星系红移的数值是“量子化的”,倾向于落入分离的小组。根据哈勃定律,星系红移的大小与该星系到我们(银河系【星河】)的距离成正比。因此,星系离我们的距离也会分成小组。这意味着所有的星系倾向于组成以我们的家乡星系(银河系)为中心的球状壳。这些球状壳之间的距离是一百万光年的量级。只有在观测位置与宇宙中心的距离小于一百万光年的情况下才能观测到清晰的红移分组现象。地球处于宇宙中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的几率小于一万亿分之一。由于大爆炸理论者预先假设宇宙有一个自然主义的开端,不可能有一个独特的中心,所以他们一直为这个现象苦苦地寻求其它解释,至今尚无明显进展。这样看来,红移的量子化成为以下观点的佐证:(1)反对大爆炸理论,(2)支持“河心说”(以银河系【星河】为中心的宇宙学),就像金特立(罗伯特•金特立Robert Gentry)在一本书或我本人在《星光与时间》中所提出的。
1. 介绍
 图1:NGC4414是一个典型的漩涡状星系。 距离我们大概六千万光年(60百万光年),直径约十万光年,包含了数千亿颗恒星,跟我们银河系比较相似。这个漩涡星系跟M31仙女座星系很相似。仙女座星系是位于北半球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星系,距离我们约2百万光年。
|
施礼佛(维斯托•斯里弗Vesto Slipher)并不知道他正在发起一场反哥白尼的革命。大约一百年前在洛威尔天文台(Lowell Observatory),施礼佛开始研究夜空中一些模糊的椭圆型物体的光线波长,这些物体当时被称为白色星云(white nebulae,nebulae是拉丁文的“云”)。现在我们把这些白色星云成为“星系”(galaxies,即希腊语的“乳白色”)。他能观察到的最大最亮的星云叫M31,位于仙女座(Andromeda)。图1展示了一个类似的星系。像以前的天文学家一样,1 施礼佛发现M31的波长谱线类似恒星的光谱,都包含了由氢(图表2)、钙和其他元素原子所发出的特征谱线。
施礼佛找到了一种方法,能拍摄出比以往更加清晰的光谱图像。借助这种方法,他能够更加精确地测量光谱线中的波长。他发现来自M31的光波波长都比它们的正常值减少了0.1%。2 也就是说,谱线向整段光谱的蓝端轻微移动了一些。天文学家也开始对其他星云波长的变化现象进行了研究测量,到1925年为止,他们一共测量了45个星云。3 结果有从-0.1%到+0.6%,平均值为+0.2%。正值反映了波长的增加,也就是说,(谱线)朝光谱的红端移动,关于这点,图2中已经有所说明,这就是我在上文中我们谈及的红移现象,这是本文的一个主题。
2. 哈勃定律
 图2. 理想化的星系光谱呈现的典型“吸收线”(在七色彩虹背景上的黑色线),这是由氢原子吸收光线后产生的。星系距离我们越远,其黑色线向光谱红色端的位移值就越大(对数比例)。
|
在1924年左右,大多数天文学家已经认为那些“白色星云”位于银河系之外。哈勃(爱德温•哈勃Edwin Hubble)在威尔逊山天文台(Mount Wilson Observatory)开始应用一种更准确的新方法,采用100英寸反射天文望远镜来计算这些“河外星云”的距离。在完成之后,他开始印证了 “星云越远,红移越大”这一普遍看法。在1929年,他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4 如图3的归纳)。在图中的趋势线说明了光谱线的波长λ,和其位移值δλ,跟各个(河外)星云与地球的距离r的比例关系:
 (1)
(1)
这里的c 代表光速,大约每秒30万公里,H 是我们现在所称呼的哈勃常数。这就是著名的哈勃定律,该定律说明了某些宇宙现象引起红移,红移值随我们跟星系的距离增加而成比例地扩大。
哈勃的距离计算给我们的宇宙观念带来了一场革命。后来人们发现“白色星云”类似于我们银河系,每个这样的星系由几千亿颗恒星组成,其直径约有十万光年。天文学家开始称这些物体为“星系”。平均来说,每个星系彼此相隔至少1200万光年(12百万光年)。目前哈勃天文望远镜能观察到150亿光年(15十亿光年)范围以内的宇宙空间,而在这150亿光年的宇宙空间中能观察到数千亿个这些的星系。
3. 膨胀红移,不是多普勒位移
哈勃随从施礼佛等人,把这种波长变化解释为多普勒位移(Doppler Shifts),完全产生于光源相对于地球的速度v。这样,在速度v远远小于光速c的情况下,波长位移可以近似地表述为:
 (2)
(2)
因此,根据公式(1),在图3中的趋势线将对应星系飞离我们的速度v与他们和我们之间的距离r成正比关系:
 (3)
(3)
然而其它因素也可以引起红移。比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指出:在一个膨胀的空间里,随着光线在其中被传播的介质被拉伸,光线的波长也会被拉长。光源越远,波长被拉伸得越大。所以红移会随距离增加。
今天,大多数的宇宙学家都相信图3和图4中的趋势线代表这样一种膨胀红移(expansion redshift),而不是多普勒位移5,6。然而,天文学家仍然为了方便起见使用“等价速度”(equivalent velocity)来描述红移,似乎它们是由多普勒位移引起的。不幸的是,这种做法误导了公众和媒体,甚至连天文学专业的本科生也会错误地认为这种红移主要是由速度引起的。
图4使用更多的最新数据展示了在超大距离范围上的红移与距离之间的关系7。趋势线上的偏差不是由膨胀所引起,而是由其他现象引起,如多普勒效应。举例而言,仙女座的M31星系似乎正以100公里/秒8的“当地”速度向我们的银河系【星河】移动,产生了一个多普勒蓝移,大于我们期待这个近邻星系的膨胀红移,因为它离我们仅2百万光年之遥。
多年来,理论学家对宇宙红移的倾向给出了其它的多种解释9, 10, 11, 12, 13, 14。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我研究了这些理论,但没有找到一个令我满意的。但是,在我注意到圣经的经文似乎支持空间膨胀之后,我对其他的红移模型就再也没有兴趣了。以赛亚书40:22是一个范例:
“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
圣经旧约中有十七段类似的经文15,用了四个不同的希伯来语动词来表达“铺张”或者“扩展”的意思。正如我在《星光与时间》16 一书所说明的,圣经中的“天”似乎是指空间本身,并不是指占据空间的物体,比如太阳、月亮和星星。所以如果我们直接接受这些经文,那么神是在说祂已经把空间的“布料”(fabric,代表质地、结构)铺张开或者扩展开。这跟广义相对论的空间膨胀思想非常吻合。通过几个简单的逻辑步骤,教科书中都展示出因膨胀而产生红移。17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膨胀是红移的主要原因。
无论什么原因,本文中所有谈及的星系红移都是大约与其距离成正比的,正如哈勃定律在等式(1)所示。
4. 提夫特(Tifft)观察到量子化的红移
天文学家经常将红移值——波长变化的比例——用一个无量纲的数字z来表示:
 (4)
(4)
星系的z值在原始数据中没有显现任何“优选值”(favored values)。然而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亚里桑那州图桑市(Tucson, AZ)的斯图尔德天文台(Steward Observatory)开始将这些原始数据转换成“功率谱”(power spectra),显示出这些数据之间多么经常地产生间隔。这种标准统计技术显示出平时难以观测到的规律,可以看见峰值在一些点超过噪声。在这种情况下,噪声的一个来源是 “局部”或“特别”的星系运动18。 提夫特惊奇地发现这些强峰值对应z值的间隔为0.00024,或0.024%。这意味着z值倾向于簇集在优选值附近,而优选值之间有相等的间隔,比如:
0.00000, 0.00024, 0.00048, 0.00072, 0.00096, …
如果用多普勒位移的术语来表述(如今的天文学家们经常如此),间隔值δz = 0.00024等同于“等价速度”的间隔值δv = 72公里/秒。19 后来,提夫特又发现另一个间隔值比较小的集组模式,大约36公里/秒。后续的观察和文献都继续支持这种现象。在1984年,提夫特跟他的同事寇克(W. J. Cocke)一起查验了1981年塔利-费舍尔(Talley-Fisher)对于光谱中无线电波(非可见光)部分的红移的普查结果。这份结果列示了星系中氢原子发出的显著的21厘米波长的红移状况。提夫特和寇克发现了“明显的周期性”,是在72.45公里/秒的精确乘数(1/3和1/2),20 于是他们声明:
“现在有非常肯定的证据表明:星系的红移是量子化的,其主要间隔是72公里/秒。” 21
然而,在随后十年里一直有人怀疑他们的的结论,尽管提夫特不断地在同行评审的刊物中发表文章,填补他的漏洞。22 , 23 后来在1997年,一个由衲毗叶(威廉•衲毗叶William Napier)和戈思锐(布鲁斯•戈思锐Bruce Guthrie)主持的对250个星系的红移状况的独立研究肯定了提夫特的基本观察结果,他们说:
“红移的分布在以银河系【星河】为中心(galactocentric)的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中有明显的量子化现象。这一现象显而易见,不能归因于统计误差、挑选过程或者是错误的数据处理。已经发现了两个以银河系【星河】为中心的周期。一个是大约71.5公里/秒,在室女座星团(Virgo cluster);还有一个是大约37.5公里/秒, 在其他一切的在2600公里/秒(大概一亿光年)之内的涡旋状星系。目前这些研究结果都被高度肯定。” 24
“河心参照系”(galactocentric frame of reference)指的是以我们的银河系【星河】为中心的一个静态框架,补偿了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以及太阳系围绕银河系【星河】的中心旋转的因素,这样显示了更加清晰的量子化。在本文第七部分,我会进一步阐明“河心”(galactocentric)在参照系之外的意思。
衲毗叶和戈思锐的结果表明量子化至少会出现到中等距离,大即约一亿光年的量级。其他证据,如哈勃天文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显示出甚至在数十亿光年的距离上也存在类似的红移集组现象。25
 图5.哈勃定律将红移的集组转换为距离的集组。数据是理想化的,只演示一个观察到的组间间隔。
|
在1996年,提夫特展示了通过考虑银河系相对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运动进一步补偿“河心系”红移的重要性。26 ,27 微波的多普勒位移显示出我们的银河系正在以560公里/秒的速度向长蛇座(Hydra)的南边移动。28 计入这种运动把“河心系红移”转换到一个相对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静态的参照系里,因此可以被假设为对整个宇宙都是静态的。在这一参照系中红移的集组就更加清晰分立。于是一些强度较小的周期成为可见的,比如2.6公里/秒,9.15公里/秒和18.3公里/秒。
或许由于这种(数据的)清晰,或许由于来自其他天文学家研究的验证,批评者似乎已经不再质疑研究数据的可靠性了。似乎红移的量子化——这一现象,而不是解释它的理论——已经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同行评审之后站住脚了。
5. 对(红移)量子化的一个简单解释
在这一部分和下一部分,我打算阐述以下问题:(a) 红移的分组对应距离的分组, (b)距离分组意味着星系处于以我们为中心的球状壳上,而且 (c)这样的分布并非偶然。如果你想跳过一些数学细节,就只需看图5到图8,还有我在等式14后面对分析结果的讨论。
 图6. 星系趋向于分布在以我们的家乡星系(银河系【星河】)为中心的球状壳上。球壳的间距是大约一百万光年的量级,但是由于存在几个不同的间隔,真实情况要比上面的理性化的图片更复杂一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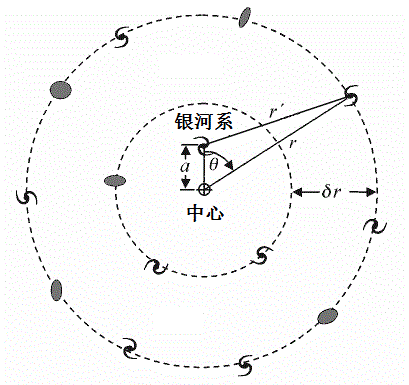
图7.在第六部分使用的坐标系统。距离r′独立于远处星系的相对于位移轴的方位角(azimuth)ƒ。如果我们的星系远离中心,从我们的位置看到的遥远的星系集组会互相重叠,变成不可辨认。
|
根据哈勃定律,每个星系的红移值的宇宙部分 z 对应一个特定的距离 r ,求解公式(1)可以得到距离:
 (5)
(5)
对红移分组的最简单的解释似乎是所对应的距离也分组,如图5所示。对等式(5)求导数,就得出距离间隔δr与红移间隔δz之间的关系:
 (6)
(6)
如果用 “等价速度”的术语,红移组群的速度间隔δv与距离间隔δr之间的关系是:
 (7)
(7)
哈勃初始估算的哈勃常数H值是大约500【公里/秒】/百万秒差距(1个秒差距【parsecond】等于3.2616光年),但是在天文学家重新校准了距离标尺之后,H值就大幅度减小。数十年前,H值一直浮动在50-100【公里/秒】/百万秒差距之间。在过去十年里,由于采用了更加精确的以空间(观测)为基准的距离测量方法,这个值缩减到70-80【公里/秒】/百万秒差距。29 让我们用以下的值作为一个可行的估算数据:
 (8)
(8)
将百万秒差距转换为我们更熟悉的距离单位之后,H值大致为23±1.5【公里/秒】/百万光年,所以等式7变为:
 (9)
(9)
于是,由衲毗叶和戈思锐提出的两个红移的间隔,37.5和71.5公里/秒,对应于距离间隔1.6和3.1百万光年。
6.距离集组的意义
除了在被银河系【星河】遮挡的方向,天文学家在所有其它的方向都观察到大约同等数量的河外星系。如果某个红移的集组代表一个星系距离的集组,簇集在离我们平均距离r1左右,那么我们可以期待这些星系大约平均分布在一个以我们为中心的半径为r1的(概念上的)球状壳上。第二组的距离是 r2 = r1 + δr,所以这些星系将会在第二个球壳上,与第一个球壳的距离为δr。图6展示了这样一种星系分布。30
现在我要证明: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距离分组的前提是我们的位置与这样一个图案的中心的距离小于100万光年。如图7所示,设想我们的星系与此中心的距离为a。根据余弦定理(law of cosine),从我们的星系到另外一个星系的距离r′可以表述为:
 (10)
(10)
这里r代表另一个星系到中心的距离,而θ则是它的余纬角(colatitude),就是从中心看该星系与位移轴之间的夹角。距离r´独立于这个遥远星系的方位角φ(环绕位移轴,在0-2π弧度之间)。所以尽管缺少第三个坐标,以上分析在三维中仍然有效。当a远远小于r时,等式(10)可以近似为:
 (11)
(11)
因为对于一个星系而言,余纬度θ会在0-π弧度中随意取值,对于任何已知半径是r的球壳,r′的值在r – a到r + a之间变动。如果a太大的话,那么红移的集组就会变成模糊不清,无法分辨。一个简单的统计分析31显示:r′依赖θ的标准偏差σθ是:
 (12)
(12)
一个在任何球状壳中的星系的半径r的值也有统计分布,并有一个标准偏差值σ,代表每个球壳的厚度。因此,根据统计学,32 r´的总标准偏差σ是:
 (13)
(13)
如果σ明显大于球壳之间的距离δr,这些红移的集组就会互相重叠,变得难以分辨。即使在σr为零的情况下,假如σθ值大于δr,这些红移的集组也会变成无法分辨。
图8解释了这种涂抹的情况。它展示了一个计算机模拟的距离的分组,第一张图的观察点是在正中心,而第二张图的观察点是在离中心2百万光年的位置。我选择较小的σ值,使峰值更容易显现。请注意远离中心的结果是低处被填高,而峰值被拉平,导致很难从统计波动中辨认出分组来。
 图8. 计算机模拟的我们的视角对星系的距离组群的影响。(a) 半径的标准偏差是10万光年,半径方向的组间距离是160万光年的模拟图。(b) 从距离中心200万光年的位置进行观察的模拟图。模拟图b中的高低值与各组中星系数量较小时统计波动所产生出来的几乎一样大,所以真正的集组在噪声中难以辨认。
|
这意味着,若要观察到可分辨的红移分组,我们必须靠近这些球状壳的中心位置。根据等式13和其后的解释,我们跟中心的距离a应该远远小于最小的观测到的δr。
 (14)
(14)
因此,我们的家乡星系到中心的距离必须小于在第五部分引用的δr值(1.6百万光年)。使用最小的观察到的间隔33会把我们放在离中心更近之处——相距大约10万光年之内,这正是我们银河系【星河】的直径。
如果我们是碰巧地处在这个独特的位置,其几率P可以由体积的比率得出:
 (15)
(15)
其中R 代表观察到的宇宙的半径,就算200亿光年吧。取δ r 值为1.6百万光年,得出的P 值为5.12 × 10-13。也就是说:我们的星系能碰巧这么靠近宇宙中心的几率将会小于一万亿分之一。
总而言之,观察到的红移量子化强烈地暗示宇宙有一个中心,而我们的星系离这个中心出奇地近!
7. 宇宙是以银河系【星河】为中心的
要命名这个思想,我们需要提高“河心”(galactocentric)这个词的地位,不像在第四部分仅被用于描述一个参照系。让我们用这个词来描述宇宙本身。这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以银河系【星河】为中心的宇宙中——它的独特的几何中心非常靠近我们的家乡星系,即银河系【星河】。
正如我在第四部分结尾所提到的,宇宙微波背景(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的数据显示我们的星系相对于这个宇宙的中心在移动。34我们的星系几乎就在这个宇宙的中心点上,但不是相对它静止不动。这与地心说(geocentrism)有别,后者认为地球位于宇宙的正中心,而且相对它静止不动。35, 36 数位创造论者都提出过“河心说”(galactocentric)的宇宙学。37
天文学的技术性文献几乎完全忽略了“河心说宇宙学”作为一个对红移量子化给出解释的可能性。38 相反,世俗的天文学家似乎更喜欢用一种尚未被解释的影响到光线本身的微观现象来解释,要么是作用于光源的原子,要么是作用于在空间中的传播。提夫特自己积极推广这一解释。他援引一个“三维时间”的新概念,并说:
“红移有来自于微观的量子物理学的印记,但是它把这一印记带到了宇宙的边界”。39
于是,世俗的天文学家逃避这个简单的解释,多数人只字不提其可能性。相反,他们抓住一般被他们蔑视的救命稻草,援引神秘未知的物理学说。我认为他们逃避明显的(解释),是因为“河心论”(galactocentricity)会质疑他们最深层的世界观。这一问题切入大爆炸理论的核心——其自然主义的进化论假设。
8. 大爆炸理论不能接受(宇宙)存在一个中心
很少有人意识到大爆炸宇宙学与他们所构想有多大差别。这个广泛流行却误导人的名字让许多人设想一个小的三维球,有中心、有外沿,向外爆炸到空虚的三维空间里。经历数百万年之后,物质将聚合成恒星和星系。数十亿的星系将组合成“岛”或“群岛”,填充本来是空虚的空间“海洋”。就像公众认为的初始的三维球一样,这样一个(星)岛会有独特的几何中心。而“中心”的定义并不是神秘的,就是字典中的简单解释:
“中心……1.是指一个与周边上或者边界上的所有的点都具有同等距离或处于平均距离的点” 40
许多人,包括众多的科学家甚至天文学家,对大爆炸的设想都是这样。但是宇宙学专家对大爆炸的想法却与此大相径庭!他们反对初始的三维球概念,也反对宇宙岛的理念。在“封闭”大爆炸中(目前最受欢迎的版本),他们设想——纯粹靠类比——我们所能看到的三维空间仅仅是一个四维“气球”的表面,而这个“气球”膨胀进入一个四维的超空间(其中不包含时间维度)。41参看图9。
 图9. 宇宙学家通过类比设想大爆炸是一个膨胀的气球。这一类比把我们看得见的三维空间局限在四维气球的三维表面上。星系就像表面上的微尘,随着气球膨胀而散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星系可以称为是独特的中心。而膨胀真正的中心位于这个气球的内部,是身处气球表面的人所不能察觉的。
|
他们设想众星系就像在气球表面的尘粒(在气球内部不存在星系)。在膨胀过程中,气球胶面(代表空间本身的“布料”【即结构】)向外拉伸。于是尘粒彼此分散。从每颗尘粒的角度来看,其它尘粒在远离自己而去,但没有一颗尘粒是膨胀的独特中心。在气球表面没有中心可言。膨胀的真正中心是在气球内部的空气中,代表“超空间”,超越那些被限制在三维“表面”的生物所能理解的范围。
如果你有困难理解这个类比,可以尝试观看《星光与时间》的视频版本。42由电脑生成的动画帮助许多人理解这个类比,领他们一步一步地认识整个过程。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去看待宇宙学专家们的这个概念。如果你能够在特定方向上作无限快的旅行,这些专家们认为你一定不会进入其中没有星系的大范围空间。你无法定义众星系的边缘或者界线,所以你不能定义一个几何中心。一位宇宙学家这样评述了流行的“宇宙岛”的错误认识,说:
“这是错误的……【大爆炸宇宙】没有中心和边缘。”43
所以大爆炸没有中心。在我们可见的三个空间维度内不存在独特的中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爆炸理论的支持者们会反对任何要求存在一个中心来解释红移量子化的理论。以下我会展示他们这种无中心论(acentricity)44 的主张是源于一个武断的、并非被观察证实的假设。s.
9. 大爆炸的假设
在他们的影响广泛、高度专业化的著作《时空的大尺度结构》中,霍金( 史提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艾利斯(乔治•艾利斯George Ellis)用以下的大致评述介绍了他们关于大爆炸宇宙学的部分。
“然而,我们对宇宙模型的建构是不可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掺合的。在早期宇宙学中,人类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自从哥白尼时代以来,我们不断地退居到一个中等大小的行星上,它围绕着一颗中等大小的恒星运转;这恒星是在一个相当普通的星系的外围,而这星系也仅是本地星系群中的一员。如今我们是如此地民主,以至于我们不会主张我们在空间的位置在任何意义上是特别地显著。我们将沿用邦迪(Bondi)在1960年的说法,把这一假设称为‘哥白尼原理’” 45。【强调是后加的】
这个观点在过去被称为“宇宙学原理”。46, 47 请注意霍金和艾利斯称之为一个“假设”和“意识形态的掺和”——一个不被观察结果要求的假设的概念。而他们的措辞“我们不会主张……”事实上是一个武断的主张,即地球在宇宙中不处于一个特殊位置。他们继续说:
要合理地解释这个模糊不清的原理,就应该这样理解它的含义:当我们用恰当的尺度(scale)去观察时,宇宙基本上是在空间中均匀分布的(spatially homogeneous)。48
“在空间中均匀分布”的意思就是“均匀地扩展到遍及所有的可及的空间(available space)”。霍金和艾利斯是在宣称空间在任何时候都完全充满了质能。他们说:“从来就没有过空虚的大范围的空间,而且永远也不会有”。
他们作了这个信心的跳跃,是因为观察表明宇宙是各向同性的(isotropic),或者说围绕着我们是球状对称的。这意味着从我们的有利位置出发观看各个方向都是相同的结果。一般情况下,霍金和艾利斯会指出,这意味着“我们身处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49——比如说是(宇宙的)中心。但那会跟他们的“地球不处于一个特别的位置”的愿望不吻合,于是他们要寻求一个不那么使他们不安的宇宙理论。
“其中在时空的每个点上宇宙都是各向同性的。所以我们会把哥白尼原理解释为主张宇宙大致在每个点上都是球状对称的(因为在我们周围宇宙大致是球状对称的。)” 49
他们把这样古怪的假设加入到广义相对论的数学体系中之后,结果就推导出各式各样的大爆炸理论。
10. 大爆炸理论的核心是无神论
让我们深究这一假设背后的动机。为什么大爆炸理论家要百般周折地设计一个“地球不在特殊位置”的宇宙学理论呢?天体物理学家高特(理查德•高特Richard Gott)在一篇专门论述哥白尼原理的文章的介绍中揭示了其原因:
“哥白尼革命教导我们:在没有充足理由的前提下假设我们人类在宇宙中身处特权的位置是错误的。达尔文也表明,关于起源,我们并不比其它的物种更优越。我们不过是处在本地星系群(local supercluster)当中的一个普通星系当中的一颗普通恒星的周围;我们的位置看来是继续地越变越不重要。我们并非处于一个独特的空间位置这一思想对于宇宙学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导致大爆炸理论。在天文学中哥白尼原理行得通,是因为有智力的观察者可能存在的地方按定义只有少数特别的位置,却有许多普通的位置,所以你最可能(likely)身处的是一个普通的位置。”50
那个词“最可能”揭示了很多东西。高特显然认为我们身处这个位置是出于偶然(by accident)!他显然根本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就是神,一位智慧的设计者,有意地将我们放置在宇宙中的一个特殊位置。因此,哥白尼原理背后的终极动机是无神论的自然主义。因为这是自然主义进化论背后的支配性哲学思想,所以高特引用达尔文是恰当的。大爆炸理论和达尔文主义是同一个无神论的起源神话的两半,分别覆盖物理学和生物学两个学科。
因此,那些支持大爆炸理论的基督徒应该意识到:他们在不经意间否定了他们的神,并且向无神论的世界观妥协。
11. 宇宙有中心这件事的科学意义
如果神在第四天的创造中使用了一些过程来创造众星和星系,那么红移量子化就见证说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我们的星系是球状对称的。举例而言,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球状震荡波,在一个不断膨胀的气体或等离子体的球内,在其中心和边缘来回震荡,我在《星光与时间》51一书中谈及这样一个尝试性的宇宙模型。这样的震荡波在一定半径上会互相干扰,而在另一些半径上会互相叠加,形成一种“驻波”(standing wave)图案,稠密的气体集中在同心的球状壳上。然后神凝聚这些气体形成众星和星系。最终形成的同心的星系图案会比较复杂,有多种间隙,对应不同的震荡模式。或许重要的是,我们观察到的最主要的球壳间隙δr是3.1百万光年,而星系之间的平均距离是12百万光年,两者是同一量级的。52
驻波暗示着物质有一个外围边缘,可以让震荡波反弹回来。这样其几何中心也成为质心。如果我们把这些边界条件(一个边缘和中心)放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式中,就可以得到我在《星光与时间》一书中所阐述的宇宙模型。其质心是引力中心,强度低但是范围广,遍及整个宇宙。于是,在膨胀的一个特定阶段,引力在中心点造成巨大的时间延缓效应。
因此,红移量子化对我提出的宇宙学模型是观察证据,证明了我在1994年初步提出的观点:
“尤其是,被很多天文学家观察到的星系红移的‘量子化’分布22似乎跟哥白尼原理和所有以此为基础的宇宙学(包括大爆炸理论)相矛盾。但是这一现象已经有了解释,就是通过我提出的非哥白尼的‘白洞’(while hole)宇宙学”。 53
12. 宇宙有中心这件事的属灵意义
对于基督徒,我们位于宇宙的中心这一思想从直觉上是令人满足的。对于世俗主义者,这却会令他们深感不安。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致力于进一步推进哥白尼革命,54 好远离中心说。卡尔•萨根(Carl Sagan)专门写了一本以下这种风格的书来贬低我们(在宇宙中)位置的和我们自己的重要性。
“在浩瀚的宇宙竞技场中,地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舞台…。我们故作的姿态,我们想象的自重,以及我们在宇宙中有特殊位置的妄想,都受到这一点苍白阳光的挑战【一张由旅行者一号拍摄的地球照片】。我们的行星是一颗孤独的微尘,被巨大的全宇宙的黑暗所包围。在我们的无名中,在这一切的浩瀚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来自其它地方的援助,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 55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人类在宇宙里的中心位置这一思想是如此重要,以致于神的仇敌试图避开它。
首先,《圣经》宣称我们的家乡行星(地球)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心位置。创世记1:1首先提到地球,是在创世周第一天,远远早于十几节经文之后在第四天提到太阳、月亮和众星。创世记1:6-10把地球放在宇宙的物质的“中间”,正如我在《星光与时间》中解释的。56 在创世记1:14-15,神说天体存在是为了地上万物的益处。所以,不是人类想象自己“处于宇宙中的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57而是神说我们在那里。能看到(科学)证据再次支持圣经,实在令人振奋。
“好吧,”你可能会说,“为什么 神不把我们放置在我们的星系的正中心呢,这样会令(地球)中心说更具说服力?”。 不过看起来神有更好的想法。首先,我们的太阳在银河系【星河】中的位置是一个很好的设计,让它处在一个理想环境。58,59星系的中心是非常活跃的,存在大量的超新星,或许有巨大的黑洞,会释放强烈的辐射。60然而太阳是在一个近似圆形的轨道上,使得地球能远离危险的中心区域。事实上,太阳与银河系【星河】的中心有一个最优化的距离,叫“共转半径”(co-rotation radius)。只有在这个位置上,恒星的公转速度与星系旋臂的速度一致——否则太阳会频繁跨越旋臂,暴露给其它超新星。另一个设计就是太阳的轨道几乎与银盘面(银河系【星河】的平面)平行,否则跨越那平面将是毁灭性的。
其次,还有美学和属灵方面的原因。如果神把太阳放在更靠近银河系【星河】中心的位置,那些厚重的星云,星尘和气体(姑且不论超新星),会让我们观察宇宙的范围缩小若干光年。所以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最优化的位置,即不在外围的边缘(那样银河系会太远而昏暗不清),而是足够地远,让我们能看清诸天的高深。这有助我们理解神的手段和思想的伟大,正如以赛亚书55:9所指出的。
最重要的是,能看到人类在神的计划里有中心地位的证据非常令人鼓舞。是地球上犯的罪使得整个宇宙落入痛苦和呻吟(罗马书8:22)。是在我们的行星上,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道成肉身,造物主进入被造物,在的神性上添加人性,不仅为了救赎我们,也要救赎整个宇宙(罗马书8:21)。神在浩瀚的宇宙中给渺小的人类最好的地位。这点思想令我们震惊和敬畏,正如诗篇8:3-4所讲: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致谢
在这里我想对众多创造论学者提供给我的意见表示感谢,——这些创造论学者包括了我经常在新墨西哥州见到的朋友。
参考文献
- 申纳,“论仙女座大星云的光谱”,天体物理学杂志,第9卷149-150页,1899年。Scheiner, J., On the spectrum of the great nebula in Andromeda, Astrophysical J. 9:149–150, 1899.
- 施礼佛,“仙女座星云的径向速度”,洛威尔天文台期刊,第58卷,1914年。Slipher, V., The radial velocity of the Andromeda nebula, Lowell Observatory Bulletin No. 58, 1914.
- 史春堡,“分析球状星团和河外星云的径向速度”,天体物理学杂志,第61卷5期353-362页,1925年。Stromberg, G., Analysis of radial velocities of globular clusters and non-galactic nebulae, Astrophysical J. 61(5):353–362, 1925.
- 哈勃,“河外星云的距离与径向速度之间的关系”,美国自然科学院汇刊,第15卷168-173页,1929年。Hubble, E., A relation between distance and radial velocity among extra-galactic nebulae, Proc. Nat. Acad. Sci. USA 15:168–173, 1929.
- 任德乐,《精华相对论:特殊的、一般的和宇宙的》,订正第二版,施普林格出版社,纽约,213页,1977年。Rindler, W., Essential Relativity: Special, General, and Cosmological, Revised 2nd edition,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p. 213, 1977.
- 哈里逊,《宇宙学:研究宇宙的科学》,剑桥大学出版社,英国剑桥,245页,1981年。Harrison, E.R., Cosmology: the Science of the Univer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p. 245, 1981.
- 莫鲁德等人,“在100百万秒差距以内的星团的速度场,第一部分:南方星团”,天体物理学杂志,第383卷5期467-486页,1991年。Mould, J.R. et al., The velocity field of clusters of galaxies within 100 Megaparsecs. I. Southern clusters, Astrophysical J. 383:467–486, 1991. 注意他们在480页上的图8。关于其它支持哈勃定律的数据,参注释8的第82-93页。
- 皮博斯,《物理宇宙学原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25页,1993年。Peebles, P.J.E., Principles of Physical Cosm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p. 25, 1993.
- 茨维基,“论光谱线穿越星际空间的红移”,美国自然科学院汇刊,第15卷773-779页,1929年。Zwicky, F., On the red shift of spectral lines through interstellar space, Proc. Nat. Acad. Sci. USA 15:773–779, 1929. 这是首个“疲倦的光线”理论,建议一种机制,就是光子在穿越宇宙空间的漫长旅程中会丢失能量(因而导致波长增大)。但是无论这个理论还是后来的许多后续理论都因为缺乏说服力而未能成功。
- 诺尔曼和塞特菲,《原子常数、光和时间》,斯坦福研究院国际部特邀研究报告,加州门罗公园市,1986年。Norman, T. and Setterfield, B., The Atomic Constants, Light, and Time, SRI International Invited Research Report, Menlo Park, CA, 1986. 这部专著提出光速的衰减会引起红移现象。
- 韩福来,“光速衰减和星系红移”,创世专刊,第6卷1期74-79页,1992年。Humphreys, D. R., C decay and galactic red-shifts, Journal of Creation 6(1):74–79, 1992. 我指出如果我们一致地应用塞特菲的理论 (注10),那么原子会释放蓝移的光,刚好抵消光线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红移。据我所知,塞特菲从来没有否认这观点。
- 阿尔普,《见红而止:红移、宇宙学和门派科学》,无边出版社,加拿大蒙特利尔,1998年。Arp, H., Seeing Red: Redshifts, Cosmology, and Academic Science, Apeiron Press, Montreal, 1998.阿尔普谈到了一些高红移值的物体(比如类星体)似乎与一些中等红移值的物体(比如星系)有联合的物理过程(因此距离很近)。他建议除了膨胀因素以外,应该还有其他因素让类星体的红移值比近邻的星系的红移值大很多。因此,对于一般的红移—距离趋势线是出于膨胀的理论,阿尔普的观察并不是反对的证据。见创世专刊第14卷3期39-45页上的评述,TJ 14(3):39–45, 46–50, 2000。
- 金特立,《创世的小奥秘》,第三版,【又见《创世的指纹》】,地球科学协会,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287-290页,1992年。Gentry, R.V., Creation’s Tiny Mystery, 3rd edition [see also Fingerprints of Creation], Earth Science Associates, Knoxville, pp. 287–290, 1992.金特立提议说遥远的星系是在一个轨道上运转,中心离我们的星系很近。其轨道速度会产生一个“横向”多普勒位移,这种红移是由于相对论的时间延缓所引起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引力蓝移,就是光线朝我们下落的结果。他后来试图引入新物理学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见金特立,“一个新的红移的解释”,现代物理学快讯,A类12卷37期2919-2925页,1997年。Gentry, R.V., A new redshift interpretation, Modern Physics Letters A12(37): 2919–2925, 1997。两个版本无一能解释星光怎样能在6000年之内到达我们这里。或许我们可以修改第一个版本,让其中已经有的引力时间延缓(引起蓝移效应)足够大,使得光线能迅速到达地球(用地球上的时钟测量)。这一点可能使它对创造论者来说更有兴趣。世俗的天文学家反对金特立的理论,因为就像我的理论一样,金氏的理论也是“河心说”的。
- 韦斯特,“宇宙的各向异性的模型”,创世科学研究协会季刊,第31卷2期78-88页,1994年。West, J.K., Polytropic model of the universe, CRSQ 31(2):78–88, 1994. 韦斯特按照金特立的理论(注13)的第一个版本,提供了几个具体范例,指出轨道红移能克服引力蓝移。
- 韩福来,《星光与时间》,主人书社,阿肯色州绿林市,66页,1994年。Humphreys, D.R., Starlight and Time, Master Books, Green Forest, p. 66, 1994. 圣经经文是:撒母耳记下22:10;约伯记9:8, 26:7, 37:18;诗篇18:9, 104:2, 144:5;以赛亚书40:22, 42:5, 44:24, 45:12, 48:13, 51:13;耶利米书10:12, 51:15;以西结书1:22和撒迦利亚书12:1。
- 韩福来,注15,67页。Humphreys, Ref. 15, p. 67.
- 任德乐,注5,212-214页。Rindler, Ref. 5, pp. 212–214.
- 这种运动不会摧毁我在第五和第六部分所描述的壳状结构。一个星系若以300公里/秒(典型的“本地”速度)运动,它需要直线运动10亿年才从其起始的位置移动1百万光年的距离。壳结构向我们暗示:我们所看到的星系要么没有运动超过10亿年,要么不是在作直线运动。
- 提夫特,“红移的分离状态和星系动力学,第一部分:单个星系里的内部运动”,天体物理学杂志,第206卷38-56页,1976年。Tifft, W.G., Discrete states of redshift and galaxy dynamics. I. Internal motions in single galaxies, Astrophysical J. 206:38–56, 1976. 这篇文章没有清楚地讨论星系群的红移量子化,而是提及他更早的一篇文章,在沙可沙夫特(编),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专题研讨会58,《星系的形成和动力学》,雷德尔出版社,荷兰多特雷赫特市,243页,1974年。Shakeshaft, J.R. (ed.), IAU Symposium The Formation and Dynamics of Galaxies, Reidel, Dordrecht, p. 243, 1974. 在随后的十年里,提夫特开始更清楚地描述这一现象,虽然他的理论还是很令人费解。
- 在提夫特展示的功率谱中,某些峰值的宽度甚至小于几个公里/秒。
- 提夫特和寇克,“全面的红移量子化”,天体物理学杂志,第287卷492-502页,1984年。Tifft, W.G. and Cocke, W.J., Global redshift quantization, Astrophysical J. 287:492–502, 1984.
- 纽曼、海因斯和特尔先,“红移数据和统计推论”,天体物理学杂志,第431卷1期第一部分147-155页,1994年。Newman, W.I., Haynes, M.P. and Terzian, Y., Redshift data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 Astrophysical J. 431(1/pt.1):147–155, 1994.
- 寇克和提夫特,“统计过程和双星系红移中的周期性的意义”,天体物理学杂志,第368卷2期383-389页,1991年。Cocke, W.J. and Tifft, W.G., Statistical procedur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eriodicities in double-galaxy redshifts, Astrophysical J. 368(2):383–389, 1991.
- 纳毗叶和戈思锐,“量子化的红移:一个现状报道”,天体物理学和天文学杂志,第18卷4期第一部分455-463页,1997年。Napier, W.M. and Guthrie, B.N.G., Quantized redshifts: a status report, J. Astrophysics and Astronomy 18(4):455–463, 1997.
- 科恩等人,“在哈勃远场中的红移集组”,天体物理学杂志,第471卷L5-L9页,1996年。Cohen et al., Redshift clustering in the Hubble deep field, Astrophysical J. 471:L5–L9, 1996.
- 提夫特,“在相对宇宙背景静止的参照系中量子化和可变的红移的证据”,天体物理学和空间科学,第244卷1-2期29-56页,1996年。Tifft, W.G., Evidence for quantized and variable redshifts in the cosmic background rest frame, Astrophysics and Space Science 244(1–2):29–56, 1996.
- 提夫特,“相对宇宙背景静止的参照系中的红移量子化”,天体物理学和天文学杂志,第18卷4期第一部分415-433页,1997年。Tifft, W.G., Redshift quantization in the cosmic background rest frame, J. Astrophysics and Astronomy 18(4):415–433, 1997.
- 史考特等人,在寇科斯(编),《艾伦的天体物理量》,第四版,斯普林格出版社,纽约,658,661页,2000年。Scott et al.; in: Cox, A.N. (Ed.), Allen’s Astrophysical Quantities, 4th edition, Springer-Verlag, New York, pp. 658, 661, 2000. 太阳正在以370.6 ± 0.4公里/秒的速度移动,相对于宇宙微波背景,向着星系经度和纬度(264.°31 ± 0.°17, 48.°05 ± 0.°10),或赤经和偏角为(11h, 9°S)。那个方向是在狮子座(Leo)的稍下方,位于鲜为人知的六分仪星座(Sextant)。我基于参考书中的数据计算如下:(a)太阳相对于我们星系的中心的速度是240公里/秒,方向是朝着星系坐标(88°, 2°)。(b)我们星系的中心相对于宇宙微波背景的速度是556公里/秒,方向是朝着星系坐标(266°, 29°)。后者的赤经和偏角为(10h 30m, 24°S),位于长蛇座(Hydra)下方。以上这些速度比地球环绕太阳的公转速度(29.79公里/秒)大很多。
- 巴考、奥斯垂克、泊穆特、和斯坦哈特,“宇宙三角:揭示宇宙的状态”,科学杂志,第284卷1481-1488页,1999年。Bahcall, N.A., Ostriker, J.P., Permutter, S. and Steinhardt, P.J., The cosmic triangle: revealing the state of the universe, Science 284:1481–1488, 1999.
- 比起在红移测量中观察到的大规模“泡沫”状的星系排布,球状壳结构其实小很多。就是说,星系的薄壳(间隔为一百万光年)存在于星系的厚“墙”(十数个百万光年)之上,而墙之间是大而空的“泡”,其中不存在任何星系。
- 取θ有一个平坦的几率分布,视等式11中的a cos θ为一个取值范围在- a到+ a之间的随机变量x。带入给出在给定θ下的几率的积分,得出x的几率分布是(a2 – x2 )– 0.5。把这一分布带入通常的计算方差的表达式(注释32,第57页,底部),进行积分,然后取方差的平方根,就得出我在等式13中给出的标准偏差。
- 布耳默,《统计学原理》,多佛出版社,纽约,第72页,1999年。Bulmer, M.G., Principles of Statistics, Dover Publications, New York, p. 72, 1979.
- 提夫特记录的最小的δv值是2.6公里/秒(虽然这个数据不如更大的间隔那么突出)。于是δr缩小到0.12百万光年,于是在等式15中的几率P降到2.24×10-16,也就是小于一千万亿分之一(10-15)的几率。
- 见注释28中的在不同参照系中的不同的速度。See Ref. 28 for various velocities in various reference frames.
- 包隔海,《地心说》,圣经天文学协会,克利夫兰,1992年。Bouw, G.D., Geocentricity, Association for Biblical Astronomy, Cleveland, 1992. 包氏提倡地心说。他引用诗篇93:1作为他的基础经文。注意这段经文中翻译成“世界”的希伯来词 תבל tevel可以被解作“大陆”,根据见郝礼待,《简明希伯来文和亚兰文旧约词典》,爱德曼出版公司,密西根州大瀑布市,第386页,1979年。Holladay, W.L., A Concise Hebrew and Aramaic Lexicon of the Old Testament, Eerdmans, Grand Rapids, p. 386, 1971. 于是,这段经文意味着在诗篇成书时(大洪水之后),各大陆相对于其下面的“地球根基” 不会再有明显的移动。
- 傅丹霓,“地心说与创造论”,创世专刊,第15卷2期110-121页,2001年。Faulkner, D.R., Geocentrism and Creation, TJ 15(2):110–121, 2001. 这是一篇详细的对现代地心说的批评。
- 金特立,注释13;韩福来,注释15。
- 范示尼,“类星体的红移假设: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吗?”,天体物理学与空间科学杂志,第43卷3-8页,1976年。Varshni, Y.P., The red shift hypothesis for quasars: is the Earth the centre of the universe? Astrophysics and Space Science 43:3–8, 1976. 范氏展示了来自384个类星体(非星系)的红移似乎被量子化为57个小组;如果用距离来解释红移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些类星体将分布在57个以地球为中心的球状壳上。他接着用这个“无美感的可能性”(unaesthetic possibility)来质疑对类星体用距离来解释红移的正确性。有一篇试图反驳他的短文抱怨说“那样的话,地球必须在宇宙中占据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见史蒂文森,“评论范示尼最近的关于类星体红移的文章”,天体物理学与空间科学杂志,第51卷117-119页,1977年。Stephenson, C.B., Comment on Varshni’s recent paper on quasar red shifts, Astrophysics and Space Science 51:117–119, 1977. 范氏在以下文章中给予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反驳,见范示尼,“类星体的红移假设: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吗?第二部分”,天体物理学与空间科学杂志,第51卷121-124页,1977年。
- 尽管有些创造论者赞成非银河系中心说的解释,他们似乎没有明白为什么世俗主义者拒绝银河系中心说,为什么这对于基督徒而言是个优势?为什么那可能是创世记1:6中的强烈暗示?见韩福来,注释15,71-72页。
- 苏卡诺夫(编),《韦氏大辞典II:新河边大学辞典》,河边出版社,波士顿,第242页,1984年。Soukhanov, A.H. (Ed.), Webster’s II New Riverside University Dictionary, Riverside Publishing Company, Boston, p. 242, 1984.
- 任德乐,注释5,212-213页。
- 德思潘,星光与时间,永远影音公司,新墨西哥州阿尔布开基市,2001年。DeSpain, M., Starlight and Time, Forever Productions, Albuquerque, 2001. 这是一个27分钟的录像,可以从创世记中的答案(Answers in Genesis)、创世研究协会(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和创造科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买到。
- 哈里逊,注释6,第107页。
- “无中心说”意味着“没有任何中心”。大爆炸理论家主张“每个点都是一个中心”,这反而模糊了问题。公众和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中心”这个词是指我在第八部分引用的那种词典中的定义,暗示一个物体只能有一个中心。 要让问题更清晰,大爆炸理论的支持者应该重述他们的主张为“每个点都是一个球状对称点。”
- 霍金和艾利斯,《时空的大尺度结构》,剑桥大学出版社,英国剑桥,第134页,1973年。Hawking, S.W. and Ellis, G.F.R., The Large Scale Structure of Space-Ti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134, 1973. 他们的引文是来自邦迪,《宇宙学》,剑桥大学出版社,英国剑桥,1960年。Bondi, H., Cosm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60.
- 罗伯森和努南,《相对论和宇宙学》,桑德斯出版公司,宾州费城,第336页,1969年。Robertson, H.P. and Noonan, T.W., Relativity and Cosmology, W.B. Saunders Company, Philadelphia, p. 336, 1969.
- 任德乐,注释5,201–203页。
- 任德乐,注释5,第134页。
- 任德乐,注释5,第135页。
- 高特,“哥白尼原理对于我们的未来可能性的隐含意义”,科学杂志,第363卷315-319页,1993年。Gott, J.R. III, Implications of the Copernican principle for our future prospects, Nature 363:315–319, 1993.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高特(Gott)这个名字在德文里的意思就是神(上帝)。
- 韩福来,注释15,31-38,74-79,122-126页。
- 史考特等人,注释28,第660页。其中h = 0.75。
- 韩福来,注释15,第128页。其中我的注3是:无名氏,“量子化的红移:正在发生什么事?” ,天空和望远镜杂志,第84卷2期28-29页,1992年八月。Anonymous, Quantized redshifts: what’s going on here? Sky and Telescope 84(2):28–29, August, 1992. 我的注22是:戈思锐和衲毗叶,“在近处星系里红移周期性的证据”,皇家天文学协会月刊,第253卷533-544页,1991年。Guthrie, B.N.G. and Napier, W.M., Evidence for redshift periodicity in nearby galaxies,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253:533–544, 1991.
-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论天球的运转”),约翰彼得出版社,纽伦堡,第一部,第10章,1543年。Copernicus, N., 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aelestium, Johannes Petreius, Nuremberg, Book I, Chapter 10, 1543. “因此我们坚称地球的中心(带着月球的轨道)在一个巨大的轨道上一年一周地(与其他行星一起)围绕太阳运转。太阳的附近就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静止的,任何表面看来的太阳的运动都可以被地球的运动更好地解释。”(从拉丁文的)翻译来自库恩,《哥白尼的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麻州剑桥,第179页, 1957年。 Kuhn, T.S., The Copernican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 179, 1957. 我同意哥白尼以下的观点:宇宙存在一个中心;但是地球既不严格地在这个中心,也不是相对它静止不动。宇宙微波背景的数据 (注释28)不同意哥白尼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太阳相对于这个中心是静止不动的。大爆炸理论的支持者是“超级哥白尼派”(hyper-Copernican),力图消灭任何中心。
- 韩福来,注释15,68-72页。
- 萨根,《苍白的蓝点:对人类在空间的未来的意象》,巴兰廷书社,纽约,第9页,1977年。Sagan, C., Pale Blue Dot: A Vision of the Human Future in Space, 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 p. 9, 1977. 断言地球无足轻重是萨根的书的一个主题。请参看在第九部分霍金和艾利斯的言论,和第十部分引用高特的话。
- 霍金和艾利斯,注释45, 第134页. 参看第九部分开头的引言。
- 夏法天,“太阳:我们的特殊的恒星”,创世杂志,第22卷1期27-30页,1999年。Sarfati, J., The Sun: our special star, Creation 22(1):27–30, 1999.
- 丘恩,“一个何等的恒星!”,新科学家杂志,第162卷2192期第17页,1999年。Chown, M., What a star! New Scientist 162(2192):17, 1999.
- 莫里斯,“在我们的星系的中心正在发生什么事?”,物理世界杂志,1994年十月号,37-43页,1994年。Morris, M., What’s happening at the centre of our galaxy? Physics World (October 1994) pp. 37–43, 1994.
如果我们直接从字面意义上解读圣经,而且使用可靠的马索拉文本,根据《创世记》里的家谱可以算出,亚当受造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4000年,是在创世的第六天。耶稣也说:“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可10:6),既然是“从起初”,就不是几十亿年以后。但是罗斯却接受进化论者的说法,认为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而亚当距今“只有”数万年。因为罗斯也接受进化论者关于原始人的“年代测定”,他认为那些原始人都与人类没有关系,尽管他们会埋葬死者、制造工具和乐器、绘制图形,等等。罗斯年代论的一个误导性暗示就是,澳大利亚土著可能不是亚当的后裔,所以按照他的神学澳大利亚土著就不是人。罗斯对人类变异的错误理解还让他得出另一个错误结论:上帝在巴别城使用超自然的手段引入了种族差异。
圣经历史大纲
- 天地和其中的万物都是在正常的、连续的六日中创造的,这六日跟我们的作息周中的日一样(出20:8-11)——见第二章。
- 亚当犯罪,导致我们肉体会死亡(罗5:12-19;林前15:21-22)——见第六章。
- 由于人类是受造界的代表性领袖,所以整个受造界也因人的堕落而受到诅咒(罗8:20-22),死亡进入动物界,终结了最初人和动物都吃素的时代(创1:29-30)——见第六章。
- 上帝用覆盖了全球的洪水审判世界(耶稣和彼得都将之与未来的审判比较——路17:26-27;彼后3:3-7)。除了登上“远洋客轮”(方舟)的之外,一切陆生脊椎动物和人类都被洪水毁灭了——见第八章。
- 洪水之后,人类拒绝分散,不肯重新遍满地面,于是上帝在巴别城再次审判人类,打乱了他们的语言。见下文“巴别之别和‘法勒时代’(创10:25)”。
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实上,圣经为这些事件都提供了精确的时间表。以下我们将看到,圣经中的族谱和基督的论断都有力地提示,人类的存在和地球的历史几乎一样长。
圣经中的族谱
应该采用哪个文本?
旧约圣经有三个主要文本:
- 马索拉文本(MT),是现代希伯来文圣经的范本,也是大多数英文旧约的依据。“马索拉”原指马索拉人(意思是“传递者”),是一群抄写圣经的专业人士,他们将文本规范化,并添注元音,以便于经文的诵读,因为之前的文本只有辅音。直到公元后七世纪到八世纪, 马索拉人才把加注的元音规范化。1
-
七十士译本(LXX)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相传这是公元前250年左右在亚历山大城由72位拉比翻译的(犹太人12个支派中各出6人),故称七十士译本。 事实上,它是从公元前三世纪就开始着笔的,历时数十年。因为译者众多,准确性也各不相同,尽管他们大多对摩西五经很熟悉。在新约时代,LXX被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广泛使用。这也是为什么新约里经常引用LXX(但也不尽然),否则的话,当《使徒行传》17:11提到的那些贤达的庇哩亚人将使徒的教导与旧约对照的时候,会说:“我们的圣经里不是这样的。”2 然而请注意不要夸大LXX对新约的影响。耶稣在同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中明确引用旧约的经文有64处(暗指的当然更多)。其中:
- 一半(32次)以上与LXX和MT都符合(因为在这些地方LXX对MT翻译得好)。
- 五分之一与LXX和MT都有出入。
- 五分之一符合MT,但不符合LXX。
- 其余的与LXX相符,与MT不符(但是有几句经文提示LXX也有不同的版本!如可13:25和可9:48)。3
- 撒玛利亚五经(SP)是个希伯来文版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世纪。当亚述人将以色列北国的许多居民驱逐以后,他们在撒玛利亚周围引进了殖民者。撒玛利亚人就是这些殖民者和犹太人的混血后裔。他们在基利心山周围建立了自己的敬拜体系(约4:20-21),其经文基础只有摩西的律法,即摩西五经,但与主流犹太人所使用的摩西五经又稍有不同。SP与马索拉文本大约有6000处差异,其中有2000处符合LXX,但不符合MT。
从下页表中可见,这三个文本中所记载的以色列先祖们在下一代出生时的年龄和死亡年龄有些出入,但都认同从创世至今只有数千年,而非亿万年。然而要研究圣经年代学,则应该依靠马索拉文本,因为另外两个文本都有修改的迹象。4例如,七十士译本中的年龄有明显的夸大,玛土撒拉活到了大洪水后17年, 这显然是错误的。
创造的日期
我们可以把创世的那一年定为世界历(Anno Mundi)元年,那么亚当死于世界历930年,挪亚生于世界历1056年。挪亚600岁时大洪水爆发,所以洪水发生于世界历1656年。他拉130岁时生亚伯拉罕, 是为洪水后352年,即世界历2008年。这样就限定了创世的可能日期。唯一的不确定性在于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这取决于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的年代和以色列王国的年代。只要知道了亚伯拉罕的年代,其他的日期就好算了。
已过世的葛哈德∙哈塞尔(Gerhard Hasel)博士曾经在安德鲁大学做教授,讲授旧约和圣经神学,他根据马索拉文本算出亚伯拉罕生于公元前2170年前后。这样洪水就发生在公元前2522年,创世是在公元前4178年。5哈塞尔博士假定家谱中没有缺漏,这是正确的,见下文分析。
家谱中有缺漏吗?
1984年,牛津大学的钦定希伯来文教授詹姆斯∙巴尔写道:“就我所知,任何一所世界级水平的大学里的希伯来文或旧约教授,也许无人不相信《创世记》第一章至第十一章的作者是希望带给读者以下的信息……把《创世记》里家谱中的数字简单地相加,就可以推算出从世界的开始
| 表9.1 不同文本中先祖的谱系年代表 | ||||||
| 人物 | 下一代出生时的年龄 | 下一代出生后在世的年岁 | ||||
| LXX | 马索拉文本 | 撒玛利亚五经 | LXX | 马索拉文本 | 撒玛利亚五经 | |
| 亚当 | 230 | 130 | 130 | 700 | 800 | 800 |
| 塞特 | 205 | 105 | 105 | 707 | 807 | 807 |
| 以挪士 | 190 | 90 | 90 | 715 | 815 | 815 |
| 该南 | 170 | 70 | 70 | 740 | 840 | 840 |
| 玛勒列 | 165 | 65 | 65 | 730 | 830 | 830 |
| 雅列 | 162 | 162 | 62 | 800 | 800 | 785 |
| 以诺 | 165 | 65 | 65 | 200 | 300 | 300 |
| 玛土撒拉 | 167 | 187 | 67 | 802 | 782 | 653 |
| 拉麦 | 188 | 182 | 53 | 565 | 595 | 600 |
| 挪亚 | 500 | 500 | 500 | 450 | 450 | 450 |
| 闪 | 100 | 100 | 100 | 500 | 500 | 500 |
| 亚法撒 | 135 | 35 | 135 | 430 | 403 | 303 |
| [该南] | [130] | – | – | [330] | – | – |
| 沙拉 | 130 | 30 | 130 | 330 | 403 | 303 |
| 希伯 | 134 | 34 | 134 | 370 | 430 | 270 |
| 法勒 | 130 | 30 | 130 | 209 | 209 | 109 |
| 拉吴 | 132 | 32 | 132 | 207 | 207 | 107 |
| 西鹿 | 130 | 30 | 130 | 200 | 200 | 100 |
| 拿鹤 | 79 | 29 | 79 | 129 | 119 | 69 |
| 他拉6 | 70 | 70 | 70 | 135 | 135 | 75 |
| 洪水时挪亚的年龄 | 600 | 600 | 600 | |||
| 从亚当到洪水 | 2242 | 1656 | 1307 | |||
| 从洪水到亚伯拉罕 | 1070 | 290 | 1040 |
到后期圣经历史的纪年表。”7
巴尔持新正统/自由派观点,所以不相信《创世记》,但他明白希伯来文清晰的教导。后来的保守派释经家形成了不同的想法,纯粹是由于他们觉得有必要与对地球年龄的认识保持一致,这些想法与经文本身毫无关系。
古老地球论者戴维斯∙杨(Davis Young)指出:“教会早期的前辈也根据《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中的家谱记载,以及圣经中其他地方的年代资料,认为基督在世的时候地球的年龄不超过六千年。”8
犹太史学家弗拉维∙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 公元37年或38年至公元100年左右)在他的《犹太人古代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也给出了一个纪年表,其中也没有显示缺漏的迹象。这说明约瑟夫时代的犹太人从来不认为有缺漏。从约瑟夫所记载的人名和年龄可以看出,他的资料主要是LXX。9
“这灾难(大洪水)发生于挪亚600岁那一年, ……据摩西记载是在当月(二月)二十七日(十七日)开始的。从第一个人亚当算起,这是第2656(1656)年。这日子写在我们的圣典里,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所作的记录,当事人的生卒年期都很准确。
亚当生塞特的时候确实是230岁,他活到930年。塞特205岁生以挪士,活到912岁。以挪士190岁时生该南,他活到905岁。该南活到910岁,在170岁时生玛勒列。玛勒列活到895岁而死,撇下雅列,是在他165岁时生的。 雅列活了962年,他在162岁时生以诺。以诺活了365岁以后走了,去了神那里,所以先祖们没有写到他的死。以诺165岁时生玛土撒拉,玛土撒拉187岁时生拉麦,玛土撒拉活到969岁。拉麦182岁生挪亚,777岁时派挪亚管理人事,活到950岁。这些岁数加起来就是前边给出的总数。人们不必考查这些人的死,因为他们与子孙同活,人们只需要考虑他们的生……10
现在我讲希伯来人。法勒的父亲是希伯,法勒的儿子是拉吴,拉吴的儿子是西鹿,西鹿生拿鹤,拿鹤的儿子是他拉,他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所以亚伯拉罕是挪亚的十世孙,生于洪水后290年,因为他拉生亚伯兰时70岁,11拿鹤生哈兰(他拉?)时120岁,西鹿生拿鹤时132岁,拉吴生西鹿时130岁,法勒生拉吴时也是130岁,希伯生法勒时134岁,沙拉生希伯时130岁,亚法撒生儿子沙拉时135岁,亚法撒是闪的儿子,是洪水后12年生的。”12
再者,以上引文出自“第一卷,跨3833年:从创造到以撒之死”。这再一次排除了缺漏或漫长的创造日。
为表明对巴尔和约瑟夫的引述不仅是诉诸权威,以下从释经学的角度讨论圣经纪年表之严密性的依据。
文法
罗斯指出圣经中某些家谱是有缺漏的,所以他声称《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家谱也远非完整(罗斯著作《创世记的问题》,The Genesis Question, 简称GQ,第108-109页)。他还称(GQ:109):“这些文字翻译成英语,变成了:‘当X活到Y岁时,他成为Z的父亲’;但别人读同一段文字的希伯来语原文时可能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当X活到Y岁时,他成为一个家族的父亲,该家族包括Z,或最终诞生了Z’”。
然而他所列举的家谱中缺漏的例子(对比《马太福音》1:8-9和《历代记上》3:10-12节),没有一个提到下一代诞生时父亲的年龄,所以这些例子与《创世记》里的家谱问题无关。再者,马太的家谱显然不是为了完整,而是明确地讲要列出三个十四代人名(太1:17),其原因也许是大卫名字的希伯来字母加起来等于14。《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没有这样的考量,所以《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名单有时也称为纪年家谱,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两个名单同时包含时间信息和人物信息。哈塞尔解释了这一差别:
“就马太的家谱而言,其模式化是不难看出的,与旧约里的家谱资料一对比就可以验证。能否证明《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也是这种情况呢?这两章里有没有十加十的模式呢?简单地数一下这两章里的先祖人数就看出,这里并没有十代一组的系列。第五章里从亚当到挪亚有十世,挪亚生三子,但是在第十一章里,从闪到他拉只有九世,他拉‘生了亚伯兰、拿鹤、哈兰’(创11:26)。如果第十一章里亚伯拉罕算为第十代先祖,那么在第五章里闪也必须照样算作第十一代,因为两段家谱里的最后一位先祖都有三个儿子列出。将《创世记》5:32和11:26的经文做比较,没有理由在一个地方把三个儿子中的一位算进来,而在另一处不算,因为模式是一样的。所以,如果在第五章里数出十代先祖,那么在第十一章里用同样的数法就是九代;如果在第五章数出十一代,在第十一章里就要数出十代。10比9或11比10很难说成是有意的安排或对称。总之,希伯来文本里并没有所谓的‘洪水前后各有十代的对称性’。所以用《马太福音》1:1-17里三组十四代做类比是牛头不对马嘴。”13
罗斯还指出希伯来文里的“父亲”也可指祖父或祖先,而“儿子”也可指孙子或后代(GQ:109)。但这里罗斯又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既毫无根据的外延扩展。14某些词在某些语境中可以有某种含义,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词在任何语境中都可以有这些含义。《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的家谱,讲到X“生儿养女”,在这个具体的语境里,意味着Z是X的一个儿子。
即使我们退一步,认可Z是X的“后裔”,但Z前边总是带有宾格助词תאֶ,助词不能翻译,但标明Z是动词“生”的直接宾语。这意味着X在Y岁时确实生了Z,不管Z是儿子还是儿子以下的晚辈。希伯来文法更进一步支持这一点——这里的希伯来动词“生”是hiphil语态的连续未完成式,hiphil词根表示主语参与某行为并导致了某一事件,比如塞特“生”以挪士。哈塞尔指出:
“一个短语在旧约里重复了15次, 就是‘某人生某人’——全部是在《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里。另外还有两处提到了三个儿子的名字(创5:32和11:26)。该短语中的动词还以同样的形式在另一个短语(“并且生儿养女”)中使用了16次(创5:4, 7, 10等;11:11, 13, 17等)。从《创世记》其他经文中这一动词Hiphil语态的用法,可以看出 “生”的是具体的直接后裔(创5:3和6:10)。旧约其他经卷中“生”的Hiphil语态也都明显地指具体的直接后裔,并无例外(士11:1;代上8:9; 14:3; 代下11:21; 13:21; 24:3)。同样的用法在《历代志上》的家谱中重复出现了两次,“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样的表述(代上1:34;参照5:37 [6:11])排除了所提到的儿子不是直接后裔而是远期后代的说法。所以,《创世记》第五章和第十一章中“某人生某人”的短语,其意思不会是 “亚当生塞特之祖先”。认为这两章中塞特或任何提到名的儿子其实是远期后代的说法,在希伯来语言用法的证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15
哪里可以塞进“缺漏”?
塞特:塞特肯定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他父母认为他取代了被该隐杀死的亚伯(创4:25)。
以挪士:一定是塞特的儿子,因为塞特给他取的名(创4:26)。
以诺:《犹大书》14节讲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表明从亚当到以诺都是直接的父子关系。
挪亚:拉麦给他取的名,所以拉麦一定是他的 父亲,而不仅仅是一个祖先(创5:29)。
闪、含、雅弗:一定是挪亚的儿子,因为他们同在方舟里。
亚法撒:显然是闪的儿子,因为他是洪水后二年生的(创11:10)。
亚伯兰、哈兰和拿鹤:是他拉的儿子,因为他们都一同出自迦勒底的吾珥(创11:31)。
玛土撒拉:以诺是洪水前的一位先知(犹:14),给他儿子取了这个名字,意思是“他死的时候就会发出”。根据马索拉文本的编年表,如果没有缺漏,他死的那一年洪水就来了。
有释经家称玛土撒拉的意思是“梭镖之人”,但基督徒希伯来文学者阿诺德∙弗鲁克顿鲍穆博士(Arnold Fruchtenbaum)指出 :
“玛土撒拉可以表示两种意思,可以是‘梭镖之人’,也可以是‘他死的时候就会发出’。争议不在于该词语的后半部分,‘撒拉’就是发出的意思,这是‘撒拉’的本义,当语境中有‘强力高速’的时候,它还可以表示投掷。 据此,有人认为‘撒拉’可以指箭、梭镖或长矛。然而那是衍生意思,‘撒拉’的原义就是‘发出’,任何字典都会指出这一点。
如何翻译‘撒拉’最终取决于如何理解该名字的前半部分,即拼成‘玛土’的两个字母。从词根上,其意思确实是‘人’。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解经家把玛土撒拉翻译成‘梭镖之人’或‘飞箭之人’。然而我在任何字典里都找不到用‘梭镖’或‘箭’来解释‘撒拉’的意思的,这显然是从‘发出’衍变成了‘投掷’,又衍变成‘制造某物品’。如果要严格照字面意思将‘玛土’理解为‘人’,那么‘玛土撒拉’就不是‘梭镖之人’或‘飞箭之人’,而是‘发出之人’。
对‘玛土’的另一种理解方式是认为它的词根来自‘死’。再者,‘玛土’和‘撒拉’之间的字母vav给它一层动词色彩。所以我主张用‘死’的词根,并严格按字面理解,‘玛土撒拉’就成了‘他死了就发出’ 了。
我主张把这个名字翻译成‘他死的时候就会发出’,有两个理由。首先是因为这样翻译更符合希伯来文对这个名字的解释思路,第二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翻译更符合大背景。如果我们遵循《创世记》的纪年表,他死的那一年就是大洪水之年。我认为这并非纯粹的巧合。”16
需要缺失许多世代
值得指出的是,罗斯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缺失的几个人名。人们通常把大洪水往前推,由于《创世记》第十一章里的家谱把洪水和亚伯拉罕连起来,这里的家谱就必须“扩展”。罗斯把洪水的年代定在“两到三万年前”(GQ:177)。然而,由于《创世记》第十一章里的人们是在35岁以前生的儿子,即使只加一万年也需要250代以上!人们不能不问,一个家谱何以缺失这么多世代而不留痕迹?再者,写进家谱的名字中,有许多并没有提到任何事迹或言论,作者为何跳过了那么多世代而专门提到他们呢?
该南是个缺漏吗?
罗斯还指出《路加福音》第三章第36节多出一个该南来,《创世记》第十一章第12节中没有提到这个人(GQ:109)。他据此声称,既然这里证明有一个缺漏,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无限增加缺漏。
《路加福音》的大多数希腊文版本和《创世记》第十一章的七十士译本都有该南的名字。17然而根据这两处经文的文字背景来看,原稿中可能没有这个名字。
- 只有在《路加福音》写成多年之后的七十士译本的抄本中,《创世记》第十一章才多出一个该南。最早的七十士译本的抄本并没有这个该南。18
- 现存最早的《路加福音》抄本没有这个该南。该抄本见于博德默收藏库,标号P75,是写在纸莎草纸上的,共102页(原稿104页), 年代定于公元175年到225年。19
- 约瑟夫采用七十士译本为依据,但他没有提到第二个该南(见上文“家谱中有缺漏吗?”)。
- 朱利叶斯∙阿弗里坎那斯(约公元180-250年)是“已知第一个提出完整纪年表的基督徒历史学家”。他于公元220年提出的纪年表也采用了七十士译本,也没有提到这个神秘的该南。20
以上证据显示圣经原稿中并没有这个额外的该南,现在我们也许可以猜测抄本中的差错是如何形成的。
注意希腊文新约的原稿中并没有标点,词与词之间也没有空格。所以《路加福音》第三章第35-38节最初应该是如下的样式。也许文稿中TOUKAINA(该南的儿子)是在第三行的末尾:
TOYΣAPOYXTOYPAΓAYTOYΦAΛEΓTOYEBEPTOYΣAΛA
TOYAPΦAΞAΔTOYΣHMTOYNΩETOYΛAMEX
TOYMAΘOYΣAΛATOYENΩXTOYIAPEΔTOYMAΛEΛEHΛTOYKAINAN
TOYENΩΣTOYΣHΘTOYAΔAMTOYΘEOY
假设早期有一位抄写《路加福音》人正在抄写第一行,但是他的目光落在了第三行末尾的TOUKAINAN,于是就把它也写在了第一行:
TOYΣAPOYXTOYPAΓAYTOYΦAΛEΓTOYEBEPTOYΣAΛATOYKAINAN
TOYAPΦAΞAΔTOYΣHMTOYNΩETOYΛAMEX
TOYMAΘOYΣAΛATOYENΩXTOYIAPEΔTOYMAΛEΛEHΛTOYKAINAN
TOYENΩΣTOYΣHΘTOYAΔAMTOYΘEOY
翻译成中文(保留原文的断行格式,再加上希腊语原文里没有的“儿子”)就成了:
西鹿的儿子,拉吴的儿子,法勒的儿子,希伯的儿子,沙拉的儿子,该南的儿子,
亚法撒的儿子,闪的儿子,挪亚的儿子,拉麦的儿子,
玛土撒拉的儿子,以诺的儿子,雅列的儿子,玛勒列的儿子,该南的儿子,
以挪士的儿子,塞特的儿子,亚当的儿子,神的儿子。
既然是一位抄写《路加福音》的人带来的错误,怎么七十士译本里也有呢?如上所述,早期的七十士译本里没有,所以一定是某个抄写者后来加上去的,以求与《路加福音》一致。还有一个证据就是“该南”在生儿子和死亡时的年龄与沙拉一样,这个容易理解,抄写的人看到了《路加福音》中多出一个名字,但那里没有年龄,所以只好把下一位先祖的年龄套用一次。
该南的分歧丝毫不影响圣经无误的教义。如上所述,错误并不在于原稿,而属于现存抄本中极少数的抄写错误。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罗斯说他也赞同)第十条是这样写的:
“我们坚信,严格说来,默示仅是针对圣经的原本说的;而在神天命中,根据现今可得的抄本,能高度准确地辨识原本〔的经文〕。我们并坚信,圣经的抄本与译文若忠实地表达了原本,就是神的话了。
我们否认基督教信仰任何主要内容,会因原本的不在而受到影响。我们更否认因原本的不在,使得圣经无误的宣称成为无效或无关紧要。”
世俗历史学
罗斯称,教导按字面理解《创世记》的宣教士之所以不为人接受,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华民族的起源早于公元前4004年……今天澳大利亚的土著……也有同样的反应,他们的历史追溯到25000年前……这都是确凿的年期。”(GQ:108)
然而《大英百科全书》如此描述中国:“有明确历史资料的第一个朝代是商,或称殷(公元前18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21不仅如此,对最早的中国文字——甲骨文的研究表明,中国文字是基于《创世记》所记载的事件的。22
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化是口耳相传的,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年期”并非基于历史记载,而是基于“测年法”。然而有些“测年”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土著的历史比罗斯所认定的亚当的年代还古老。如果这样的年期被广泛地接受,他自己的护教学又会怎样?
耶稣和宇宙年龄
从所谓的大爆炸至今的“世俗年代表”,是罗斯年代学的基础。然而该年代表将人放在创造的末尾,好像人的创造是造物主后来临时做的决定。芝加哥大学进化论古生物学家尼尔∙叔宾(Neil Shubin)在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的进化论系列片第二集中打了一个比方。他和罗斯一样,称地球有45亿年的历史。为了说明人类是如何地微不足道,他把地球史压缩成一小时。然后他称,动物直到最后十分钟才存在,而人类出现于最后的百分之一秒。罗斯自己也用了一个类似的比喻(见《上帝的指纹》,The Fingerprint of God, 第178页,以下简称FoG):“如果把宇宙被造以后的时间压缩成一年,全部人类历史还不到一分钟。”

进化论/亿万年史观与基督的教导不相容,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主耶稣基督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格,是道成肉身(约1:1-14),他在圣经中明确地说这种史观是不对的。因为人类在创世之初就存在,所以这世界不可能有亿万年之久。比如耶稣在解释婚姻的基础是上帝的创造时,他引用了《创世记》第一章27节和第二章25节(太19:3-6;可10:6-9)。在《马可福音》第十章6节,他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如果耶稣不肯定《创世记》本来应该按字面理解,这句话就没有意义。如果地球在他之前4000年被造,而亚当和夏娃是在第六天被造的,那么第六天在4000年的标尺上跟“起初”就没有什么区别(6天是4000年的0.0004%)。相反,进化论者通常认为我们是几百万年前从树上悠荡下来的,人类在世界史上的位置就被移到了另一端。而罗斯认为亚当和夏娃是一万到六万年前才创造的,这就更跟耶稣的观点背道而驰了。23
有人一厢情愿地声称,耶稣的意思只是“当初‘他们’被造的时候”,但这种理解说不过去——他们自己被造的时候当然就是一男一女,否则他们能是什么?是两性人? 不,上下文明确显示,耶稣指的是上帝在创造之初的计划。希腊文ἀπὸ δὲ ἀρχῆς κτίσεως,就应该译成“从起初创造的时候”。这个词组在别处经文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是指整个受造界: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可13:19)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彼后3:4)
这两处经文中都有希腊文词组ἀπ’ ἀρχῆς κτίσεως,与《马可福音》10:6中是完全相同的。有没有连词δὲ(但)无所谓,另外ἀπὸ在元音前略为ἀπ’,只是写法不同。另外,这两处经文也都支持人类从创世之初就存在的教导。
还有其他的经文表明耶稣和使徒们都承认人类从起初就存在。
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50-51节,耶稣说:“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迦利亚的血为止……”就是说,屠杀先知的事情几乎从世界的开始就有。因为代替亚伯的塞特是在亚当130岁时生的(创4:25, 5:3),所以亚伯死的时间在世界历史的标尺上距离起始点还不到3%。保罗在《罗马书》一章20节指出,人们可以透过“所造之物”清楚地看到神的大能,而且“自从造天地以来”就是如此,这再一次排除了人类在创世后数十亿年才被造的说法。
堕落的时间
亚当夏娃的堕落是在什么时候?从圣经中我们可以逻辑地推测,不会是在创造的那一周,因为上帝称一切“甚好”(创1:31)。也没有迹象表明是在第七天,因为上帝祝福这一天,这一天并没有罪和诅咒的意思。所以堕落一定发生于创造周之后。
然而从亚当和夏娃儿女的历史来看,堕落不会在创造之后很久。他们受命“遍满地面”;在未曾堕落前他们肯定遵从了,而且因为他们的肉体是完美的,一定能马上受孕,至少在第一个月经周期之内就能怀孕。但是他们孕育的第一个孩子(该隐)无疑是个罪人。
所以堕落一定发生于创造周之后不久,也许不过三四个礼拜。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断撒旦堕落的时间范围,撒旦的堕落一定发生于被神祝福的第七天和人类的堕落之间。
人类的长寿
罗斯接受圣经记载的长寿命,反对重新定义“岁”(可惜他对“日”并不这么认真)。然而他在GQ第十五章中把《创世记》第六章第3节的120年解释成个人的寿命缩短到120岁。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与其他经文抵触,圣经记载洪水后多年还有许多人活到几百岁。最好的理解是全人类的时间还剩下120年,然后洪水将毁灭人类,只在方舟上保留数人。
罗斯是这样解释人类寿命缩短的:贝拉超新星(Vela supernova)爆炸形成了大量的放射线,增加了人类罹患癌症的风险,上帝为了“保护”我们,便以超自然的方式加快了细胞凋亡(程序性细胞死亡)的速度。他说这次超新星爆炸是自人类出现以来离地球最近的一次,距离我们1300光年,发生于“18000 ± 9000或31000 ± 6000年前”(GQ:121-123)。这种说法莫名其妙,为防止人们在500岁或900岁的时候患癌症,就让他们衰老,在120岁之前就死亡!下一步会怎样?为了防止人们在80岁的时候患老年痴呆症,就让他们在60岁的时候死于心脏病发作?
而且,贝拉假说之所以没有道理,还有另一个原因。大约700年前发生了RXJ0852.0-4622超新星爆炸,距地球600光年。这比贝拉近多了,可是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在公元1300年前后人类又出现了一次急剧的、永久的寿命缩短。
关于人类长寿的一个可能的科学解释
人类寿命的缩短有一个可能的科学机制,就是“长寿基因”通过基因漂变而流失,这是由于洪水造成人口急剧减少,而且在巴别之后出现基因库的分离,然而罗斯忽略了创造论文献和基因研究的发现。24(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大量死亡,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繁殖,群体数量减少50%以上,这称为瓶颈,因为这种变化曲线类似于从宽到窄的瓶颈形状。大家公认瓶颈能加强基因漂变和自然选择的效果)。另外挪亚生子的时候年龄大了,这可以解释闪的相对短寿。
对长寿的一个解释与端粒有关,端粒是染色体末端的重复性DNA序列,其作用是保护基因信息。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都会缩短。如果端粒消失了,信息就会被腐蚀,细胞就会死亡。端粒酶能够将端粒延长——2009年颁发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就是因为1980年发现了“染色体受端粒和端粒酶保护的机制。”将端粒酶基因导入培养中的人体细胞,便可以使细胞获得无限分裂的能力。25生殖细胞中有活跃的端粒酶,所以传递给下一代的信息尚且是相当“新鲜”的。克隆羊“多丽(Dolly)”遗传的是“老化”的端粒,这可能是她早衰的原因。
不幸的是,端粒酶也常常活跃于癌细胞中,造成它们分裂失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亨利艾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当年她31岁,家住马里兰州巴尔迪摩市,是个非洲裔美国人,是五个孩子的妈妈,患了恶性子宫颈瘤,人们从她的身上分离出肿瘤细胞。1951年,在发现癌症仅仅八个月后,亨利艾塔不幸病故。然而她死后50多年以来,她的癌细胞在一直不断地分裂,所以HeLa细胞系(在她的名和姓中各取两个字母作为细胞系的名称)实际上是永生的。几十年来HeLa细胞系为医学实验室所使用,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和其他医学进展中功不可没。
在第二版中(GQ:124-125),罗斯放弃了细胞凋亡的解释,他在网站上承认自己也许夸大了这一现象。26然后他紧紧地抓住端粒,这一次他声称上帝降低了端粒酶的活性,其目的仍然是“保护”我们,用缩短寿限的办法来防止癌症!
早老症
还有反面的证据支持人类长寿是受遗传因素影响。早老症(Progeria,其词根源于希腊文的“老”字,Υερας,与老年病学gerontology的词根一样)),学名哈钦森 - 吉尔福德早老综合症(Hutchinson–Gilford progeria syndrome, HGPS),平均每8万儿童中有一例患者。患者的老化速度比正常快5-10倍,表现典型的衰老症状如脱发、白内障及骨质疏松,13岁左右死亡,通常死于心脏病或中风。美国国立人体基因组研究院发现,早老症是由于一个突变,改变了甲型核纤层蛋白基因25000个碱基对中的一个。27如果一个胞嘧啶变成胸腺嘧啶就能让患者的寿限缩短至十分之一,也许大洪水后一个类似的突变也导致了人类的寿命以类似的比例缩短。
种族的起源
巴别之别和“法勒时代”(创10:25)
圣经记载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在巴别城语言的混乱(创11),这发生于法勒的时代(创10:25)。在赖尔(Charles Lyell)和达尔文之前的解经家(包括约瑟夫28、加尔文29、凯尔和德里采30)以及后来的解经家(如路普尔德31)都几乎一致同意这段经文指的是巴别塔的语言分隔和此后的领土分隔。有的创造论者提出这句经文指的是洪水后的所谓大陆分离,但是大陆分离的灾难性不会亚于洪水本身!
我们永远应该以经解经,而圣经中没有依据提示这句话指的是大陆分离。从《创世记》10:25提到法勒时代到《创世记》11:1(“那时,全地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只有八节经文(注意圣经章节的划分不是神的启示),而且由于他们的不顺从,“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全地的言语”(创11:9)。这无疑证明被分裂的“地”就是讲同一种语言的地,就是说,从上下文看,“地”指的是地上的人民,而非地球。
从表9.1,我们可以算出法勒出生于洪水后101年。由于人类的长寿和圣经中所记载的子孙数量,届时可能有3000人了。如果希伯给法勒取的名字是预言(就像玛土撒拉的名字一样),巴别事件有可能是在法勒时代的后期发生的,那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让人口增长。32
巴别的结果
最明显的结果是产生了主要的语系,并从中演变出了各种现代语言。然而按照新创造出的语言群体而对人类进行分割,这也导致了其他的效应。
巴别产生了许多相互隔离的小群体,每个群体只携带人类全部基因库的一小部分。这有助于将一些性状固定,从而产生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不同族群(“种族”)。自然选择和性别选择在此基础上发挥作用,对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精细调整。
罗斯相信巴别之分离在“种族”的起源上至关重要,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这是他的一个严重失误)。他说(GQ:181-182):
“人类族群的起源仍然是一个迷。圣经、圣经以外的文献和现代科学研究都没有给出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从圣经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事实,既种族多样性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存在。……
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人类在从挪亚时代到摩西时代的短时期中,何以形成了如此显著的肤色差别以及一些比较细微的其他差别?通常的回答是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但这似乎还不够。……
根据对阳光的敏感性而进行选择的收效甚微。……我们看到深色皮肤的爱斯基摩人住在北极,而浅色皮肤的希腊人住在地中海的岛上,这证明自然选择虽然对某种肤色有利,对另一种肤色不利,但其效果显然不大。
这些观察提示,自然选择不能解释种族多样性是如何在数万年间形成的。冒着‘神在知识空白里’的嫌疑,我在这里提出另一种解释。
既然《创世记》第十一章如此明白地描述了上帝亲自介入 人类,以瓦解团结起来的破坏力量,并激励人们分散到地球上一切可居住的陆地,当时上帝可能不仅仅分化了他们的语言。他或许还引入了某些外在变化——那些我们称之为种族特色的性征——以促使人们分离。
……上帝介入的方式或许是……奇迹般地引入一些新事物,在这里可能是新的遗传物质,以产生种族特性。”
然而,简单的遗传学可以很容易地解释种族特征的起源。在人类,新“品种”可以快速形成。大家知道,两个黑白混血儿(含有多种“种族”性征)结婚能生出各种肤色的子女。当然种族特征不可能通过进化的途径快速形成,因为那要靠许多随机突变形成新基因,还要在人群中经过许多世代而缓慢地取代旧基因才能固定下来。33
这就是为什么爱基斯摩人和南美洲赤道附近的土著都有中间性的褐色皮肤,而不是很白或很黑——他们根本没有相关的遗传信息。今天这些“族群”都是高度特殊化的,没有黑白混血儿(类似于亚当夏娃)那么多样的基因,所以形成的后代变化有限。
但是罗斯提议上帝在巴别直接参与,在不同群体中引入了“种族”特征。圣经中没有丝毫这样的提示。罗斯承认这是“神在知识空白里”的解释。如果他理解了基本的创造论文献,这种说法便没有必要了。
然而最让人忧心的是,罗斯声称不同的“种族”特征是上帝设计的,目的是帮助人类的分散。罗斯明白地表示(我也同意)他无意赞成任何形式的种族优越感,他说“这并不提示不同民族在商业或婚姻上的合作和混合有什么不对。”
可是他的见解事实上令人想起十九世纪的种族主义。当时有些人拒不承认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尤其在智力上和灵性上。那些种族主义者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种都来自亚当和夏娃,而只有他们自己种族的成员才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他们认为,向没有灵魂的深色人种派遣传教士是徒然的。
罗斯的说法,即认为上帝直接介入了亚当的生物遗传谱系(为的是使某些族群与其他族群有所区别)的说法,确实带着这些不正确思想的味道。实际上这暗示种族歧视是上帝的设计,为的是“促使人们分离”。
最后,他提出的“新的遗传物质”似乎强化了一种偏见,即认为在族群之间真有显著的基因差异,而且是本质的差异。然而几乎所有的现代遗传学家都承认(基于生物学事实,而非“政治正确”)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是如此地微小, “人种”这个概念在生物学上没有意义。
罗斯的年代表里土著不算人类吗?
亚当和夏娃的年代范围
1997年,罗斯在他的网站上宣称:“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双足灵长类动物都灭绝了。后来,大约在10000到25000年前,上帝以亚当和夏娃取代了他们。现存于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从亚当和夏娃而来。”34
范围的界限
罗斯就这样提供了一个范围。在时代学研究中,有两个术语描述一个时间范围的绝对上限和绝对下限。“起点”(拉丁文Terminus a quo)指最早的日期,“终点”(拉丁文terminus ad quem)指最晚的日期。这两个点是范围的界限。
土著的“年代”
罗斯认为土著是人,所以必定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这一点和创造事工国际(CMI)一致。上一章提到,罗斯同意,即使他的局部洪水也消灭了全人类,只有挪亚一家存活,所以土著也必定是挪亚的后裔。
所以,任何“确定”的土著日期的起点都必然是大洪水的终点(最晚)日期。换句话说,任何关于大洪水发生的日期都必然早于土著的日期,而亚当和夏娃受造的日期当然早于大洪水。
罗斯不加批判地接受放射性测年法,但这为他的人类学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表面上可靠的加速器质谱(AMS)碳-14测定法将澳大利亚土著的历史追溯到41000年前。35不太可靠的热释光法把土著民族的历史定在60000年左右。36 由于罗斯相信这些日期,尤其是AMS测年法,他怎能把土著的历史置于亚当和夏娃的整个年代范围之前?罗斯的“信仰的理由”组织和我们的“创造事工国际”都认为只有亚当的后代才算人,可是为土著“鉴定”的41000年的历史把他们置于罗斯所认可的亚当年代之前。所以到了2002年,罗斯把上述引文的中间一句改成了“后来,大约在10000到60000年前,上帝以亚当和夏娃取代了他们。”37当然没有什么新的希伯来文研究支持他的改变,这一改变纯粹是出于所谓的“科学”,再一次显示科学压倒一切。
然而罗斯没有意识到这并不解决问题。他为亚当的创造提供了一个范围,从10000年前到60000年前。注意该范围意味着亚当的年代可以在10000到60000年前的任何日期,然而这还不排除原住民不是人的可能性。如果罗斯相信土著的历史有60000年之久,这个数字应该是亚当年代范围的终点(最晚)日期,所以亚当受造的日期应该早于60000年前,然而他错误地将土著的日期当作亚当受造的起点(最早)日期,与逻辑背道而行。
还有更糟糕的,因为罗斯把他的毁灭人类的局部洪水定在“两万到三万年前”(GQ:177),但罗斯还提到“澳大利亚土著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25000年”(GQ:108)。再一次,“信仰的理由”和“创造事工国际”都同意,现存所有人类族群都是挪亚的后裔,所以必然晚于大洪水。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土著可能不是人。这与任何测年法的可靠性无关——根据他自己估计的日期,他自己的书里就有这些矛盾。
“猿人”
创造论对穴居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理解
我们注意到巴别之分散的重要性,该事件造成了人类基因库的分离,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同时有些族群与文明世界隔绝。即使在今天,如果一个典型的小家族突然与世隔绝,比如说,到了一个荒岛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许多家族不会熔炼金属,也不会盖房,只好使用所能找到的最坚硬的材料(石头)做工具,住在自然存在的结构(山洞)里。不同的家族也将表现出不同水平的艺术能力。
所以,根据圣经的时间表,创造论者认为尼安德特人以及直立人都是真正的人类,是亚当夏娃的后代,生活在巴别塔之后。随着巴别的分散,他们与都市隔绝,而且由于某些基因在小群体和选择的作用下被固定下来,他们也演化出某些躯体特征。“石器时代”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是不同族群的穴居/石器技术阶段。 即使今天还有人生存在这样的技术水平上,比如伊里安查亚(Irian Jaya)的达尼人(Dani),但他们是与我们同时代的、同样的人。
灵性表现
但是罗斯如此地表述他对所有这些所谓“猿人”标本的基本见解:
“大约二百万到四百万年前,上帝开始制造一些类似于人类的哺乳动物,或叫‘原始人’。这些动物两足直立,脑容量大,并会使用工具,有些甚至埋葬死者并在洞壁上绘画。然而,他们与我们的差异很大。他们没有灵性,没有像我们一样的意识。他们不敬拜上帝,也没有宗教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双足灵长类动物都灭绝了。后来,大约在10000到60000年前,上帝以亚当和夏娃取代了他们。现存于地球上的所有人都是从亚当和夏娃而来。”38
罗斯关于 “灵性表达”最早出现的时间完全是基于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宗教活动用具,据鉴定是在24000年以前(GQ:110),他这样做犯了好几个错误。有些错误我们在下面提到尼安德特人时还会进一步讨论。当我们转而考虑一些无可置疑的人类成员时,罗斯的有关论点会变得更不堪一击。
第一点:如前所述,没有半点证据显示古代智人(根据传统的测年法,生活于6万年前)与现代人在认知能力上有什么差别。因为宗教是一种认知过程(如对自己生命的有限性的认识、形成抽象的是非概念的能力、崇拜强大实体的欲望,等),所以罗斯试图将智人分为“有灵性表现”和“没有灵性表现”,或者分为“有敬拜能力”和“不会敬拜”,都没有任何实质的依据。这完全是随心所欲。
第二点:罗斯又在用知识空白进行论证。事实上,海登(Hayden)特别警告不要将“没有证据”认作“没有的证据”。比如说,洞壁上的绘画似乎是近期出现的,但事实上也可能只是由于绘画习惯的改变,之前也许画在外面,所以容易被水冲洗掉,近期转而画在洞穴深处了,因而得到长期保存。39
如果将来有人发现祭坛或其他宗教遗迹,经“鉴定”是6万年以前的文物,那又如何?既然罗斯会说6万年前的人类遗骨只是外表像人,而实际上是没有灵魂的“亚当前”动物,他会不会也说这些遗迹不过是没有灵魂的“亚当前”动物制造的、看起来像用于宗教敬拜的遗物呢?由此也可见他的立场是何其荒谬。
第三点:罗斯人为地把敬拜和其他形式的宗教行为分别开来。根据罗斯的说法,有些动物也会将其死者浅浅地埋葬,在这个过程中看不出明显的宗教敬拜。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始人埋葬死者和文物的行为也和动物一样,无关灵性。罗斯如此认为,这至少是毫无根据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斯不过是在竭力否认“6万年前”的人类成员有灵性。
第四点:罗斯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坚称保存至今的祭坛或其他宗教遗迹是宗教活动的必要条件,甚至是敬拜性的属灵能力的必要条件。
可是许多现代部落宗教在敬拜过程中都不用祭坛或宗教设施,这又当如何看待呢?这些人都没有罗斯所称的“灵性表现”或“敬拜能力”吗?不好说吧。
最重要的是,圣经中的真神禁止任何偶像崇拜(出20:4)或用凿出的石头做祭坛(出20:25)。摩西律法中的这些条文符合上帝对待他的子民的一贯做法。证据显示,人类最早是一神教,后来才堕落成偶像性的泛神教,这与圣经教导一致。40所以根据真正符合圣经的历史观,我们不认为挪亚的早期后裔会留下偶像形式的宗教遗迹或用石头凿成的祭坛。
罗斯怎么知道有些早期文物(如石器)是不是兼有宗教用途,甚至是崇拜的对象?例如,海登指出,尼安德特人用石头堆砌成几何图形,显示有仪式上的用途。41这类似于某些现代部落在象征性或宗教性行为中使用的石碓。即使我们容许罗斯人为地把“非敬拜性仪式”和“敬拜性仪式”区别开来,我们也怀疑他怎么知道这些行为没有包括敬拜。
罗斯相信,我们可以推算出亚当和夏娃是在7000年前到60000年前被造,这种信念被上述所有这些证据彻底推翻了。罗斯还宣称,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曾局限于中东一带,所以挪亚的洪水虽然是局部性的,却能够把他们完全消灭,只留下挪亚和他全家。(无论如何,鉴于人类的领土意识和迁徙本能,认为在数千年间没有人跨出一个狭窄区域的说法似乎是极端的诡辩,旨在挽救一个护教理论。)
相反,证据提示,现代人在过去10万年间已遍布各大洲(根据目前的测年法和罗斯所接受的进化论地质学)。也就是说,根据古老地球的假设来解释的化石证据,显示人类不是某一个时间突然起源的,现代人也从来没有全部局限在中东!
罗斯却强调这些化石不过外表上好像人类。就是说,无论其骨骼解剖、交流能力、文物、艺术等等看起来如何,他们实际上是低于人类的动物,没有能力进行宗教敬拜。所以,虽然罗斯看起来试图维护人类的独特性,但他实际上贬损了我们的独特性,因为他将我们的许多特征划给了他所称的不是人的动物。
罗斯人为地把古人类遗骸划分成“没有灵魂的亚当前动物”和“亚当夏娃的纯人类后裔”,其实 19世纪的种族主义者也曾把当代人进行过类似的划分,其随意性和无理性并无二致。
原始人的化石记录
人类是特别的创造,这一点罗斯和我们都同意;对于哪些应该划归人类,他却有不同的意见。即使我们认可进化论者的“测年”法,化石记录也明确地显示,许多教科书中所描绘的清晰的进化过程只存在于进化论宣传家的头脑中。马文∙卢比诺(Marvin Lubenow)指出,各种各样所谓的“猿人”并不能按照进化“年代”排成连贯的序列,而是呈现大幅度的年代重叠。42比如,智人化石的时间跨度包含了直立人化石的时间跨度,但后者据称是前者的祖先。
支离破碎的证据:卡达巴始祖地猿(Ardipithecus ramidus kadabba)个案分析
人们所称的过渡化石,不管是“猿人”还是其他生物,常常是基于支离破碎的化石证据。例如,《时代》杂志曾报道过一个卡达巴始祖地猿标本,经“鉴定”有560万年到580万年之久。43该杂志称新发现的这个标本已经能直立行走,处于所谓的“人类进化的黎明”时代:
“黑猩猩或任何现代猿类都是用四肢踯躅而行,但几乎可以肯定,卡达巴地猿大部分时间是直立行走的。从这个一英寸长的趾骨可以明确地看出来。”
可是究竟有多么明确?《时代》引述“露西”的发现者唐纳德∙约翰逊(Donald Johanson)的意见:
“除此之外,他怀疑这根520万年前的趾骨与其他的化石是否同属一类:它不仅在时间上与其他化石相隔几十万年,而且其发现的地点也距离其他化石10英里以外。”
注意这根趾骨是直立行走的主要“证据”,然而10英里以外的趾骨仍被认作同一个标本的一部分,这简直不可思议。44一位研究者曾说:“化石最善变,你想听什么歌曲,骨头都会给你唱。”45当你深入研究各种化石时,就会发现它们原来不是过渡类型,甚至连混合类型都不是。
人类的特别性
当你有了足够的化石证据,可以进行仔细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类的特别性。人与猿类动物(如南猿)截然不同,在这一点上我和罗斯的意见一致。但是仔细推敲时会发现罗斯关于许多其他“猿人”的说法是错误的。有人对匠人(Homo ergaster)、直立人(Homo erectus)、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和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的一系列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他们很可能是现代人的变异族群。46这与罗斯的宣称相抵触,罗斯把这些人种都划归没有灵魂的原始人。另一方面,被归于能人(Homo habilis)的许多标本和被称为鲁道夫人(Homo rudolfensis)的一个标本不过是南猿(已绝种的猿类)的亚型。47
表9.2:化石人类特征的分析结果总结。48 1. 体型,2. 体形,3. 行姿,4. 颌齿,5. 发育,6. 脑容量。H = 像现代人, A = 像南猿, I = 人猿之间,? = 无资料。
| 种名 | 1 | 2 | 3 | 4 | 5 | 6 |
| 鲁道夫人(H. rudolfensis) | ? | ? | ? | A | A | A |
| 能人(H. habilis) | A | A | A | A | A | A |
| 匠人(H. ergaster) | H | H | H | H | H | A |
| 直立人(H. erectus) | H | ? | H | H | ? | I |
| 海德堡人(H. heidelbergensis) | H | ? | H | H | ? | A |
| 尼安德特人(H neanderthalensis) | H | H | H | H | H | H |
近年来,许多进化论的专家都承认,“能人”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的分类,归入其中的化石不是直立人/匠人就是南猿,它成了“分类学的垃圾桶”。这种说法是弗莱德∙斯普尔博士在一次采访中提出来的,他是荷兰裔英国古人类学家,是《人类进化学杂志》(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的编辑之一。49
进化论学者Wood和Collard的分类结果(见表9.2)与稍早些的创造论古人类学家西格里德∙哈特魏格雪尔博士(Sigrid Hartwig-Scherer)的看法一致。哈特魏格雪尔是慕尼黑拉德魏格-迈克斯米兰大学(Lugwig-Maximilian University)人类学与人体遗传学院的研究员。她的结论是:直立人/匠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都属于同一个基本类型(创造类,见第七章),即人类(Hominidae)。同时她把阿法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湖畔南猿(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非洲南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粗壮南猿(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埃塞俄比亚南猿(Australopithecus aethiopithecus)、鲍氏南猿(Australopithecus boisei)以及可能存在过的始祖地猿(Ardipithecus ramidus)都划归另一个基本类型,即南猿类(Australopithecinae)。50
哈特魏格雪尔的分类发表于《单纯的创造》(Mere Creation)一书,罗斯在同一本书中也有著述,所以罗斯没有理由把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说成比人类低等。
两种对立的进化论观点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存在两种主要的进化论观点。一种理论叫做“走出非洲”或叫单一起源模式,甚至叫做“挪亚方舟模式”。该理论认为现代人从非洲发源,取代了更早走出非洲的进化程度较低的原始人。然而还有一种进化论观点,叫做“多地区”模式或“区域连续性”模式,甚至叫做“挪亚子孙”模式。该理论认为两百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原始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进化成了现代人。
这是古人类学家之间最激烈的争辩——两种理论的倡议者之间恶语相向。究其原因,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彼得∙昂德黑尔(Peter Underhill)说,“自负、自负、自负,科学家也是人。”罗斯和我一致认为,双方都是正确的——就他们相互之间的批评而言——因为人类根本没有进化!51
哈德魏格雪尔博士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个基本生物类型,考虑到巴别之后人类的迁徙模式,她提出一个单一起源模型:
“人类从非洲-阿拉伯盾出发,发生过三次迁徙。在第一波迁徙中,形态不明的人群向不同的方向分散,在非洲形成了典型的匠人形态,而在东南亚则形成了直立人的特征。第二波迁徙在相对闭锁的欧洲形成了尼安德特人的形态。最后,第三波迁徙在世界各地形成了现代智人。至于那些由不同更新世形态结合而成的混合特征,则可能是各波移民杂交所致,也可能是(多价?)祖先基因库中的隐性特征表达出来的结果,也可能两个因素都存在。”52
毫无疑问的智人竟然早于罗斯所认定的亚当年代?
对于毫无疑问的智人,罗斯也完全不着边际。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即使退一步,任凭他相信尼安德特人是“没有灵魂的亚当前动物”,但仅靠现代人遗骸所提供的证据,罗斯的观点也无以立足。首先,没有丝毫的证据提示有特别的人类在7000年前到60000年前这一段时间里出现。对罗斯更为不利的是,解剖意义上的现代人早在60000年以前已经存在——根据他所卫护的测年方法:
“‘这一带(南非克拉西斯河口)的化石在所观察到的各个方面上都是完全的现代人,’芝加哥大学的里查德∙克莱恩博士(Richard Klein)如是说,‘包括发育良好的下颌。’证据强烈支持其年代是在10万年前。”53
“……基本的颅骨构造至少10万年没变。”54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证据,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根据传统测年法认定的“早期人类”在认知能力上比现代人低下:
“单一起源模型认为现代智人出现于10万到20万年前,又有人认为西欧在3万到4万年前出现了现代智人,然而没有资料提示人类的语言能力在上述任何一个时间段内发生过重大质变。相反,考古学和古生物学证据似乎提示,复杂的语言能力很早就随着人属的进化而形成了。”55
长者智人
最近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智人化石,经“鉴定”有的16万年,有的15.4万年,这些都进一步反驳罗斯的人类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提摩太∙怀特博士(Tim White)1997年在亚的斯亚贝巴东北230公里以外的河头(Herto)村附近发现了这些化石。该发现登上了著名的《自然》(Nature)杂志的封面(2003年6月12日),该期杂志刊发了关于这项发现的多篇文章,都是进化论古人类学的领军人物写的。怀特和他的同事们撰写了化石研究报告;56另一篇文章是使用最新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得出的年代鉴定报告,并提供证据,说明其行为完全像人类;57还有一位进化论古人类学的领袖,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起源组的克里斯∙斯准格尔(Chris Stringer),也对该发现进行了深入的评论。58斯准格尔认为,该发现进一步支持关于人类起源的“走出非洲”模式,不支持与之对立的多区域进化模式(见上文“两种对立的进化论观点”)。
埃塞俄比亚这些骨骼残骸与“早先”的人类骨骼在解剖学特征上并非完全不相干,就是说,虽然他们明显地属于智人,但在某些解剖特征上却类似于“远古”人类。所以发现者建议他们的全名称为“长者智人”,提示他们是现代人类的一个亚种(或亚型)。这意味着,他们不仅明显地属于现代人,而且与罗斯主义者们试图贬低为非人类成员的类型(包括尼安德特人,见下)有遗传关系。
这些化石的确是智人,而不是非人的原始动物,这一点不容回避。他们的脑容量实际上比现代人的平均水平还高。澳大利亚墨尔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时代》引述进化论专家说:
“在埃塞俄比亚的河头村发现了最早的现代人头骨,这表明,与我们非常类似的人群在16万年前就已经在非洲的平原上游荡……
怀特教授说,河头的早期人类与河马、鳄鱼、鲇鱼和水牛一起生活在一个浅水湖里。他们还发现了600多件石器……
澳大利亚的人类学家对这些头骨与现代人的相似程度表示惊讶。新英格兰大学的考古学讲师斯提凡∙考利尔(Stephen Collier)说:‘看起来与现代人真是出奇地相似,在10年前你想都想不到如此现代的人类化石。’
地质学家吉姆∙包勒(Jim Bowler)曾在1974年发现了澳大利亚最早的人类残骸,即据称有四万年之久的芒枸人(Mungo man),他说埃塞俄比亚这些头骨太像现代人了,‘如果你给这个伙计穿上灰黑色的西装,他走在考林斯大街上也不会惹人注目。’
‘完全智人 (Homo sapiens sapiens)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系的考林∙格鲁夫斯(Colin Groves)如是说,‘新样本正是我们预想中的智人在分化出种族特征之前的样子。’”59
这些标本不仅在解剖上无疑是现代人,而且他们拥有无可争议的人类文化特征,如殡葬习俗和屠杀大型动物的做法。进化论者称“他们的技术水平是中石器时代和晚期阿舍利(Acheulean)时代的有趣结合。”60
对长者智人年代范围的鉴定被认为“很可靠”,所使用的技术是一种基于氩同位素的放射性测年法(氩-40/氩-39)。我们在第十二章将显示,这些测年法并不可靠,但问题是罗斯接受这一套。这样就把更多的无可置疑的现代人远远地定位于六万年之前了(六万年是罗斯人为地为亚当设置的年期)。
罗斯辩称,所有早于六万年前的遗骸都不过是在解剖上和文化上似乎是人,事实上却是没有灵魂的“亚当前动物”。但这显然是空抓稻草,玩弄人为的主观臆测。
线粒体夏娃
现在我们看分子生物学和(据此得出的)一对所谓的现代人的祖先。罗斯对线粒体DNA的证据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GQ:111-112):
“晚近的年期排除了现代人从另一种两足灵长动物进化而来的可能性(意味着人类必然是特别创造的)。”
其实不然。既然罗斯如此偏爱科学家的见解,他也应该知道,传统的科学家中即使有人不否认从前可能有过神灵的干预,也没有人认同把线粒体DNA当作几十万年前亚当和夏娃被直接创造出来的证据。“非洲夏娃”和“Y染色体亚当”的说法只表示所有现存的人类都来自同一个谱系,而丝毫不能否认其他人类谱系曾经存在过的可能性,只不过这些谱系都灭绝了。61
尼安德特人
这是最有名的“猿人”,其名字来自德国的尼安德谷(“特”在德文中就是山谷),第一个化石样本就是1856年在那里出土的。该山谷的名称来源于17世纪的纽幔牧师(Joachim Neumann),因为他经常在那里散步。“纽幔”的意思是新人,希腊文译作“尼安德”,这也是他的笔名。尼安德特人刚被发现的时候,德文的拼法是Neanderthal,到了1904年德文简化成了Neandertal,但是尼安德特人的正式科学名称仍然为Homo sapiens neanderthalensis (作为智人的一个亚种)或Homo neanderthalensis(若作为一个不同的种),因为命名时的拼写方法必须保留。
线粒体DNA(mtDNA)
这种DNA位于细胞的“发电厂”,即线粒体里,与细胞核内的主要DNA不同。一般来说,我们只从母亲那里获得mtDNA,尽管也有例外。罗斯辩称(GQ113-114):
“最近发现的尼安德特人DNA印证了施瓦茨和塔特撒尔的结论,即人类不是尼安德特物种的后裔,也与他们没有任何生物学关系。”
然而他给的参考文献与他所说的相抵触,因为该文献在标题中就称尼安德特人为“灭绝的人类”。62 罗斯并不在意这一点,他又进一步引述著名古生物遗传学家斯凡特∙帕伯(Svante Paabo)的团队在《细胞》杂志(Cell)上发表的研究:
“该科研团队的某些成员和另外几名科学家又对同一骨架的另一个片断进行了分析,发表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论点。63 他们的结果与第一次研究基本相同,结论是:他们的分析‘不支持尼安德特人在现代人的基因库中留下了mtDNA的观点。’”64
然而,他所引用的关于mtDNA的这一证据始终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评估,其可靠性很值得怀疑。65 仅靠一个标本就得出如此重大的结论,这在统计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分子生物学家约翰∙马可斯博士(John Marcus)对帕伯文章中的一副图做出如下观察:
“该图好像让人认为尼安德特人的序列介于现代人和黑猩猩的序列之间,并可能进一步给人一种印象,即尼安德特人是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一个环节。然而,仔细看来并非如此。从图上的标记可以看出,该图显示人与人、人与尼安德特人以及人与黑猩猩之间序列差异的数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给出尼安德特人与黑猩猩之间序列差异的分布。在这篇文章里,群体间的比较一共有四种,我不明白为什么作者没有显示最后一种比较。然而,根据我所做的DNA差异分析,很容易看出尼安德特人与这两个黑猩猩序列之间的差别,实际上超过了现代人与黑猩猩的序列差别。我使用了不同的人类序列进行计算,结果表明,任何一个人类序列与黑猩猩序列的相似程度都比尼安德特人与黑猩猩序列的相似程度高。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DNA序列与黑猩猩的DNA之间的距离差别不是很大,这一事实提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同属一个物种。尼安德特人与黑猩猩的关系显然不比任何人更近。如果说有差别的话,尼安德特人离黑猩猩实际上更远。66
况且,帕伯自己也称他的论文被误解了,他的数据不可能证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没有遗传关系。67 首先,因为这是线粒体DNA,它最多能证明尼安德特人的母系没有在现代人基因库中留下线粒体DNA,但不能排除尼安德特人的父系在现代人基因库中留下细胞核基因的可能性。比如在战争中,尼安德特男人可能打败过现代人,并让“摩登”女性怀孕。再者,迁徙也可能主要涉及男人。68
此外,进化论人类学家沃尔帕夫(Wolpoff)也同意,尼安德特人的mtDNA没有超出现代人类的变异范围。69 现代人的mtDNA变异范围与其他的灵长目动物相比是很窄的,即使加上了尼安德特人,也只把人类的变异提高到正常水平。
最后,尼安德特人和现存人类的mtDNA与黑猩猩的mtDNA 之间的差异是在相同的碱基位点上。沃尔帕夫认为,这一事实表明尼安德特人并不是独立于现代人之外的一个物种。在本书初版发表多年后,对更多资料的细致研究显示,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跟我们的很相似。70 这包括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共有的一个语言能力基因。71
因变异热点而形成的差异
生物化学家兼神经科学家大卫∙德魏特博士(David DeWitt)对尼安德特人的DNA进行了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在mtDNA上的差异集中于D-环上的突变热点区域。72但是我们与黑猩猩的差异不在这些突变热点上。他写道:
“有的研究者主张尼安德特人自成一个谱系,其主要的原因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在mtDNA上有许多差异。然而,正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突变热点,这说明他们关系密切。因为有些位点保持不变,而另一些位点则变异频繁,所以你不能靠简单的差异计数来说明问题。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异计数比现代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异计数多一些,但这并不说明尼安德特人不是人,或者说尼安德特人与人类在遗传上有分别。此外,顾提莱孜(Gutierrez)指出,以前的研究,比如克灵(Kring)的研究,存在群体偏差。他们用的大多是欧洲人(DNA序列很相似),这就让尼安德特人显得不一样了。
还有一点,尼安德特人的mtDNA序列在现代人群中见不到,这并不说明他们没有通婚过。比如,在美国,我们知道有些美洲原住民与欧洲移民通过婚,然而要发现线粒体里的证据就难了。”73
德魏特指的是顾提莱孜等最近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显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现代人与现代人之间两两比较的距离分布比之前研究所提示的有更多的重叠。”他们还说:“考虑到这些因素(即突变热点的高速置换变异)的时候,尼安德特人独特的分类学地位就没有多少支持了。”74
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混血
如果尼安德特人与现代长相的人能杂交,那么他们就必定属于同一个物种。最近有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曾经与现代人在中东并肩生活了十万年(进化时间),制造的石器也几乎相同。75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杂交后代在许多地区被找到,76包括葡萄牙的一具儿童骨骼77和罗马尼亚一个熊洞里的成人下颌骨。78不难看出,尼安德特人完全是人,而且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在欧洲融合了。79
颅骨特征
罗斯称,尼安德特人有独特的鼻骨分化,所以不可能与现代人有什么关系(GQ:113)。然而这些特征在人类也有,从非洲布须曼人到爱斯基摩人,各个种族中都可见到。80而且罗斯的说法本来毫无意义:虽然罗斯抓住早先的发现,当作事实,但后来证明这是基于错误的重塑,现在已经否定了。81
根据对牙冠资料的统计分析,82人们注意到,克拉皮纳(克罗地亚)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差别一般地大于现代人种之间的差别。然而这里也有高度的重叠。尼安德特人与现代西伯利亚东北人的相似程度大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与任何现代人种(除了中国人)的相似程度。83类似地,克拉皮纳尼安德特人与现代西伯利亚人之间的差别小于澳大利亚土著与其他任何现代人种(除了西伯利亚人)的差别。所以,如果按照罗斯的逻辑,我们把尼安德特人看作“没有灵魂的非亚当后裔”,那么我们就也应该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看作没有灵魂的非亚当后裔。显然,只有种族主义者才会接受这样的结论,但这是罗斯教导的逻辑推论,尽管他自己也不会同意。
尼安德特人牙齿以外的特征也与罗斯的观点相抵触。沃尔帕夫列举了尼安德特人特有的(至少在其他更新世群体中罕见)的18项骨骼特征。84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中有一大部分也见于尼安德特之后的欧洲人种中,有些甚至见于现代欧洲人中。这一点有力地否定了罗斯所谓的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分别被造、互无关联的观点。
手的灵巧程度
尼安德特人手上的肌肉发达,指头较宽,看起来肯定与“现代”手不同。但他们的双手与现代人的手同样灵巧,甚至更灵巧。这是最近由加州圣贝纳迪诺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学系和北达州法戈的北达科他州立大学考古技术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现的。他们研究了在法国拉佛拉西(La Ferrassie)发现的化石,根据对化石骨骼的扫描图像,完成了对尼安德特人拇指和食指的最新三维电脑模拟。他们就像最先进的动画制作师一样,把图形转换成了完全动态模型。
他们显示,尼安德特人的拇指可以轻易地接触食指尖端。对握的拇指是人类独有的灵巧性标志。事实上,研究人员对骨骼的活动范围选择了相当保守的估计,所以尼安德特人的手如果与普通的现代手有区别的话,也只会是更灵巧。“鉴于尼安德特人的大多角骨——掌骨——第一指骨关节的开放造型,尼安德特人的拇指可能都比现代人的拇指更灵活。”85
文化证据
罗斯不赞同把音乐、器具使用、艺术和殡葬习俗等作为尼安德特人之真实人性的依据,因为他认为动物也有类似的行为(GQ:110)。事实上,根据遗迹推测出来的尼安德特人的行为,与最聪明的动物的简单行为相比,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尼安德特人表现出复杂的、有预谋的、有目的的行为。这方面证据很多,86包括:带有礼仪和审美考量的工具和石器;将遗体在复杂的墓穴中按照预先设计的几何图形摆放;从远处采集用于工艺美术的赭石;“高科技万能胶”;87 符号思维;88发达的化装艺术。89
小结
关于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差异是否足以使尼安德特人成为一个独立的物种,古人类学家远远没有达成一致。把人科所有的“物种”合并在一起,他们在脑容量和体重上的变异系数,并不比现代智人的变异系数大。一般认为这表明人科各“种”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种内变异。90该现象也支持伍德和科拉德在关于人类形态学的综述中发表的见解。91
直立人
根据多性征形态学分析可以看出,直立人是人类的另一个变种(见表9.2)。他们的颅顶大小与现代人的重叠。92爪哇是最早发现直立人的地方,从那里出土的一件新标本“否定了有关人类脑容量进化的一个假说。”93该标本具备一个“显著的现代特征”,94即高度弯曲的颅底。哈佛大学古人类学家丹∙利伯幔说:“这是一项重大发现,因为这是第一个颅底相当完整的直立人,而它看起来很现代。”95
利伯幔当然把直立人看作人类的祖先,但这一证据也符合直立人不过是神所创造的人类的一个变种的看法。
沃尔帕夫等表示,从各种人类颅骨的特征来看,现代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甚至与直立人肯定杂交过。96
直立人的文化技能有力地展示着他们的人性。甚至有迹象表明他们有航海的能力!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小岛上发现了一些被屠杀的大象的骨头,这个岛太小太荒芜,不可能有人居住,根据工具和年期鉴定,杀象者只能是直立人,但是这个岛需要乘船跨越大片的深海才能到达。97这说明直立人曾经跨岛迁徙,岛与岛之间的海峡从数公里到数十公里,而且水域很深。直立人旅行过的岛屿包括龙目岛、巴厘岛、松巴哇和弗洛雷斯,98他们显然穿越了这些岛之间的海峡,提示他们至少有某些航海技能。根据罗斯所接受的传统测年法,这一切都是在80万年前。文章的作者说:“而且,结果显示,在80万年前到90万年前这段时间内,这一带的直立人获得了穿越海洋的能力。”99
主张人类“多区域进化”的著名科学家沃尔帕夫强调直立人的航海技术,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意思的是,极力倡导“走出非洲”理论的斯准格尔说这样的航海技术表明直立人“更像人,和我们一样。”
但是根据罗斯的说法,直立人是亚当前的无灵魂动物。然而这些所谓的亚当前动物却具备一项明确地属于人类的技能——设计出能够跨越数十公里洋面的船只! 这进一步证明罗斯把人类遗骸划分为“亚当后裔”和“亚当前无灵魂的动物”的做法完全是主观武断的。
结论
圣经的历史观在许许多多方面与罗斯的历史观背道而驰,其中最重要的是时间表,因为根据圣经中的族谱推算出的人类历史比罗斯的大爆炸年代表所能容许的人类历史要短许多。
罗斯的理论对圣经人类学还有其他方面的损害,其中一点就是关于种族起源的错误认识。罗斯教导人们,上帝的介入造成了种族差异,而后者正是诸多偏见的源头——但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所谓人“种”的生物学/遗传学基础纯属无稽之谈。另一点就是说尼安德特人比人类低等。尽管尼安德特人有许多人类性征,罗斯却否定这些性征为人类所特有,模糊了人类与动物的分别。
最后,罗斯为亚当所定的年代范围,其下限晚于完全现代的智人。更糟的是,他的年代范围甚至提示,澳大利亚土著在澳大利亚生存的时间可能早于挪亚,甚至早于亚当,所以罗斯的神学隐含着澳大利亚土著不是人的可能性。虽然罗斯本人并非种族主义者,但他错误地信任漫长年代测年法,而非圣经,其逻辑后果就成了种族主义。
参考与注释
- G.L. Archer Jr., Encyclopedia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2), p. 40.
- Ibid. Gleason Archer 指出这一点。
- 见 G. Miller, “Septuagint”, www.christian-thinktank.com/alxx.html, January 30, 1995.
- 关于采用马索拉文本而非被修改过的七十士译本的原因,见P. Williams, “Some Remarks Preliminary to a Biblical Chronology”, J. Creation 12(1):98–106 (1998); creation.com/chronology.
- G.F. Hasel, “The Meaning of the Chronogenealogies of Genesis 5 and 11”, Origins 7(2):53–70, (1980); www. grisda.org/origins/07053.htm.
- 注意亚伯拉罕并非他拉的长子。创12:4记载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也是在他拉死后不久,他拉死时205岁(创11:32),两者之差(205 – 75)即他拉生亚伯拉罕时的年龄,实际上是130岁,而非70岁(Ussher似乎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现代史学家)。创11:32提到三个儿子,70岁是他拉生长子(可能是哈兰)时的年龄。
- J. Barr, letter to David C.C. Watson, 1984.
- D.A. Young, Christianity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2), p. 19.
- 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Books I–IV (Cambridge, MA: Harvard Press, 1930), p. 73,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 242.R. Young, Analytical Concordance to the Holy Bible, 1879; 8th edition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39), p.210. 约瑟夫算出创造的日期是公元前5555年,因为他的资料主要是LXX里夸大了的年龄(根据LXX,创造日期应该在公元前5508-5586)。
- Josephus,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3):3–4, www.ccel.org/j/josephus/works/ant-1.htm.
- 见注6。
- Josephus, Antiquities 1(6):5.
- G.F. Hasel, “The Meaning of the Chronogenealogies of Genesis 5 and 11”, Origins 7(2):53–70, (1980); www.grisda.org/origins/07053.htm.
- D.A. Carson, Exegetical Fallacies, 2n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96), p. 60.
- G.F. Hasel, “The Meaning of the Chronogenealogies of Genesis 5 and 11”, Origins 7(2):53–70, (1980); www.grisda.org/origins/07053.htm.
- A.G. Fruchtenbaum, personal communication, November 7, 2000.
- J. Sarfati, “Cainan: How Do You Expla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uke 3:36 and Genesis 11:12?” creation.com/cainan.
- 又见T.R. Freeman, The Genesis 5 and 11 fluidity question, J. Creation 19(2):83–90, 2005, creation.com/fluidity; J. Sarfati, Biblical chronogenealogies, J. Creation17(3):14–18, 2003, creation.com/chronogenealogy.
- N.L. Geisler and Wm. E. Nix,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revised and expanded (Chicago, IL: MoodyPress, 1986), p. 390–391.
- 见本章注17。
- “China”,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3:230, 15th ed. (1992).
- E.R. Nelson, R.E. Broadberry, and G.T. Chock, God’s Promise to the Chinese(Saint Louis, MO: Concordia, 1997).
- H. Ross, “Genesis One, Dinosaurs and Cavemen”, Reasons to Believe, http://reasons.org/kidsspace/dinocave.shtml?main, accessed March 15, 2003.
- C. Wieland, “Living for 900 Years”, Creation 20(4):10–13, (1998); creation.com/900.C. Wieland, “Decreased Lifespans: Have We Been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J.Creation 8(2):138–141,(1994); creation.com/lifespan.
- Bodnar et al., Science 279:349–352, (1998).
- www.reasons.org, December 5, 2002.
- M. Eriksson et al., “Recurrent de novo Point Mutations in Lamin A Cause Hutchinson–Gilford ProgeriaSyndrome”, Nature 423(6937):293–298, (May 15, 2003).
- Josephus, Antiquities 1(6):4. 约瑟夫写道:“希伯生约坍和法勒,法勒得名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各族正在分散成各国。法勒在希伯来文中就是分裂的意思。”
- J. Calvin, Genesis, 1554 (Edinburgh, UK: Banner of Truth, 1984), p. 324. 加尔文写道:“在他(摩西)提到闪的第三个儿子亚法撒之后,他又提到法勒,亚法撒的曾孙,在法勒的时代出现了语言的分化。”
- C.F. Keil and F. Delitzsch, Commentaries on the Old Testament, n.d., 德文原版发表于19世纪,英文译本出版者Eerdmans, Grand Rapids, MI. 《五经》1:171: “在亚法撒的子孙中,希伯的长子得名法勒,因为在他的时代因为建巴别塔的缘故,地(即地上的人民)被分裂了。”
- H.C. Leupold, Exposition of Genesis(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42), 1:378. “法勒是‘分裂’的意思,因为在他的时代地被分裂了(niphlegah),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语言混乱。”
- D. Batten, “Where Are All the People?” Creation 23(3):52–55, (June–August 2001); creation.com/people.
- W.J. ReMine, The Biotic Message(St. Paul, MN: St. Paul Science, 1993).
- H. Ross, “Genesis One, Dinosaurs and Cavemen”, Reasons to Believe, http://reasons.org/kidsspace/dinocave.shtml?main, accessed May 20, 1998.
- S. O’Connor, “Carpenter’s Gap Rockshelter 1: 40,000 Years of Aboriginal Occupation in the Napier Ranges,Kimberley, WA”, Australian Archaeology 40 (June 1995).
- J. Allen, “A Matter of Time”, Nature Australia 26(10):60–60 (Spring 2000).
- H. Ross, “Genesis One, Dinosaurs and Cavemen”, Reasons to Believe, http://reasons.org/kidsspace/dinocave.shtml?main, accessed March 15, 2003.
- H. Ross, “Genesis One, Dinosaurs and Cavemen”, Reasons to Believe, http://reasons.org/kidsspace/dinocave.shtml?main, accessed March 15, 2003.
- B. Hayden, “The Cultural Capacities of Neandertals: A Review and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HumanEvolution 24, (1993), p. 124–125.
- W. Schmidt,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New York: Cooper Square, 1971).
- B. Hayden, “The Cultural Capacities of Neandertals: A Review and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HumanEvolution 24, (1993), p. 121.
- M. Lubenow, Bones of Contention(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s, 1992).
- M.D. Lemonick and A. Dorfman, “One Giant Step for Mankind”, Time magazine cover story (July 23, 2001).
- J. Sarfati, “Time’s Alleged ‘Ape-man’ Trips Up (Again)” J. Creation 15(3):7–9 (2001); creation.com/kadabba.
- J. Shreeve, “Argument Over a Woman”, Discover 11(8):58 (1990).
- B. Wood and M. Collard, “The Human Genus”, Science 284(5411):65–71 (1999).
- J. Woodmorappe, “The Non-transitions in ‘Human Evolution’ — on Evolutionists’ Terms”, J. Creation 13(2):10–13 (1999); creation.com/non-transitions.
- 本表出自注释44。
- 见录像片The Image of God, Keziah Productions.
- S. Hartwig-Scherer, “Apes or Ancestors?” chapter 9 of Wm. A. Dembski, Mere Creation: Science, Faith andIntelligent Design(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 关于走出非洲模式和区域连续性模式的解释,以及圣经中的相关论述,见C. Wieland, “No Bones about Eve”, Creation 13(4):20–23 (September–November 1991); creation.com/eve2; 及 S. Hartwig-Scherer, “Apes or Ancestors?” chapter 9 of Wm. A. Dembski, Mere Creation: Science, Faith and Intelligent Design(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 Ibid., p. 229–230.
- R. Lewin, Human Evolution(Cambridge: Blackwell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1993), p. 153.
- W.A. Neves et al., “Modern Human Origins as Seen from the Peripherie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37:132 (1999).
- L.A. Schepartz, “Language and Modern Human Origins”, 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36:91–126 (1993).
- T. White et al., “Pleistocene Homo sapiens from Middle Awash, Ethiopia”, Nature 423(6941):742–747 (June12, 2003).
- D. Clark et al., “Stratigraphic, Chron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texts of Pleistocene Homo sapiens fromMiddle Awash, Ethiopia”, Nature 423(6941):747–752 (June 12, 2003).
- C. Stringer, “Human Evolution: Out of Ethiopia”, Nature 423(6941):692–695 (June 12, 2003).
- S. Cauchi, “Fossils Find Writes New Chapter in Our Narrative”, The Age(June 12, 2003): p. 1.
- 见注释55和56。
- 有关进化论思想的确切描述,以及“线粒体夏娃”其实晚得多的证据,参见C. Wieland, “A Shrinking Date for ‘Eve,’ ” J.Creation 12(1)1–3 (1998), creation.com/eve;“Mitochondrial Eve and biblical Eve are looking good: criticism of young age is premature”, J. Creation19(1):57–59, 2005; creation.com/eve3.
- P. Kuhn and A. Gibbons, “DNA from an Extinct Human”, Science 277:176–178 (1997).
- M. Krings, A. Stone, R.W. Schmitz, H. Krainitzki, M. Stoneking, and S. Pääbo, “Neandertal DNA Sequences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Cell 90:19–30 (1997).
- Ibid., p. 5584.
- M.L. Lubenow, “Recovery of Neandertal mtDNA: An Evaluation”, J. Creation 12(1):87–97 (1998).
- Ibid., 引述J. Marcus 与M. Lubenow的通信。
- S. Pääbo interview on television/video, Neanderthals on Trial, Nova, 2002.
- 见注释63。
- M.H. Wolpoff, Paleoanthropology, 2nd edition (Boston, MA: McGraw-Hill, 1999), p. 759.
- R.W. Carter, Neandertal genome like ours (There may be Neandertals at your next family reunion!) creation.com/neandertal-genome-like-ours, 1 June 2010; based on Green, R.E., et al., A draft sequence of theNeandertal genome. Science 328:710–722, 2010.
- P. Borger and R. Truman, The FOXP2 gene supports Neandertals being fully human, J. Creation 22(2):13–14, 2008; creation.com/foxp2.
- W. Skinner and D. DeWitt, “The Neandertal’s Place in Human History”, Virginia Journal of Science 51(2):83(2000).D. DeWitt and W. Skinner, “Rate Heterogeneity and Site by Site Analysis of mtDNA Suggests Neanderthals andModern Humans Share a Recent Common Ancestor”, Discontinuity p. 31, 2001.
- D. DeWitt, personal communication, May 19, 2003.
- Gutierrez et al., “A Reanalysis of the Ancient 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s Recovered from NeandertalBones”, Mol. Biol. Evol. 19:1359–1366 (2002).
- B. Bower, “Neandertals and Humans Each Get a Grip”, Science News 159(6):84 (2001).
- E. Trinkaus and P. Shipman, The Neandertals — Changing the Image of Mankind(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93), p. 391.
- B. Bower, “Fossil May Expose Humanity’s Hybrid Roots”, Science News 155(19):295 (1999).
- J. Amos, “Human Fossils Set European Record”,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1/hi/sci/tech/3129654.stm, September 22, 2003; based on E. Trinkaus et al., “Early Modern Human Cranial Remains from thePetera cu Oase, Romani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03 (in press); E. Trinkaus et al., “An Early ModernHuman from the Petera cu Oase, Romani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2003.
- Thompson, Andrea, Humans and Neanderthals Might Have Interbred, Livescience.com, 30 October 2006.Soficaru, A., Dobo, A and Trinkaus, E., Early modern humans from the Petera Muierii, Baia de Fier, Romania,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1073/pnas.0608443103,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3 November 2006.
- M.H. Wolpoff, Paleoanthropology, 2nd edition (Boston, MA: McGraw-Hill, 1999), p. 755–756.
- R.G. Franciscus, “Neandertal Nasal Structures and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Specialization,’ ” Proceedings 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USA) 96:1805–1809 (1999).
- A.J. Tyrrell and A.T. Chamberlain, “Non-metric Trait Evidence for Modern Human Affinities and theDistinctiveness of Neanderthal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34:549–554 (1998).
- Ibid., p. 550.
- M.H. Wolpoff, Paleoanthropology, 2nd edition (Boston, MA: McGraw-Hill, 1999), p. 756.
- W.A. Niewoehner, A. Bergstrom, D. Eichele, M. Zuroff, and J.T. Clark, “Manual Dexterity in Neanderthals”,Nature 422(6930):395 (March 27, 2003).
- B. Hayden, “The Cultural Capacities of Neandertals: A Review and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HumanEvolution 24:113–146, (1993).
- J. Viegas, “Neanderthals Made High-tech Superglue”, Discovery News(January 16, 2002); “Neanderthals‘Used Glue to Make Tools,’ ” http://news.bbc.co.uk.
- J. Sarfati, “Neandertals were fully human in thinking: Symbolic items show human cognition and symbolicthinking”, creation.com/nean-thought, 30 August 2006.João Zilhão and 5 others, “Analysis of Aurignacian interstratification at the Châtelperronian-type site andimplications for the behavioral modernity of Neandertals”, PNAS 103 (33):12643–12648, 15 August 2006 |10.1073/pnas.0605128103.
- R.W. Carter, The Painted Neandertal Ancient cosmetics are upsetting evolutionary stories, creation.com/thepainted-neandertal, 20 May 2010; João Zilhão et al., Symbolic use of marine shells and mineral pigments by Iberian Neandertal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USA)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11 January 2010.
- M. Henneberg and J.F. Thackeray, “A Single-lineage Hypothesis of Hominid Evolution”, Evolutionary Theory 11:31–38 (1995).
- B. Wood and M. Collard, “The Human Genus”, Science 284(5411):65–71 (1999).J. Woodmorappe, “The Non-transitions in ‘Human Evolution’ — on Evolutionists’ Terms”, J. Creation13(2):10–13 (1999); creation.com/non-transitions.
- J. Woodmorappe, ““How Different Is the Cranial Vault Thickness of Homo erectus from Modern Man?”J. Creation 14(1):10–13 (2000).
- A. Gibbons, “Java Skull Offers New View of Homo erectus”, Science 299(5611):1293 (February 28, 2003).
- Ibid.
- Ibid.
- Wolpoff et al., “Modern Human Ancestry at the Peripheries: A Test of the Replacement Theory”, Science 291(5502):293–297 (January 12, 2001); comment by E. Pennisi, “Skull Study Targets Africa-only Origins”, p. 231.
- Morwood et al., “Fission-track Ages of Stone Tools and Fossils on the East Indonesian Island of Flores”,Nature 392(6672):173–176 (March 12, 1998).New Scientist157(2125):6 (March 14, 1998); based on Morwood et al., (see previous reference).See also Creation 21(1):9 (December 1998–February 1999).
- R.G. Bednarik, B. Hobman, and P. Rogers, “Nale Tasih 2: Journey of a Middle Palaeolithic Raft”,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28(1)25–33 (1999).
- Ibid.
基于圣经的真实恐龙历史
恐龙的灭绝是世俗科学界的一大谜题。如果人们相信真实的目击证人在圣经中写下的地球历史,这就不再是个迷了。圣经中的记述如下:
- 陆地动物(包括恐龙)和人都是在约6000年前的第六个创造日被创造的,所以恐龙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 亚当犯罪,将死亡、疾病和凶杀带入世界。在此之前,恐龙不会死。
- 此后的1656年左右,发生了一场全球洪水(global Flood),毁灭了所有(没上方舟的)用鼻孔呼吸的陆地动物。不计其数的动物被快速掩埋,形成化石(fossils)。恐龙化石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
- 每一种动物,挪亚都带了一对(洁净的动物带了七只),进入远洋游轮一般大小的方舟(Ark)——动物中也包括恐龙。详细内容,见《挪亚方舟怎么装得下所有的动物?(How did all the animals fit on Noah’s Ark?)》
- 洪水之后的一段时间,恐龙的后代和人类曾一起生活过,似乎也有一些目击证人的记录,如约伯记40:15,而且世界各处都有关于龙的传说。
- 它们最终全部灭绝了,尽管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可能有人偶尔看到过恐龙,但未经确切证实。恐龙的灭绝可能与其他物种灭绝类似,也是由人类的猎捕、气候变化、食物稀缺、栖息环境的破坏等因素所致。
关于恐龙的真实历史,更多信息参见 问题与解答:恐龙(Q&A: Dinosaurs)
世俗(与圣经相对的)理论
不相信圣经的人尝试用各种理论解释恐龙的灭绝:
- 哺乳动物吃恐龙蛋。
- 在植物界进化出有麻醉药效的植物。
- 全球气候变冷/变暖
- 植物稀缺导致食草和肉食动物饿死。
- 大气中的氧分压降低。
大撞击理论
目前最“亮眼”的理论是地质学家瓦尔特·阿尔瓦雷斯(Walter Alvarez)于1980提出的,称一颗陨石在6640万年前撞击地球,导致一系列的气候聚变,如‘核冬’。这导致了恐龙和许多其他物种的灭绝。其证据是他所发现的遍及全球的高铱粘土层。他父亲路易斯(Luis),曾因亚原子物质研究获得196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帮助他推广这个理论。该理论现在已经在很多圈子中被视为‘既定事实’,并通过《与恐龙同行》(Walking with Dinosaurs)等“纪录片”深入大众。
“大撞击”理论的若干问题
《关于恐龙灭绝的巨大争议》是一部世俗著作,书中揭示了关于恐龙灭绝的陨石理论是如何在证据远远不足的情况下成为新教条的,(见 Carl Wieland写的书评Journal of Creation 12(2):154–158, 1998)。部分理由如下:
- 从进化论/漫长岁月论对地质记录的解释来看,灭绝并不是突然的。但是,恐龙在地质记录中的广泛分布,如果用挪亚洪水中形成的大量沉积物来解释,是非常合理的。
- 对光照要求高的物种存活了下来。
- 灭绝的年代与陨石坑的年代不吻合。
- 现代火山爆发即便会使温度一时下降,也不会导致全球性物种灭绝。
- 高浓度的铱被认为是陨石影响的主要证据,但实际上远没有像人们声称的那样被明确证实。
- 位于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半岛的希克苏鲁伯火山口被认为是撞击的残留证据,但是岩芯研究并不支持这是一个陨石撞击坑。
- 有些科学家不敢明确反对这个观点,似乎深怕会因为反对“核冬天”理论而被归为“核战争贩子”。
气象学家麦克·奥德(Mike Oard)的综述文章《恐龙的灭绝》【‘The extinction of the Dinosaurs’ (Journal of Creation 11(2):137–154, 1997)】解释道,许多恐龙化石的特征都与洪水相关,恐龙的脚印符合恐龙正在洪水中逃难的情况。奥德指出高浓度的铱可能是由于大型火山喷发所致,许多进化论者也是这么认为的。火山喷发一定是大洪水爆发的那一年的常见现象,这与“大渊的泉源”(创世记7:11)开裂有关。奥德认同,最大的铱浓度异常是由陨石在大洪水期间撞击地球导致:“从大气中落下的铱元素丰富的粘土只会在洪水间歇期积累。”
这解释了为何所谓的峰值岩层实际上是由几个峰值带组成,或者是分布在大范围的沉积层内。约翰·伍德莫拉普(John Woodmorappe)指出:
“在显生宙的记录中有三十多层铱的‘痕迹’。这些可以解释为(无论是源自地球还是外太空)当铱由天而降时,沉积速度有所减缓。这种现象不会对洪水说造成任何影响。”
也就是说,铱层代表洪水期间沉积过程的缓解阶段,而 “铱雨”本身在洪水期间则是比较恒定的。
K/T(白垩纪/第三纪)的分界
奥德也指出,被认为是标志着恐龙时代之终结的K/T分界,在全球也不是一致的,而且没有得到系统性的界定。在这个分界线附近发现的恐龙化石很少。有的时候这个论证是在绕圈子。举例来说,在地质柱中,K/T分界应该清晰地标明恐龙时代的结束,但是在很多地方,K/T界却是由最高层的恐龙化石确定的。另外,铱在K/T分界的分布被用来支撑阿尔瓦雷斯理论,但是在某些地区,K/T界却是根据铱的峰值确定的。
结论
圣经是合理地解释历史的唯一的系统框架,恐龙的历史也应在这个框架内理解。其他理论,即便现在看来光彩夺目、影响深远,也注定要失败。若忽视了关于创造和大洪水的唯一的的目击证据——圣经,所有的间接证据都毫无价值。
2009年5月21日更新:普林斯顿地球科学家格尔塔·凯勒(Gerta Keller)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恐龙并非因陨石而灭绝。(Princeton geoscientist Gerta Keller offers new evidence that meteorite did not wipe out dinosaurs)
几年前,我在新西兰南岛一所大学讲创造论的证据时,有一位观众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挑战。(我后来发现他是一位狂热的神导进化论者。)他问我,明明已经有文献记录,在一头现代鲸鱼身侧发现了后肢,我如何还能坚持自己的立场。我记得当时自己略感惊讶。这个发现如果是真的,肯定会令反对创造论的质疑人士大为兴奋自豪。也肯定会反复出现在头版,成为他们攻击维护创世记和圣经权威人士的武器,那么为何世界上的创造论组织从来不曾听闻?
当然,我知道有一些现代鲸类会有一对骨头嵌在组织里面,每个都是为了支撑骨盆壁,起到固定器官的作用。我知道进化论者一般都称这些微小但又有作用的结构为退化器官(“痕迹器官”)。他们选择相信这一对骨头是鲸类祖先盆骨的遗留,根据进化论观点,鲸的祖先曾经在大陆行走、奔跑。虽然这几条骨头都是有已知功能,雌雄不同,而且也没有与脊椎骨相连,他们依然选择这样认为。我也认识一些生来就多了一个指头、一根肋骨的人,但是没有进化论者会称我们是由六指祖先进化而来的。若是鲸生来多了一小块骨头,进化论者就会称这是返祖现象,是退化的肢体。

上: 照片显示格陵兰露脊鲸的骨骼(病态),小盆骨在下方。 引自 E.J. Slijper, Whales,2 图226, 第423页,经Routledge出版社同意。非经该社许可,不得复制。
下: 抹香鲸小盆骨的画图,有一更小的异常骨块与之融合,该异常结构被进化论者称为“股骨残余”,但这一骨块与任何陆生动物的腿骨相去甚远。

但若是从海里拉上一头后面拖着一条腿的鲸,这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不记得当时具体是如何回应的,但是我指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将对创造论理论模型的解释提出严肃挑战。我也表示怀疑,但挑战者强烈地肯定这个“发现”是真实的。我请他将相关文献发我,他也答应了。从此再也没有得到音讯,直到几年后我又回到这所大学开讲座。一位当地的基督徒医学专家站起来问问题,又提起了这个“鲸鱼后肢”的事情,称他自己当时也在场。后来交流如何,我有没有收到文献?我说我没有,又说我依然质疑那个发现。
当时,在前一次讲座上挑战我的神导进化论者没有露面。但是在接下来的研讨会上,他出现了。他手里捧着一位著名的人本主义斗士写的在伦理上和科学上都已经声誉扫地的反对创造论的书,挑战创世记的记载中的某些细节。他一定听说了我对“鲸鱼故事”的反应。借中间休息的机会,他上前来,在许多人面前告诉我现在可以为我提供那份文献。他说他是在著名进化论古生物学家罗伯特·巴刻(Robert Bakker)的畅销书《恐龙异说》(The Dinosaur Heresies)中读到的。
事情变得复杂了
一回到澳大利亚,我们就查找了这个出处。后来我们找到了,在该书的第317页,巴刻博士并没有标注来源,写道:
“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一头侧面长着一条后肢的现代鲸鱼被拖出海洋,大腿和膝盖的肌肉都是完整的。这些返祖后肢反映了五千万年前进化成为鲸鱼前的形态。”1
因为没有注明证实该说法的文献,我们便请了美国的同事联系巴刻博士,问他这个重大声明所依赖的证据。我们的同事回复说,巴刻告诉他,证据是斯里帕(Everhard Johannes Slijper)的书《鲸鱼》(Whales),据说书中还有一张长着全肢的鲸鱼图片。
斯里帕(1907-1968)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普通动物学的一位教授。他是全世界顶级的鲸鱼权威。他的经典著作《鲸鱼》第二章的标题是“进化和外形”。在书中,他提到了鲸鱼中有一块他称为“盆骨”的骨头,有30厘米(12英寸)长,“但是不像一般哺乳动物的骨盆,它不与脊柱相连。”这块骨头充当着固定雄性生殖器官的功能。斯里帕继续写道,有的时候“会有另一块小骨头附着在上面。”作为一名进化论者,他自然将这块小骨头解释为股骨的返祖现象,反应鲸类祖先的大腿骨。然而,他说在这些偶然的情况中,这块骨头一般也只有2.5厘米(刚刚超过1英寸)长,有时与盆骨“融合”。
注意,到目前为止,他一直都没有提及任何关于从鲸鱼侧身有“后肢”突出的说法。这个证据最多也只能说明有些鲸鱼(他也承认一般都在盆区有功能性的骨骼)偶然会带着一些与生俱来的不正常的小骨头。在鲸的这个解剖部位,指导正常骨骼发育的基因系统是十分复杂的。程序中的一个突变失误很容易造成一两块多余的骨头,而这些骨头难免要长在同一个区域,与正常骨骼或分离或融合。同样地,有些人生来就有多余的指头、肋骨、乳头等。如果多出来的骨头有两块,无论其外形如何扭曲、另类,热心的进化论者无疑会将第一块多余的骨头解释为股骨,第二块称为胫骨。没错,斯里帕将偶尔在他所谓的股骨上附着的第三个骨质结构称为胫骨。这种情况偶尔会出现在露脊鲸和抹香鲸中。
到此还没有什么大问题。然而我这种说法不能解释现代鲸鱼上出现的真正的后肢(无论是在体内还是在体外),因为真正的肢体显然有设计的特征。如果第一批鲸是创造而来的,这些显然就是多余的。好奇心催促着我们继续探索。
继续揭露神话
最接近他们所声称的、我们原本所要调查的现象的,是斯里帕写的:“因此,1956年在日本的鲇川滨捕鲸站,人们拖进了一头抹香鲸,长有一个5.5英寸的‘肉包’,里面包着一根5英寸的胫骨。1959年俄罗斯的一艘制造船也在白令海遇见了相似的情况。”但是都没有留下照片。暂且忽略这个证据的传说色彩,人们要用它证明什么?抹香鲸体型巨大——长至19米(62英尺)。相比之下,侧身上一个14厘米(5.5英寸)的“肉包”几乎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痘痘。肉包中间的骨头,可能有12.5厘米(5英寸)“长”。没有证据能合理将其归为“腿”。斯里帕称这个“肉包”中的骨头为“胫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进化论者可以随意将任何异常的骨头帖上标签,以符合他们的自然主义宗教。
鲸鱼化石有腿吗?
最近有很多人声称现代鲸鱼的化石祖先已经被发现,而且有些已经绝种的动物呈现出从用腿爬行的陆地动物过渡到今天的无肢鲸鱼的中间形态。
- 巴基鲸:被称为‘会行走的鲸鱼’——但是人们发现的这种动物的标本只有颌骨和头骨碎片。
- 龙王鲸:也被称为鲸鱼的祖先。它虽然有功能性的后肢,但这些肢体太小,无法用于行走,而且进化论者也称它们可能是用于在繁殖时抓持。
- 走鲸:有清晰的后肢,明显可以走路,是最近发现的候选化石——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个通过想象重构的动物不知道和鲸鱼的历史有什么关系,正如之前的文章(见参考文献)所述。
从鲸到人类的尾骨
即便这些记录不全的证据是真实的,鲸鱼侧身一个拳头大小的肉包,里面有一些骨质结构,这和著名进化论者巴刻的报告(前文引述的)也是很不一样。遗憾的是,这些消息对人们传达的信息是,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表明,有的现代鲸鱼生下来侧身就挂着完整的后肢!这个证明进化论的“证据”,似乎类似于偶尔会有婴儿生来在脊柱尾端有一个异常脂肪包。虽然这些包里面没有任何尾骨结构,而且往往这些结构并不在中线上,但它们还是经常被称为返祖,认为反映了一个进化前有尾巴的祖先!
在进化论信仰体系中,陆地动物进化成鲸所需要的改变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影响深远。正如进化论者安东尼·马丁(Anthony Martin)的解释:
“从原则上来说,这意味着一套新型运动系统(从行走到游泳)的发展,一套可以应对高密度介质(从空气到水)的生理机能,一套新的捕食方法和能够有效地在海面呼吸的功能。‘这种适应是通过身体的每一个部分的改变而获得的,尤其是头部……除了头部之外,要适应水生生活,身体的其余部分都会发生根本性的调整。”3
相反,现代鲸鱼的解剖,包括偶尔发生的小异常,从创造论的角度解释其起源,不存在任何问题。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创造者,在马可福音10:6中说道,人是在“起初创造”的时候被造的(不是在几十亿年之后出现的)。鲸和其他海洋生物则是在比人早一天的时候出现的。4 这对于能够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是轻而易举的事。
参考和注释
- R. Bakker, The Dinosaur Heresies: A Revolutionary View of Dinosaurs, U.K. edition, Longman Group, Essex, 1986; published in USA as The Dinosaur Heresies: New Theories Unlocking the Mystery of the Dinosaurs and their Extinction, Morrow, New York, 1986.
- E.J.Slijper, Whales, translated from Dutch by A.J. Pomera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U.K. edition Hutchinson, taken over by Routledge, London, UK), 2nd edition, 1979.
- Anthony R. Martin, Whales and Dolphins, Bedford Editions, London, p. 12, 1990.
- 渐进创造论者/罗斯主义者常常称进化论科学家所说的生物出现的顺序符合创世记的记载。然而,他们想要亲和的世俗科学家强调陆地生物是在鲸鱼之前出现的,而圣经的教导说,鲸鱼出现在陆地生物之前。扭曲释经学把创世记的‘日’强解成几十亿年,仍然无法绕过这个问题.
摘要
本文回顾了病毒的结构、功能及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结论是:病毒是非生物体,其作用类似于种子和孢子,其功能包括将所携带的基因从一个植物或动物转移到另一个植物或动物。病毒是促进生物多样性系统的一部分,多样性对生命至关重要。病毒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能将抗病能力从一个生物体携带到另一个生物体。大多数生活在宿主中的病毒都不会造成任何问题。病毒致病是由于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例如基因突变,或基因的意外移动,而并非源于一个特意设计来导致人类疾病和痛苦的系统。
导言
反对神创论的一个主要论据是:“一个仁慈的上帝为什么创造了致病的微生物,而它们的唯一功能似乎是导致疾病和痛苦?”挪亚洪水事件经常被人批判,他们声称,上帝一定希望世界上有致病病毒,它们今天既然存在,一定是因为上帝把它们带上了方舟。1一位进化论者将这一观点总结如下:
“虽然这个地球和其上的动植物有非常美丽的一面,但也有很丑陋的一面。当然,美与丑是人的观念,正如认为必须要以智慧的创造者来解释世界的属性和存在一样,这都是人的观念。无数肮脏的生物学现实用进化论可以完全地理解,但若用一位无限聪明、智慧和慈悲的创造者来解释,则令人费解。每一个生物,包括植物,都必须与疾病和寄生者生物斗争。致病的细菌和病毒像百科全书那样丰富,其中大多数除了感染其他生物、折磨它们或缩短它们的寿命以外,没有任何有益的‘目的’。”2
提起“病毒”这个词,使人想起病毒瘟疫,例如1918年的流感,导致大约2000万人丧生。3公众的普遍观念是,病毒的唯一作用就是引发疾病。许多常见的疾病都是由病毒引起的,例如唇疱疹、乙型肝炎、疱疹、黄热病、病毒性脑膜炎、水痘、感冒、单核细胞增多症、腮腺炎、狂犬病、小儿麻痹症、带状疱疹、天花、疣病、病毒性肺炎、艾滋病和某些癌症。
病毒也会影响免疫系统,使免疫系统攻击生物自己的肌体,从而带来健康问题,这就是一些自体免疫性疾病,如糖尿病,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病毒导致自体免疫性疾病的一个机制,就是将其DNA片断留在宿主细胞内,进而将病毒蛋白(免疫识别指纹)插入宿主细胞膜。当这些细胞繁殖时,它们的子细胞也具有这些独特的标记。白细胞就可能误将这些自身细胞认作外来细胞,进而发动错误的攻击。在乙型肝炎病人中,免疫系统攻击肝细胞所造成的损伤可能要比病毒造成的损伤更大。病毒甚至会造成某些癌症,如白血病,也会危害牲畜和庄稼,是农民的大敌。
虽然病毒是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才被发现的,但至今已经发现大量的证据,表明它们在生态系统中有几个重要的作用,病毒对于生命也是至关重要的。若没有病毒,我们正在经历的基因革命不可能发生。它们还有许多积极的功能,都是人们刚刚开始研究和理解的。
病毒的发现
科学家首次发现并开始研究这个神秘的“生命”形态时正值世纪之交。研究人员发现,如果从某些患病的动物和植物身上提取的液体被溶解在一种溶剂中,用当时最细的过滤器(常使用未上釉的陶瓷盘)过滤,滤液仍然能够引起疾病。4俄罗斯科学家伊凡诺夫斯基(Dmitri Ivanovski)发现感染烟草花叶病植物的滤液还是能够感染健康的植物。5

图1. 腺病毒模型,衣壳为二十面体,有20个三角形的面,12个顶点和30条边(按照Luria 等人的图画)63
荷兰植物学家比杰林克(Martinus Bijerinck)称之为传染性液体生命。这种液体含有导致传染的物质,现在被称为病毒,即拉丁词“毒”。起初,许多研究人员认为疾病必定是由毒素引起。比杰林克不赞同这一理论,他发现树汁的致病能力在连续传递许多代后并不减弱。这表明病原体能够在植物中繁殖,否则每传递一代它都会减弱。其他人推测这种疾病的病原体是细菌孢子,但远比已经发现的细菌孢子要小。最终研究人员意识到,疾病的罪魁祸首是一种非细胞的“生命”形式,它可以穿过细胞壁和细胞膜而进入细胞的原生质。
1931年,伦敦国立医学研究所的威廉·艾福德(William Elford)发明了一个新的过滤技术,借此研究人员认识到病毒是何等微小。6我们现在知道一个病毒和一个动物细胞的大小相比起来就像篮球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直到1930年代电子显微镜被发明以后,科学家才能最终看到病毒。
1930年代中期,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温德尔•斯坦利(Wendell Stanley)将病毒混入溶剂,然后让溶剂挥发,发现病毒形成了晶体。既然病毒能够结晶,就表明所有的病毒单位都有几乎相同的形状、重量、电荷和化学特征。许多病毒,包括呼肠孤病毒科、细小病毒科和虹彩病毒科是规则的正二十面体,有20个三角形的面,12个顶点和30条边(图1)。7这一证据清楚地表明,病毒不像任何已知的生命,而更像无生命的物质。有些病毒是对称的,有些像长圆管,还有的病毒形状如微型火箭。斯坦利的发现公布不久就引发了病毒是生命还是无生命的辩论。今天,我们认识到,病毒是基因的携带者,正如脂蛋白就是人体循环系统中胆固醇和脂肪酸的携带者一样。
病毒的结构

图2.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示意图。GP120和GP41是糖蛋白的两个组件,镶嵌在在脂质膜上。外膜和蛋白膜分别是由蛋白质P24和P18所组成。(源自Gallo)9
病毒有五个基本形状:球形、圆柱形、长方形、子弹性和带尾形。病毒是由蛋白质的衣壳包裹,衣壳外常有一个外膜,由碳水化合物或脂类构成。正二十面体的衣壳是由122个壳粒组成,其中110个是六联体蛋白,12个是五联体蛋白。8 衣壳包裹着核酸和其他结构, 为的是保护基因(图2)。9 核酸可能是双链或单链的DNA或RNA。图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遗传物质是RNA,该病毒被称为逆转录病毒,需要借助被称为逆转录酶的复合酶将RNA逆转录为DNA。所有病毒的表面都有突出的蛋白质(称为抗原),可以让病毒与特定的宿主细胞受体结合。
一些更复杂的病毒还有附属结构,使其能附着在特定生物上。这些结构包括一根管状鞘、几个尾纤维和一个注射器(图3)。10、11这些看似简单的结构其实相当复杂,每个结构都含有成百上千的组件。致力于理解这些结构的研究,比如T-4病毒(一种细菌病毒,或称噬菌体)的形态发生学,直到二十一世纪仍然会处于分子生物学的前沿。12
病毒没有生命的特征,不会生长,缺乏细胞结构,而且只有几个标准样式,部件很少变化。它们缺乏生命所需的大部分酶和细胞器,所以必须利用宿主的细胞器。因此,病毒被称为专性细胞内寄生体,是“感染性颗粒”而不是生物。完整的传染性单位被称为毒粒,毒粒中的酶(如整合酶)不多,这些酶通常与它们进入宿主的细胞的机制有关。病毒通常只在特定的宿主中繁殖,而且通常只感染宿主的一个特定的器官(如肝脏)。一个病毒类型的所有成员,除了外膜上的糖蛋白抗原之外,通常在各方面几乎是完全相同的。13糖蛋白是信号蛋白,能触发宿主的免疫反应。
人们一旦认识到病毒其实是基因的携带者后,下一步就是研究病毒如何将基因带到其他细胞,以及如何将基因拼接到这些细胞的DNA上。另一个研究重点是病毒基因组中令病毒可以的扮演它们的角色的DNA信息。随着对病毒作用的深入理解,研究人员开始试图利用病毒来造福人类。这就产生了遗传学革命,包括DNA重组技术和基因治疗。
病毒复制
病毒是已知最小的传染性病原体,其大小范围是从200纳米(牛痘病毒)至20纳米(细小病毒)。相比于动物细胞,病毒非常微小——普通的人类细胞可以放入整整5000万个脊髓灰质炎病毒。14典型的细菌直径是1微米,而噬菌体大小是四十分之一微米长。病毒和宿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通常是从病毒接触潜在的宿主细胞开始的。所有已知的生命形式都可以被病毒感染,但有些生命形式似乎比其他更容易受感染,例如,一些节肢动物和裸子植物容易成为病毒宿主。15
病毒繁殖有六个基本步骤:

图3. 噬菌体注入装置是一个复杂的辅助结构,使病毒与宿主细胞结合。a)病毒附着于宿主细胞是鞘是伸开的。b)鞘收缩将噬菌体的DNA注入宿主细胞(按照Luria等人的图画).64
吸附:病毒和所有的动物细胞表面都含有突出的结构,通常是糖蛋白,可以让病毒和动物细胞结合,若兼容,则可以进行化学和机械结合。病毒的蛋白衣壳(或者脂质包膜)必须附着在宿主细胞的外膜上。病毒的表面抗原与宿主细胞的受体位点必须匹配,才能感染这个细胞。如果配合得不精确,病毒就不能附着并进入细胞。这种配合通常有种属特异性,因此特定的病毒类型只会感染特定的动物或植物类型。然而,有些病毒,比如狂犬病和流感病毒,其宿主范围比较广泛。
穿入:附着之后,大多数病毒可以被细胞膜‘向内包入’,由此进入细胞。这个过程称为细胞内吞作用,与细胞摄入营养的过程是一样的。不过有一些病毒类型可以直接穿过宿主细胞膜上的细孔。还有其他一些病毒如噬菌体,可以在细胞外部将DNA注入细胞(图3)。
整合:病毒DNA被整合酶拼接到宿主DNA的一个特定位点。酶首先切割环形的病毒DNA,然后将它拼接到宿主的DNA上,并修复两个拼接位点(参见图5)。
复制和合成:病毒DNA或RNA指导宿主细胞合成病毒的核酸和蛋白质,包括酶。
组装:病毒一旦进入细胞,就可以建立像流水生产线那样的生物合成机器(图4)16。在一种噬菌体中,尾部组装首先需要构建蛋白质脚手架。然后蛋白质组件一个一个地安装。另一种蛋白质起到“卷尺”的测量作用,判断尾部是否达到适当长度。若达到了,它会发出信号,表示尾部安装已经完成,于是尾部和脚手架蛋白分离,脚手架蛋白则被用于安装另一个病毒的尾部。疱疹病毒和某些病毒会自带蛋白质工具包。而大多数其他病毒,如烟草花叶病毒,几乎完全依赖于宿主细胞的蛋白质工具包完成其合成和复制。
释放:新病毒从原宿主细胞中释放并感染其他细胞,将其基因向更多的细胞传播。17
逆转录病毒在利用逆转录酶将其RNA逆转录为DNA之前,并不能破坏细胞。逆转录之后,宿主可以将病毒DNA整合进自己的DNA,然后每当细胞复制时病毒也随之复制。在这种状态下的病毒DNA被称为前病毒。

图4. 通过在连接点切开和拼接,噬菌体DNA插入细菌基因组。PP’ 和BB’分别是噬菌体和细菌的连接点。BP’ 和PB’是混合连接点 (按Luria 等人的图画)65
所有病毒的起源
一些进化论者假设病毒是细菌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它们成为寄生生物,它们失去了细菌生活所需要的所有复杂的蛋白质结构。还有一些人假设病毒是最早的生命形式,而细菌是从它们进化而来的(所有其他生命也是从病毒进化而来的)。这一理论的致命问题是,病毒不是生命,它们要繁殖和制造ATP(能量)就需要依赖细胞内的复杂细胞器。而其他一些科学家推测发生了一个共生逆转过程,病毒发源于细胞的组分,如细菌质粒和其他细胞器,并最终演变成特别的生命形式18。
迄今为止这些理论都缺乏支持证据。细菌质粒和病毒的DNA都含有启动复制所需的核苷酸序列。这种结构对于两者的功能都是必要的,但与两者的源流无关。此外,迄今为止在“古代”琥珀中和其他地方发现的“古老”病毒及其他地方所发现的“古老”病毒,都是功能完善、发展成熟的病毒。
病毒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病毒与细菌的重要性密切相关。马古利斯(Margulis)指出,微生物长期以来被认为“大都是一些会导致疾病的小东西。”19与这个大家熟知的形象相反,细菌是我们生态系统的基础。它们供给我们的肥沃的土壤和大气中的气体。它们净化水源,稳定大气中氮的浓度,调节土壤的酸碱性,使我们的世界生生不息。20
现在对病毒最新的认识是,从病毒和基因的正常关系来看,它们不是宿主和入侵者的关系;病毒更像传播花粉的蜜蜂,促进了基因的交流。病毒不仅携带自己的基因,也携带其他生物的基因,特别是细菌的基因。21虽然细菌之间可以通过几种方式传递遗传信息,比如通过菌毛传输(见下文),但目前认为病毒在基因传播上是极其重要的。22

图5. 噬菌体的复制周期(按Stent 和 Calendar绘制)16
噬菌体之所以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细菌内部有一个恒常、稳定的遗传系统(大复制子),但细菌若要在生态系统中发挥功能,就需要吸收和交换各种可变化的遗传系统(几种小复制子,包括质粒、病毒等)。小复制子是与细菌的主要DNA(称为基因带)分开的。基因带中可以插入新DNA,插入序列通常与基因带同步复制,但有一些小复制子能够自动启动自我复制(图5)。
马修(Mathieu)和索内雅(Sonea)声称病毒将所有的细菌转化成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的“超级生物体”,而且病毒“拥有一个创造和交换遗传物质的卓越机制。”23 在被交换的基因中,有一大类就是抗药基因(参见图6),另外还有一些使细菌能降解毒素(如多氯联苯)的基因,或将汞转化低毒性形式的基因。24这一机制有助于细菌抵抗其他生物产生的抗生素,让细菌能够生存,并维持至关重要的生态平衡。
前噬菌体、噬菌体和其他病毒是小复制子的一个重要类型。而且,“在自然界中尚未发现没有这样的临时性附加基因的细菌。”25 一些细菌复制子,特别是对细菌没有用的,最终会消失。这个过程曾经被称为“治愈”,因为人们一度把这些复制子看作对细菌有害的传染性因子。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病毒的作用很重要,它们使细菌更加多样化。因此病毒对细菌至关重要,而细菌对生态至关重要。26
要产生这种多样性,每个小复制子可能会访问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菌株;尽管每一个细菌细胞通常只能同时携带几个不同的小的复制子,但是一个菌种能接纳的小复制子类型可达数十种甚至数百种。”27
细菌可以通过几个复杂而精妙的机制进行活跃的基因交换,这是造物主的设计。其中一种机制,是温和噬菌体将其DNA注入细菌,称为转导。28 实验室研究发现噬菌体可以在一个地方吸入细菌DNA,通过转导将它向远处播散。米勒指出:
“……当一个携带新基因的细菌进入某一个栖息地,噬菌体就会感染这个细胞,在它里面制造出更多的噬菌体颗粒。如果有的噬菌体颗粒把新基因包括进去了,它就会把这个新基因传递给当地的菌群。不论染色体DNA还是质粒DNA,都可以通过这一机制转导。我们在不同的湖泊中分离出细菌和噬菌体,显示在这些环境中细菌都会通过转导而分享遗传信息。许多微生物学家最初认为转导不是自然界中的细菌间进行基因交换的一个重要方式,因为它需要病毒和细菌共同作用,而人们认为这两者在自然界存在的浓度都很低。但是……其实噬菌体的浓度是非常高的,每毫升淡水和海水中通常都含有1000亿个病毒颗粒。这些观察数据使人们重新评估细菌和病毒的相互作用的频率,包括噬菌体在宿主细菌之间进行基因转导的频率。”29
质粒或前噬菌体DNA整合于宿主细菌染色体DNA的过程称为转染。如果只是病毒载体的基因或游离DNA被吸入细胞,则称为转化。转染和转化并不是随机进行的,而是被严格控制的过程。细胞表面的特异性受体决定了哪些基因或基因包可以进入细胞。
尽管基因从一个细菌转移到另一个细菌的方式有多种,但是转化的发生率很低。在几乎所有的原核生物中,一般是以有传染性的前噬菌体、温和噬菌体或噬菌体的形式进行。”30
质粒很少整合到细菌的染色体中,而是像“移动性图书馆”一样,被传递到需要的地方使用,无用的时候就被丢弃(图6)。并不是所有病毒都是为了传递基因,很多病毒在自然界中的功能,我们可能一无所知。人们对某些病毒在生命体中有广泛作用的认识导致了生物学的革命。按照之前的研究经验我们现在尚不了解的细菌和病毒很可能在自然界中有重要的作用。
病毒作为基因载体(以及其他功能)的有力证据是病毒相对简单的结构,与之相比,细胞极其复杂并且有精妙的防御系统。细胞有复杂的防御系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这是必要的,以防止被外来基因控制。这是进化理论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如斯宛嫩(Syvanen)所说,“如果病毒只会带来痛苦和灾难的话,细胞应该会全力进化出对病毒的抵抗能力。但实际情况是,细胞虽然表现出某些方式的抵抗,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似乎相当容忍。”31

图6. 噬菌体组装程序(Stent 和 Calendar提供)16
致病性病毒
根据传统认识,人们将病毒视为外来入侵者,为争夺细胞内的生产资料而与人类进行生死搏斗。现在发现,这种传统认识如果不算错误,也至少是过于简单了。杀死宿主于病毒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可能导致病毒的死亡。
病毒必须有众多的储存宿主,在宿主物种中永久居住,不然会很快灭绝。比如说,艾滋病感染一些灵长类动物却不会导致疾病或死亡,可能已经在这些宿主中共生了许多世代。宿主生物体肯定能和它们融洽相处——事实上,某些病毒种类与宿主建立了和谐的共生关系。
显然,人类的不当性行为使得慢病毒从猴子传染到人。若HIV慢病毒只生存在猴子身上,它就不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在猿类中的艾滋病毒(称为猴免疫缺陷病毒)似乎在大多数天然宿主中并不引起生病,而且今天的致病细菌和病毒以前可能并不是这样的。32梅毒(似乎是从羊传染给人的)和许多其他传染病的情况也是一样。狒狒能够抵抗艾滋病毒感染,多年来研究人员让某些动物与这些病毒接触,发现它们不会被感染。
这一事实支持病毒通常不会、也不应该引起疾病的论点。只有出了差错,如基因突变或偶尔出现的非正当基因流通,这些病毒才会引发问题。查尔斯•斯泰尔斯博士(Dr. Charles Stiles)在许多年前就总结道:‘细菌被创造的时候,并非像今天这样,但它们后来演变成致病细菌……这些致病细菌最初被创造时,是以某种非致病菌的形式存在。’33斯泰尔斯声称,致病菌的出现是世界从被造以来不断退化的结果。
不断累积的证据显示,大多数或所有有害病毒和细菌都是非致病微生物的变异形式。致病菌的出现是由于基因重组,无意中破坏了正常的共生关系。白喉杆菌原本无害,但“因为前噬菌体或质粒带来的毒素基因而成为致病菌” 34,这可能不是唯一的案例。霍乱弧菌(致命的霍乱病原体)也显示了这一点。
“霍乱弧菌有许多菌株,其中一株是导致几乎所有死亡和痛苦的根源。这一菌株被称为O1,它产生的毒素会与小肠细胞结合,引发一连串的生理反应,使细胞排出大量的氯离子和水,有些时候水量达到一天5加仑。如果盐和水得不到迅速的补充,病人就会死亡。
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的霍乱弧菌菌株都是无害的,它们在河流和大海中生存和繁殖。而在霍乱弧菌的演化历史上的某个阶段,O1菌株变成了致命生物。是什么导致了这场要命的转化?据微生物学家马修·瓦尔多(Mathew Waldor)说,是病毒。他和哈佛大学的同事约翰·美卡拉诺斯(John Mekalanos)在研究编码霍乱毒素的CTX基因时,发现了这种病毒。他们怀疑是病毒感染了细菌,带进了这个基因,病毒经常将自己的遗传物质插入到细菌DNA中。”35
后来,研究人员证实,O1霍乱弧菌变为致病菌株的原因的确是病毒。虽然噬菌体和其他病毒相似,但它们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有的研究人员将只有寄生功能的病毒定义为真正的病毒,而噬菌体按定义则不是真正的病毒,因为一些噬菌体不杀死细菌细胞,只是将它们的DNA拼接到细菌染色体上(参见图5)。“噬菌体”这个名词可能是创造出来以降低‘病毒’一词的负面含义。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传染性的致病病毒也可以携带有利的基因,有的甚至有助于真核生物的演化。关于致病机理起源的研究是很复杂的,要讲清楚这个“曾经是无害的霍乱细菌是如何得到毒素基因而成为致命杀手的”真实故事,“需要对复杂分子的工作方式及其影响进行多年的深入研究,……CTX基因的发现只是在过去的几个月对微生物之间和微生物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而引起疾病的研究中的一连串的惊喜之一。对疯牛病(牛海绵状脑病)、艾滋病和疟疾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关于疾病演变的问题上,正面临很大的困难。”36
细菌被首次发现的时候,人们难以想象它们竟然在生态系统上起到了如此重要和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对细菌的重要作用已经非常清楚,而病毒显然也是如此。37此外,病毒在自然界各种环境中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在过去十年中科学界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海洋生物学家发现海洋生物群主要是由微小的生物组成,主要包括病毒、细菌、藻类和原虫。
“一茶匙的海水中可能包含超过十亿个病毒——是之前估量的1万到1000万倍。实验室科学家说世界海洋是一个巨大的培养基--人类现在所知的最大培养皿。仅仅一种生物就可能在每盎司的海水中形成数百万个体,它们在地球的碳循环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地球是否会经历全球变暖的灾难,可能要由我们所不了解的微小生物决定的。如海洋科学比奇洛(Bigelow)实验室的鲍勃·吉亚尔(Bob Guillard)所发现的:‘虽然海洋科学发展了一百年,但无人从中认识到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 ’”38
人类平常生活的环境中居住着数万亿微生物,其种类多达30万。每克土壤中估计含有高达1万个不同种类的细菌和病毒。39许多海生和陆生动物的生活环境中也充斥着亿万病毒,但是这些动物很少被感染。40、41 在人体中,如果把人自身的细胞和共生生物的细胞加起来,估计90%的细胞是微生物。42 微生物无处不在,在我们体内,在我们周围。
大量的证据表明,病毒的存在并非疾病的主要原因。这些证据来自人们对动物的研究,它们的生长环境中含有大量病毒和细菌。一个已经被深入研究的例子就是鲨鱼。梅斯特(Mestel)说:“在海洋中,很少看见野生鲨鱼生病,虽然海洋中充满细菌和病毒……。”43尽管鲨鱼的免疫系统相当简单,缺乏“T细胞”(一种存在于人类和动物免疫系统中的细胞),对移植器官的排斥反映相当迟钝。
鲨鱼缺乏人类拥有的复杂的抗体反应。如果将外源蛋白质注入一条鲨鱼的体内,它会产生抗体,与外来抗原结合,但与人类不同的是,免疫反应不会因重复注射外来蛋白而增强。因此,鲨鱼没有免疫记忆。
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疾病是由于“某些东西出错”而产生的,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事实感到意外。从几个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对“一系列‘新兴’疾病(即最近才在人群中出现的疾病)的研究都提示这一点。该领域也许比其他领域更谜团重重。标准的理论认为,当微生物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时(如艾滋病毒的情况),它的危害性比会对原来的宿主更大。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艾伯特认为,在新的宿主身上,寄生生物的传染性、适合度和致病能力常常减弱。当然,也有例外,而艾伯特认为我们常常只看到例外。事实上,细菌、病毒和其他寄生生物可能经常从一个物种转移到另一个物种,其频率可能比人们所知道的要高,但并不造成危害。”44
莫尔斯(Morse)还说:“一般地认为,新病毒突然跳出来,因为它是刚刚从头进化出来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新’的病毒根本不是新的,而是病毒转移过程带来的……新转移到人类的疾病,其实之前已经存在于一些动物种群中。”45
他还补充说,“新” 病毒,如艾滋病毒等,可能只是反映了我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不足,而不是病毒进化上全新的趋势。46他认为基本的问题是生物错配——生物从一个宿主转移到它不该去的地方。用莫尔斯的话说,是人类‘破坏了生态秩序,无意中鼓励了“生物杂草”(病毒)物种的适应性,病毒往往让新宿主发烧和痛苦。’47
这个对病毒发病机制起源的新理解是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引起创造论者的浓厚兴趣,因为这一新的证据符合神创论的世界观。毫无疑问,世界的堕落使得病毒和宿主之间曾经的共生互利关系发生了问题。病毒对某些生命形式,如细菌的生存,可能至关重要。
致病性病毒只是所有病毒类型的“冰山一角”,科学家越多地了解生物世界,就越意识到病毒在生命界发挥着重要作用。48只有少数微生物是致病性的,这一事实支持有害病毒起源于突变的理论。另一重证据是,大多数毒株通常不致病,只有一株或几株会带来问题。再者,致病病毒通常并不直接杀死宿主,而是间接危害宿主。例如,一种汉坦病毒会在宿主体内触发剧烈的免疫反应,后者会危害健康的细胞。
大多数致病病毒只是制造麻烦,而并不构成威胁。带尾的噬菌体,只有1%是致病的。就目前所知,几乎在每一例感染中都致死的病毒只有狂犬病毒(对未受保护的人)和艾滋病毒。49这一小部分病原微生物的起源是目前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
病毒在医疗上的应用
噬菌体(字面意思是细菌吞噬者)可能有助于控制细菌生长和传播。几乎所有已知的细菌都有特定的噬菌体捕食。研究表明,某些动物体内的一些噬菌体病毒可以抵抗细菌感染。拉德斯基(Radetsky)总结了使用病毒来治疗疾病的优点以及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他指出,过去没有多少人“……愿意拿感染性病毒胡闹,特别是在吃几片青霉素药就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西方科学家将噬菌体疗法束之高阁。到了今天,噬菌体疗法会很快回来了。在大概使用抗生素治疗细菌疾病50年之后,抗生素治疗的黄金时代逐渐结束了……越来越多的微生物产生耐受抗生素的能力。科学家又开始寻找治疗细菌疾病的特效方法了。一些科学家开始回顾过去,重拾几乎被遗忘的细菌捕食者。事实上,噬菌体疗法从未真正消失。[一些]……医生和卫生工作者常规性地使用噬菌体疗法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50
病毒治疗的明显优势包括:
‘……即使抗药性细菌没有成为不断增大的威胁,噬菌体疗法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抗生素有一定的风险。它们不仅仅杀死特定的目标,也会杀死很多其他细菌,因而它们不仅除掉体内有害的微生物,也除掉了有用的微生物,例如帮助消化的细菌。为了保证抗生素有效,病人必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严格地反复使用抗生素。若停药,你会发现自己受到疾病的再次攻击,而这一次攻击的是耐药细菌。抗生素也有可能导致肠道疾病和酵母菌感染。不仅如此,还有些人对抗生素严重过敏。在这种情况下,过敏反应可能比疾病本身更可怕。噬菌体疗法不会出现以上种种问题。噬菌体不会引发过敏反应,并且是出了名的挑剔——它们只攻击自己要寻找的目标。如果你少吃了一个剂量的噬菌体,问题不大,因为它们会在所攻击的细菌内繁殖,并在体内存留数日,然后才被清除。51
虽然噬菌体疗法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但这项技术让人充满了期待。已经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如治疗痢疾、伤寒、食品/血液中毒,以及皮肤/咽喉/尿路感染:“如果有人患了肠道疾病,可以喝噬菌体……如果是皮肤感染,噬菌体可以涂抹于患处。我们也已经开发出气溶胶和噬菌体片剂。”52噬菌体通常只结合到一种特定细菌的表面,这一特性可以让人们用噬菌体区分不同的菌株(该过程称为细菌分型)。
一种潜在的疗法是使用病毒来杀死病毒。病毒可以被做成生物武器,用来侦查被艾滋病毒感染的细胞。包被着特殊蛋白质的良性病毒可以侦查感染艾滋病毒的细胞,然后贴在细胞表面。正常情况下,艾滋病病毒外膜上的分子与宿主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当艾滋病毒的分子与受体连接后,病毒就可以进入细胞。艾滋病毒使用的主要受体是CD4,这个受体存在于免疫系统的血细胞,它是艾滋病毒的主要目标。艾滋病毒也需要使用免疫系统细胞上的至少一两个其他受体。其中之一是CCR5受体,艾滋病毒早期感染巨噬细胞时会使用这个受体。另一个受体是CXCR4,艾滋病毒随后感染T细胞时会使用这个受体。
研究人员运用这些知识改造一种无害的病毒,为它包裹上艾滋病毒借以入侵细胞的受体蛋白分子。人们在实验室内让被改造的无害病毒(猎人病毒)接触被艾滋病毒感染的细胞。表面装有CD4和CCR5的猎人病毒成功地锁定了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巨噬细胞。表面装有CD4和受体CXCR4的猎人病毒成功找到并锁定了感染艾滋病毒的T细胞。在这两种情况下,猎人病毒忽略了没有感染艾滋病毒的正常细胞。“这种技术提供了一种在体内向感染了艾滋病毒的细胞注入抗病毒基因的方法……”53
病毒和基因革命
受病毒感染的动物细胞可以表达多种蛋白质的成千上万个拷贝,但最多只能同时为六种病毒生产足够的病毒蛋白。另一方面,如果病毒蛋白基因通过DNA重组方式拼接到一种细菌的DNA,这种细菌将可以主要地生产这些病毒蛋白,使分离和研究这些蛋白变得很容易,这就大大简化了遗传学研究的过程。使用病毒进行研究的另一个优点是,一个特定毒株的几乎所有个体都是相同的。
现在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者都意识到,病毒对于医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是多么关键。齐默尔曼(Zimmerman)和齐默尔曼(Zimmerman ,1993)指出,现代分子生物学“是病毒时代”,“在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中没有比这更重要的。54在分子生物学中很多关键的工具(酶),都是在病毒中发现或因病毒而存在,包括:逆转录酶、细菌制造的用来控制病毒的限制性内切酶、以及许多其他的酶。这些研究极大地帮助了病毒学家对病毒和宿主之间的关系以及致病机理等领域中的探索。
病毒的基因载体功能可能很快会在治疗遗传疾病上扮演关键角色。现在已知超过5000个疾病是由于遗传缺陷而造成的,包括亨廷顿氏舞蹈病、镰状细胞贫血症、囊性纤维化病等。目前基因疗法的目的(曾首先试用于治疗囊性纤维化),就是将健康基因装入病毒载体,然后让病毒感染病人相关的组织,把病毒所携带的新基因整合到病人细胞内的DNA。“用病毒来运输基因是一个最理想的方法,因为它们在自然界本来就是要感染细胞并将其遗传物质注入。”55
最常见的病毒载体是Moloney小鼠白血病病毒,到目前为止,大约四分之三的基因治疗使用的是这种病毒。通过添加cre重组酶基因来修改病毒,能有效地使病毒“在完成基因配送任务之后就自杀。”56具体地讲,cre重组酶把病毒DNA切除,只留下治疗性基因。这降低了病毒导致问题的可能性,或病毒基因被拼接到错误地方的风险。
病毒仍然是基因治疗取得重大突破的源泉。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一种病毒,“……喜欢独自活动……(这)解决了科学家们需要将外源基因植入老鼠体内的一个棘手问题……这项技术可以大大加速和简化新基因的分析。十多年前当生物学家发现可以把新的DNA直接注入正在发育的老鼠胚胎中,基因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这种技术有一个大缺点,当数百万个基因拷贝被注射到胚胎中时,不知怎么的,这些基因在拼接到老鼠染色体上之前,往往倾向于连接起来,形成一长串。57
病毒就可能解决这个外源基因聚合的问题,因为通常一次只有一个病毒侵入染色体,这似乎是由于蛋白质会结合在病毒DNA的末端,像盖上帽子一样,防止病毒基因链接在一起。
病毒疗法对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包括老年痴呆症和帕金森症)、许多遗传疾病和几种脑肿瘤特别有发展前途。治疗脑部疾病的主要困难是,许多物质根本不能穿过血脑屏障,而某些病毒可以携带着新基因通过血脑屏障,使病人恢复健康。目前有100多个不同的临床试验研究正在进行中,测试这个前景极好的疗法。58 慢病毒载体似乎有特别好的发展前途。改造后的疱疹病毒株已被成功用于治疗老鼠脑部肿瘤。这个特殊的研究使用一种会在肿瘤细胞内增殖的病毒,该病毒产生一种酶,将无毒的药物转化为只破坏肿瘤细胞的化合物。59
免疫系统
脊椎动物的免疫系统通常是一个强大的防御体系,可以抵御几乎所有致病病毒。机体出现疾病,其问题往往是由基因突变、不良的饮食习惯、卫生状况差、接触新的病原体(或大量的病原体,免疫系统超出负荷)、情绪压力、睡眠不足和缺乏锻炼等因素导致免疫系统减弱。一些病毒有能力改变它们的抗原结构,使人体的免疫防御系统将其视作一个新的、陌生的外来生者。
病毒通常不会通过演化或变异来征服宿主的免疫系统,但正如莫尔斯指出的,产生新病毒株的关键事件“并非基因突变,而是将现有的基因成功地重组。”60这些基因有许多可能是从动物病毒转移来的。因此其致病性可能并非出于设计,而是出于意外。此后,宿主必须开发一个全新的免疫反应来对付新病毒。这个开发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疾病的急性期至少持续2 - 3天,直到身体的免疫防御系统可以开发出足够的反应细胞以摧毁入侵者。流感病毒、感冒(鼻病毒感染)病毒和艾滋病病毒比大多数其他病毒更善于使用基因重组的方法来产生新的病毒。

图7. 显示一个细菌细胞携带着一个多重耐药质粒。包括氨苄青霉素抗性基因、四环素抗性基因和氯霉素抗性基因,分别以Ampr、Tetr和Cmr代表。
这种重组,通常被错误地称作“变异”,其实是一个允许病毒生存的设计。在普通情况下,某些基因制造表面蛋白,使宿主的免疫系统将病毒视作外来物质。然而,如果病毒由于基因重组而产生了新的抗原蛋白,该病毒就不会立即被免疫系统识别,从而减缓了免疫反应。这种基因重组偶尔也可能将基因拼接在基因组中错误的位点上,产生上述的致病性细菌或病毒。
除了这些程序化的基因重组产生的变化外,我们没有病毒进化的确凿证据。所有现存的证据表明,古代病毒与今天发现的病毒是相同的。61
脊椎动物机体的防御系统不仅仅包括免疫系统,皮肤也能够分泌核糖核酸酶,从而能够剪断RNA病毒的RNA。皮肤还能分泌蛙皮素,可以杀死病原体。这个复杂的防御系统几乎完全有效,因此,我们周遭数以万亿计的病毒很少导致健康问题。
小结
病毒学是一个比较新的学术领域。许多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现在对病毒的理解,就如同在20世纪初对细菌认识那样肤浅。目前已知病毒有数种有益的功能,研究表明病毒可能还有另外几个重要功能。根据现有模型,疾病并非由于病毒本身,而是由于病毒与宿主的关系被破坏了。成千上万的病毒类型存在于宿主的细胞内,但不会产生问题。疾病的产生是由于病毒的基因重组,宿主的基因突变,或宿主生物体的健康状况受到破坏。研究显示,病毒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组分。福尔摩斯(Holmes)所指出的:
“单按数量来说,没有其他海洋生物可以与病毒相比。每一滴海水中可能有成千上万,有时甚至上百万的这类分子寄生物,其数量远超过细菌的十倍……证据显示,病毒是海洋中的强大力量,决定着海洋生态系统可以支持多少浮游生物,最终决定支持多少鱼,甚至多少人……病毒一定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产生深远的影响。若细菌被原虫吃掉,能量便沿着食物链传递,从原虫传递到浮游动物,再传递到更大的掠食者,包括鱼。但若细菌被病毒感染而破裂,其细胞内富含能量的物质便流入海水中,进而被其他细菌摄入。富尔曼(Fuhrman)说,‘病毒倾向于让营养远离大的生物,而在小东西中循环。’如果是这样,病毒就塑造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62
鸣谢
在此感谢伯特•汤普森(Bert Thompson)和约翰·伍德莫拉普(John Woodmorappe)的建议和宝贵反馈。
参考文献
- Woodmorappe, J., Noah’s Ark: A Feasibility Study, ICR, Santee, CA, 1996.
- Young, W., Fallacies of Creationism, Detselig Enterprises, Calgary, Alberta, 1985.
- Zimmerman, B. and Zimmerman, D., Why Nothing Can Travel Faster than Light, Contemporary Books, Inc., Chicago, IL, 1993.
- Hsiung, G.D., Diagnostic Virology, Third Edition, Yale Univ. Press, New Haven, CT, 1982.
- Curtis, H., The Viruses, The Natural History Press, Garden City, NY, 1966.
- Stanley, B., Animal Viruses, Vol. 3 Academic Press, Inc., New York, 1959.
- Valentine, R.C. and Pereira, H.G., Antigens and structure of the adenovirus, J. Mol. Biol. 13(43):13–20, 1965.
- Jensen, M., Wright, D. and Robinson, R., Microbiology for the Health Sciences,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J, 1996.
- Gallo, R.C., The AIDS Virus, Scientific American 256(1):37–48, 1987.
- Starr, C., Biolog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Wadsworth Pub. Co., Belmont, CA, p. 292, 1996.
- Simon, L.D. and Anderson, T.F., The infec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by T2 and T4 bacteriophages as seen in the electron microscope, I. II. Virology 32(158):279–305, 1967.
- Coombs, D. and Ariska, F., T-4 Tai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p. 28, 1994.
- Brooks, S., The World of Viruses, A.S. Barnes, London, 1973.
- Talaro, K. and Talaro, T., Foundations in Microbiology, Wm C. Brown, Dubuque, IA, p. 132, 1993.
- Evans, A.S., Viral Infections of Humans, Third Edition, Plenum Publishing Corp, New York, 1989.
- Stent, G.S., and Claendar, R., Molecular Genetics: an Introductory Narrative, W.H. Freeman 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p. 319, 1978.
- Starr, C., ref. 8, p. 294.
- Hapgood, G., Viruses Emerge as a New Key for Unlocking Life’s Mysteries, Smithsonian 18(8):126, 1987.
- Margulis, L., Foreword to Sonea and Panisset, p. vii, 1983.
- Margulis, ref. 16.
- Karam, J.D. (editor), Molecular Biology of Bacteriophage T-4 ASM Press, Washington, D.C., 1994.
- Sonea, S. and Panisset, M., A New Bacteriology, Jones and Bartlett, Boston, MA, 1983.
- Mathieu, L. and Sonea, S., A Powerful Bacteria World,Endeavor 13(3):115, 1995.
- Miller, R., Molecular Biology of Bacteriophage T-4, ASM Press, Washington D.C., 1998.
- Mathieu, ref. 20, p. 112.
- Hecht, J., Rare Bug Dominates the Oceans, New Scientist 144(1952):21, 1994.
- Sonea and Panisett, ref. 19, p. 36.
- Mathieu and Sonea, ref. 20, p. 114.
- Miller, ref. 21, p. 71.
- Sonea and Panisett, ref. 19, p. 42.
- Hapgood, ref. 15, p. 126.
- Brown, P., How the parasite learnt to Kill, New Scientist 152(2056):32–36, 1996.
- Quoted in The San Antonio Express 1 April 1923.
- Mathieu and Sonea, ref. 20, p. 112.
- Glausiusz, J., How Cholera Became a Killer, Discovery 17(10):28, 1996.
- Brown, ref. 29, p. 32.
- Mathieu and Sonea, ref. 20.
- Wiley, J., Phenomena, Comment and Notes, Smithsonian 21(4):29, 1990.
- Tiedje, J.M., Microbial Diversity: Of Value to Whom?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News 60(10):524, 1994.
- Homes, B., Who Rules the Waves? New Scientist 152(2054):2 supp, 1996.
- Mestel, R., Sharks’ Healing Powers, Natural History 105(9):40–48, 1996.
- Creager, J., Black, J. and Davison, V., Microbiolog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p. 2, 1990.
- Mestel, ref. 38, p. 41.
- Brown, ref. 29, pp. 35–36.
- Creager, ref. 39, p. 16.
- Creager, ref. 39, pp. 16–18.
- Creager, ref. 39, p. 18.
- Zimmerman and Zimmerman, ref. 3.
- Curtis, ref. 5, p. 14.
- Radetsky, P. The Good Virus, Discover 17(11):52, 1996.
- Radetsky, ref. 47, pp. 54–55.
- Radetsky, ref. 47, p. 56.
- Enders, M. et al., Targeting of HIV-and SIV-Infected Cells by CD4-Chemokine Receptor Pseudotypes, Science 278:1462–1463, 1997.
- Zimmerman and Zimmerman, ref.3, p. 274.
- Hotz, R., Researchers Alter Viruses to Combat Brain Disorders, The Journal Gazette, pp.2, 20 November 1996.
- Coghlan, A., This Message Will Self-Destruct … , New Scientist 151(2042):20, 1996.
- Cohen, P., Lone Virus Speeds the Gene Shuttle, New Scientist 151(2044):23, 1996.
- Hotz, ref. 52, p. 1.
- Hotz, ref. 52, p. 2.
- Morse, S., Stirring up Trouble; Environmental Disruption Can Divert Animal Viruses into People, Science 30(5):20, 1990.
-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see Herrmann, B. and Hummel, S., Ancient DNA, Springer, New York, NY, 1994.
- Holmes, B., Who Rules the Waves? New Scientist 152(2054):8–9, supp, 1996.
- Luria, S.E., Darnell Jr., J. E., Baltimore, D. and Campbell, A., General Virology, John Wiley and Sons, New York, NY. p. 36, 1978.
- Luria, ref. 63, p. 159.
- Luria, ref. 63, p. 228.

照片由大卫·斯文瑟提供
复印件上附着一张手写的字条,上面写着:“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个关于地质方面的问题?”这位自称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正面临一些困惑。他刚刚接触到一些与圣经中直白记述的地球历史相冲突的地质学说——这些学说以“地质证据”为由,否认创造事件发生在不久的过去,否认全球大洪水。
在过去的25年中,许多著作挑起了所谓的“地质问题”,瓦解了很多人对圣经笃信不移的信念。令人痛心的是,引发最大困扰和疑惑的著作正是出自所谓的“相信圣经的人”。1,2,3,4
一位基督教家庭教育协会的教材编辑来信说,他读了这些书以后“不知所措”。5他问我们“能不能回应这些作者的言论。”我们肯定可以回应!另一位接触了其中一些书的读者来信说:“我可能……忽略了质疑新近创造模型(译注:创造发生于最近几千年前)的证据。”
他提到的“新近创造理论模型”其实就是圣经直接平白的记述,可见他已经开始质疑圣经了。
毫无防备的读者拿着这类书,以为正在看“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著作,期望从中获得鼓励,得到造就。在一串混杂着异端神学和伪劣科学的对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强烈抨击面前,这类读者往往不堪一击。
比如说,作家阿兰·海沃德(Alan Hayward)自称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他却持守神只有一个位格,即不相信上帝的三位一体。新约明确教导了基督的神性[约翰福音1:1-14,5:18;提多书2:13,更多详细内容可参见问答页面“耶稣基督真是神吗?”(Is Jesus Christ really God?) 和“一位神真有三个位格吗?”(Is one God really three persons?)],但海沃德却否认这点。6海沃德自称“相信圣经”,却明显刻意曲解新约中他所不认同的内容。
他也这样对待旧约。他不接受创世记清楚明显的教导,而是要将他所认可的数十亿年的地球年龄理论框架读入经文。7
他这样做,当然会给信徒造成混乱,摇动他们的信心。圣经告诫我们要对曲解圣经明晰记述的假教师保持警惕。(歌罗西书2:8)
照片由Y. Robertson提供

表面看来,海沃德似乎汇聚了一批可观的论据,证明为何圣经的意思不能按照字面直解。但是其实他的书中唯一值得我们吸收的就是策略。他用来攻击神的话的每一个论据,无论是地质学、天文学、世俗历史学或神学,都是对某种“权威”抬举,超过了圣经的地位。这个手段可以一直追溯至伊甸园。
圣经是一切真智慧的开端(箴言1:7,,诗篇119:160,138:2),也应该成为我们的起点。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是在场的。祂知道这一切,从不撒谎,也不会犯错。我们从圣经中得知,这个世界是“年轻”的(见“这个世界看上去有多老?”The earth: how old does it look?)。
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已存在亿万年,8我们就应该如此相信。然而亿万年死亡和痛苦的观念与神的话语相悖,而且有损于基督福音的根基。
很多人难以认同科学调查应该以圣经为前提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带着“开放的思想”面对证据,地球年龄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其实,没有人的思想是开放的。证据不会自我解释。相反,每个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基于固有的思想框架。遗憾的是,我们人类永远无法接触到所有的信息。因此,由证据着手,我们无从确定结论是否正确,这有点类似悬疑小说的情节,仅从一条信息难以看到全局。但是与此相反,如果我们从神的话语出发,我们就可以肯定其中的记载都是真实的。
即便我们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肯定一定会有答案。在永恒的这一端,我们可能找不到答案,但是这仅仅是因为我们一时拿不到推断出正确结论所需要的全部信息。但另一方面,继续研究有可能找到答案——而且实际往往如此,下文也将提及。
乍眼一看,海沃德提到的证据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他提到的问题很容易解答——其中很多已经在他著书前就被解答了。他要么是不知道答案,要么是故意无视。我们来看看他所提到的非常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吧。
纹泥
照片由史蒂夫·奥斯汀提供

图为潜水员考察圣海伦火山脚下斯皮尔特湖中的一根断裂的树干,树干直插湖底。这个树干本来属于漂浮的“树干毯”,从这里可以看出它是树根朝下下沉的。
一个常用于反驳圣经的论据就是纹泥——由颜色较暗的细腻沉积层和较亮的粗糙沉积层交替叠加形成的岩石构造。人们认为一年中的规律变化造成了纹泥的特征,亮色层形成于夏天,暗色层形成于冬天。人们在一些岩系中发现了成百上千层的纹泥,认为这足以“证明”地球要比圣经说的古老得多。9但是认为每一层都需要一年才能形成的假设本身是错误的。从最近的灾难中,我们得知这类带状的岩石可以在短时间内沉积而成。华盛顿州的圣海伦火山爆发时,一个下午就产生了厚达8米的平整沉积层!10而且,海滩上还在短时间迅速沉积了厚达一米的砂浆层,覆盖面积相当一个足球场。
照片由Don Batten提供

层次分明的沉积层在海滩上迅速形成。
人们在实验室里研究沉积作用发现水流中挟带的不同大小的物质会侧向沉积,从而自动地形成层次分明的带状层。12令人吃惊的是,每一层的厚度都取决于对应沉积物的大小,而不是水流的状态。13一块岩石(硅藻岩)被分解,重新悬浮在流动液体中时,会再一次形成同样的岩层。14
人们对美国迈阿密绿河的纹泥层做了很多文章。9这些岩层不可能是一年形成一层,因为其中有跨越多层的保存完好的鱼和鸟。
这些动物遗体跨越多层,说明它们是在灾难中被快速掩埋的。常有人说,这些鱼和鸟的遗体能在湖底完好保存是因为湖底的水呈强碱性,有利于保存。9实际上,强碱性的水会促进有机物的分解,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在洗碗机中放碱粉![编者注:有些怀疑人士声称碱只会“分解油脂”,这是完全不懂基础化学,即碱会催化聚合物的水解过程,这与保存鱼的过程恰好相反。]纹泥年度解释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地质构造各处的岩层数目不一致;如果是一年一层,各处的层数应该是一样的。16
蒸发岩
德克萨斯州有几个大规模沉积构造,其中有多层碳酸钙和硫酸钙条带,这也被用于支持漫长的时间。17一种解释称,这些岩层是海水在阳光下蒸发后形成的,因此被称为“蒸发岩”。以这种方式形成如此庞大的沉积构造,自然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沉积层中化学物质的纯度极高,显示它们不是在干燥、多尘的气候下经千百万年的时间而成的。相反,它们更可能是在海底火山爆发时,在冷水和热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迅速形成的——热液沉积物。18
化石太多?
质疑圣经的人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化石太多’。19如果这些动物都复活的话,它们会以0.5米(1.5英尺)的厚度覆盖整个地球。所以这些化石肯定不可能是大洪水时期仅仅由一代生物被掩埋而形成的。20
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一如继往地迎刃而解。化石的数量其实是依据非正常现象进行计算的——如南非干旱台地构造。在这一构造中,这些化石形成了“化石墓区”——动物遗体全部汇聚在当地的一个“沉积盆地”。21根据这个异常高的种群数量来计算全球的种群数量,当然是不合理的。这个计算使用的关于今天动物种群密度的资料也不正确,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大洪水之前的境况可能有所不同。22
煤太多?
另一个反对圣经纪年的论据认为,大洪水之前的世界没有足够的植被以形成当今看到的这么多煤。23这个论点与其它论点一样,是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之上。大洪水前,地表水量尚未增加,陆地面积肯定要大许多。同时,气候很可能也更有利于植物的生长。24不仅如此,人们发现,很多煤炭都形成于漂浮在水面上的森林(见320k JPG drawing of the floating forest.),25所以仅仅根据陆地面积估算植被数据是错误的。最后,人们是根据“煤只能由腐烂在沼泽地里的植被形成”这一错误观点,推算形成这些煤所需要的植被的数量。大洪水中植被可以被立即填埋,这样所形成的煤炭要比沼泽地中形成的煤炭数量大几百倍。22
森林化石
照片由Lowell Baker提供

图:黄石公园中立着的树干化石。有证据证表明这些树并非在此处长成的。
黄石国家公园的石化森林往往被人们视为反对圣经纪年的论据。26人们曾经认为这些树原生于此,被填埋、石化,之后有新生树木在其上生长成林,这一过程至少循环了50次。显然,根据这种解释,要形成这许多层化石森林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圣经的时间表有冲突。但是这一解释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这些树干和树墩都在底部断裂,没有根系。还有,不同层次的树木有着一样的年轮模式,说明它们生长于同一个时期。27
与其说有50层相继生长的森林,地质学的证据更倾向于支持以下解释:这些树生长于另一个地方,在一次次灾难性的火山泥石流中被拔起并冲刷到这里——这与1980年圣海伦火山爆发时的情景类似,当时,人们也看到了随水漂流、根部向下沉于水底的树。28
沥青
人们也曾以沥青为例,讽刺圣经里关于挪亚的记载。29他们告诉我们,沥青是原油的残渣,而创造论者称原油是在大洪水时期形成的。那么,挪亚去哪儿找的用来密封方舟的沥青呢(创世记6:14)?这个古老的论据源于人们不了解沥青的形成。人们对石油的使用直到20世纪才普及,但是在没有石油的古代,人们用什么来密封船只呢?古时候,人们用松脂做沥青。30由于需求巨大,沥青的制造也曾经蓬勃发展过。
挪亚的泥浴
有些人称圣经的描述过于荒唐,在为期一年的大洪水中不可能形成世界上众多的沉积岩。他们称,若果真如此,方舟则是浮在泥汤上,不可能有鱼能生存下来。31这个论据完全无视水挟带沉积物的方式,无知地认为在持续一整年的洪水阶段中,所有沉积物都均匀地混合在水中,好像花园里完全搅混了的鱼池一般。沉积作用并不是如此发生的。相反,流动的水体会将沉积物搬运到盆地,一旦沉积,沉积物就脱离了水流系统。12随着大洪水期间的地壳运动,这些水体在陆地上不断地流动,将一批又一批的沉积物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
更多(之前的)问题,更多答案
有些类似的地质问题曾经被认为是信徒“无法回答”的,但现在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了:

- 珊瑚礁需要亿万年才能生长。32[其实,人们以为的“珊瑚礁”不过是很厚的碳酸盐台地,大部分大概是大洪水时期沉积而成的。33珊瑚礁只是表面薄薄的一层。还有一些情况,“珊瑚礁”不是该处原生的,而是由水运过来的。34]
- 白垩矿床需要亿万年的时间。35[白垩矿床不是持续稳定形成的,而是呈阶段性产生的。在洪灾的影响下,球石藻会爆发性地生长,并在短时间内形成大量白垩层。36]
- 花岗岩也需要亿万年的时间冷却。37[但是有循环水的冷却效果下则不需如此38]
- 变形岩需要亿万年的时间形成。39[在有大量的水时,变形岩可以很快形成,如此庞大的水量刚好是洪灾可以提供的。40]
- 覆盖变形岩的沉积层厚达数公里,侵蚀时间需要亿万年。41[只有按照今天的侵蚀速率才是如此。在洪水期间,水流速度大,水量大,侵蚀数公里厚的沉积物不成问题。]
结论
以上的部分列出了曾经在这一领域中被视为“不可解答”的一些问题。如果这篇文章写于几年前,我们也没有以上所有问题的答案。目前我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答案,而是人们还没有找到答案。当然以后还会有人从其他的角度“证明”圣经或以上列出的某个回答是错误的。但这些被解答了后,又会冒出新的。这就是科学的本性。所有的结论都是尝试性的,新的发现意味着陈旧的观点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何创造论研究如此重要。但是科学无法最终证实或证伪圣经。信心——但并非盲目的信心——是需要的。反对圣经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解释。因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必须从神坚定的话语出发,才能明白周遭世界的运作原理。
引文与注释
- Hayward, Alan,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Facts and Fallacies, Triangle, London, 1985.
- Wonderly, D.E., God’s Time-Records in Ancient Sediments, Crystal Press, Michigan, 1977.
- Morton, G.R., Foundation, Fall and Flood, DMD Publishing, Dallas, 1995.
- Ross, H.N., The Genesis Question, NavPress, Colorado Springs, 1998 (见评述).
- John Holzmann, Sonlight Curriculum, letter and catalogue on file.
- 在致创造论者David C.C. Watson的信中承认了这点—见海沃德著作的书评,载于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22(4):198–199, 1986.
- Hayward, 注释1, pp. 167 ff., ‘重解’圣经,称上帝不是在六日之内完成创造之工,不过是在六日宣布了创造的命令。但是祂的命令用了数十亿年实现。这个观点不仅与圣经相悖,也与进化地质学相悖。这个观点没有解决问题,不过增加了混乱。
- 如果真是漫长岁月,希伯来作者可以很容易地表达,见Grigg R., How long were the days of Genesis 1? Creation 19(1):23–25, 1996.
- Hayward, 注释1, pp. 87–88.
- Ham, K., I got excited at Mount St Helens! Creation 15(3):14–19, 1993.
- Batten, D., Sandy stripes: Do many layers mean many years? Creation 19(1):39–40, 1997.
- Julien, P., Lan, Y., and Berthault, G., Experiments on stratification of heterogeneous sand mixtures, Journal of Creation 8(1):37–50, 1994.
- Snelling, A.A., Nature finally catches up, Journal of Creation 11(2):125–6, 1997.
- Berthault, G., Experiments on lamination of sediments, Journal of Creation 3:25–29, 1988.
- Hayward, 注释1, p. 215.
- Garner, P., Green River Blues, Creation 19(3):18–19, 1997.
- Hayward, 注释1, pp. 89–91.
- Williams, E., Origin of bedded salt deposits,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26(1):15–16, 1989.
- Hayward, 注释1, pp. 125–126.
- 创造论者认同有些化石是在洪水之前形成的,这些比较少,但对论点没有影响。
- Froede, C., The Karroo and other fossil graveyards,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32(4), pp. 199–201, 1996.
- Woodmorappe, J., The antediluvian biosphere and its capability of supplying the entire fossil record,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Robert Walsh (ed.),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p. 205–218; The The Karoo vertebrate non-problem: 800 billion fossils or not? CEN Tech. J. 14(2):47–49, 2000.
- Hayward, Ref. 1, pp. 126–128.
- 人们已经反复观察到高层大气的CO2 可以让植被更繁茂。
- Wieland, C., Forests that grew on water, Creation 18(1):20–24, 1996. 同见 Scheven J., The Carboniferous floating forest—An extinct pre-Flood ecosystem, Journal of Creation 10(1):70–81, 1996, 和 Schönknecht, G., and Scherer, S., Too much coal for a young earth? Journal of Creation 11(3):278–282, 1997. 有一位“年老地球论”作者竟然去掉问好引用了这篇文章,暗指,这篇文章其实向年轻地球论者提出了问题,但其实这是一个解答! 见Ross,注释4,p. 152–153, 220 (注释17和21).
- Hayward, 注释1, pp. 128–130.
- Morris, J., The Young Earth. Master Books, Colorado Springs, pp. 112–117, 1994,
- Sarfati, J., The Yellowstone petrified forests, Creation 21(2):18–21, 1999.
- Hayward, 注释1, p. 185; Ross, Ref. 4, pp. 153–4.
- Walker, T., The pitch for Noah’s Ark, Creation 7(1):20, 1984. 同见: ‘Naval stores’, The New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8:564–565, 15th Ed., Chicago, 1992.
- Hayward, 注释1, p. 122.
- Hayward, 注释1, p. 84–87.
- Oard, M.J. The paradox of Pacific guyots and a possible solution for the thick ‘reefal’ limestone on Eniwetok Island, Journal of Creation 13(1):1–2, 1999.
- Roth, A.A., Fossil reefs and time, Origins 22(2):86–104, 1995.
- Hayward, 注释1, p. 91–92.
- Snelling, A.A., Can Flood geology explain thick chalk beds? Journal of Creation 8(1):11–15, 1994.
- Hayward, Ref. 1, p. 93.
- Snelling, A.A.. and Woodmorappe, J., Granites—they didn’t need millions of years of cooling, Creation 21(1):42–44, 1998.
- Hayward, 注释1, p. 91–92.
- Snelling, A.A., Towards a creationist explanation of regional metamorphism, Journal of Creation 8(1):51–57, 1994. Also: Wise, K., How fast do rocks form?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Robert Walsh (ed.),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pp. 197–204, 1986.
- Hayward, 注释1, pp. 91–92.
本章驳斥那些基于错误的解经方法和错误情感的、认为地球有数十亿年历史的论证。圣经里所有表示“年代久远”的词,都可以解释成几千年,因为几千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事实上,《创世记》第一章里没有出现表示年代久远的词,这进一步支持6000年的时间尺度。与罗斯的说法相反,创造论者从来没有害怕“如果有几十亿年的时间,进化论就成了可能”。
虽然我们常被称为“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但这不是我们关注的要点。这是接受圣经权威性的一个结果,即接受以下几个明显的教导:
- 《创世记》的一天,是24小时。
- 整个宇宙是在一周的时间里受造的,跟我们所认知的工作周一样长。
- 人类是在“创造之初”的第六日被造。
- 圣经家谱的记载显示亚当是大约6000年前受造。据此,宇宙也应该有大约6000年的年龄。
罗斯的立足点是颠倒的。他以大爆炸理论为出发点,把数十亿年当作事实。他大部分的信念都以此为依据;例如他认为,创造日是很长一段时间,亚当是在数十亿年之后才被造的,大洪水只淹没了局部地区等等。他的其他教导,如原始人没有灵魂,所以不是人,物种是不变的,也是因为他首先接受了数十亿年的历史。鉴此,这一章没有必要再解释为什么说年轻地球是圣经的启示;但还是需要看一看罗斯是如何辩解的,说他相信数十亿年也是符合圣经的。本章也会谈到罗斯的一些其他论点。
数十亿年更能展示神的永恒性?
罗斯在《创造与时间》一书(Creation and Time,以下简称C&T)第52页宣称:“(从圣经中智慧书的教导看来)短暂的地球历史似乎不够用来展示神的永恒性。圣经用地球的古老来展示神的永恒,这提示圣经认为地球是非常古老的。”为了让罗斯这种说法有意义,他必须先承认永恒是一个无限的时间。然而,与无限相比,任何一段有限的时间会比另一段更有说明性吗?即使是十亿年的时间,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不管怎样,就如奥古斯丁指出(罗斯也接受),上帝不是在时间里创造了宇宙,而是在创造宇宙的同时,也创造了时间。就是说,时间本身是被造的(对创造时间的主而言,在未来事件还没有发生之前,就预测未来,一点都不是问题)。这意味着永恒不是无限长的时间,而是一个无时间的状态。因此,当我们对永恒有正确的理解时,罗斯的论说就显得语无伦次了。
归根结底,“非常古老”到底是什么意义?我相信地球是古老的,非常的古老,它已经有几千年了——六千多年了。(所以,即使我接受罗斯的论点,在一个6000年老的宇宙里,地球的年纪也足以显示神的永恒性)
这样的想法可能会令很多人感到惊奇,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已经被进化论洗脑,认为“古老”意味着数十亿年,而感觉几千年只不过是“地质学里的一瞬间”。其实“古老”和“年轻”是相对而言(比如问“长”,一根线要多长才算长?)。我现在看50岁以上就是老了,但一个80岁以上的人,可能觉得一个50岁的人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对很多地质变化而言,即使几年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来到澳大利亚西部的游客,看到“石化的水车”非常稀奇:“只用了60年的时间,就把这东西完全包在了岩石里面?”溶有石灰的水不断地滴在一样东西上,使石灰沉淀包围其上,达60年之久,这实际上是难以置信的一段长时间。
这显明,所有远超过人类平均寿命的事物都可以被描述为“古老”或“久远”。所以几千年的地球可以被认为是“古老”的,而且确实是难以想象的一段长时间。3000年前,大卫作以色列王的时候,西方国家还在遥远的千年之后的未来。而我们通常被称为“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因为“年轻”是相对于进化论者所号称“上亿年”而言。罗斯就是这亿年观的跟随者。其实我们是圣经创造论者!
在接下来篇幅里,我们分析罗斯的论点时,必须考虑到这些。罗斯挑出一些圣经章节,讲述地球或地球的某些特征为“古老”、“久远”等等,用来“证明”地球的远古或“反驳”地球的年轻。因此,我们必须用圣经作者的原意来解释这些章节,而不是把一些当代的思潮读进这些字句里。尤其,这些带有相对性含义的词,我们必须用其它有明确含义的章节来解释,比如有关创世的“天”和家谱里“年”。但是,罗斯把这些相对性的词字,按照现代的均变理论或进化论的观念来解释,曲解了那些含义明确的词的意思。
圣经中描绘 “古老” 的词
罗斯在《上帝的指纹》(Finger of God, 以下简称FoG)第151页引用了几段圣经来支持古老地球的观点:“在描述神存在的永恒时,圣经的作者们把它与诸山的年代或大地的根基做比。诗篇90:2-6,箴言8:22-31,传道书1:3-11和弥加书6:2,用比喻给我们描述了神的存在和神的计划之无法量度的古老。如果这些文学手法的使用是恰当的和准确的(这是当然的,因为是神的默示),那么地球及其根基的年龄必定超出相对短暂的人类历史好几个数量级。哈巴谷书3:6直接称山为永久的,岭为长存的,而彼得后书3:5说到天是太古就有的。”
这是罗斯能举出的最好的例子。我们已经指出,这些词的含义都是相对的,只要分析希伯来原文就可以知道。事实上,当我们按着罗斯使用的顺序来分析每一个例子,就会发现这些词是指,相对于人的寿命而言是古老;但它们指向数千年,而不能强解为数十亿年。
诗篇90:2-6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於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乾。”
这没有说明任何问题,因为“从亘古到永远”是指神,是在诸山生出之前。前面已经指出,用与神的永恒相比来证明诸山有上百万的年龄是谬误的。
箴言8:22-23(指拟人化的智慧)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
“太初”是 מאז(‘az 带介词 me),字面的意思是“那时”;有“这之前,早些时候”的含义,如撒母耳記下15:34,“...我向来作你父亲(大卫)的仆人,...”。 在这段上下文中用了同样的一个词,显然是指在过去历史中发生的一件事,并且是上千年前,而不是上亿年前。所以,这个论据实际上更支持年轻地球创造论的时间尺度。
其它黑体词也不证明什么,因为智慧是在创造之前就存在了,而且许多解经家认为这是指成肉身之前的基督,那永恒的道,或三一神格里的第二位格。支持罗斯的詹姆斯∙达布森(James Dobson)博士,“关注家庭协会”的发起人,在1991年四月的一次电台广播中,也同样肤浅地引用了英文翻译的“太初”。不过,达布森举的例子是诗篇102:25,那里说:“你太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
在这节经文里,希伯来原文是 לפנים (lephanim),也在其它经文出现过19次1。但每一次,lephanim 很清楚都是指在人类历史中发生的事——上千年,而不是上亿年。又一次,一个古老地球创造论的论据,反而支持年轻地球创造论的时间尺度。
1991年7月9日,罗素∙杭福瑞博士(Russel Humphreys)给达布森博士写了一封信,很客气地指出“太初”这个词在圣经里的上下文和它对世界年龄的含义,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传道书1:3–11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
“永远”原文是עולמ (‘ôlām) 或 עלמ (‘ōlām),基本的含义是“长久,持续的一段时间”(《旧约希伯来文和亚兰文词典》,以下简称HALOT)。连罗斯也不相信地球已经存在了无限久,或能无限地存在。上下文很清楚表明这相对于人的世代而言,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样“以前”原文是‘ôlām,在这里的上下文中,很清楚是指一个人所知道新事的时候,下文中对该词的含义还有进一步讨论。
弥加书6:2
“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
我看不出来这跟主题有任何关系。或许是打字错误,作者本意应该是引用弥加书5:2“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祂的根源从亘古【קדם, qedem】,从太初就有【עולמ‘ôlām ,词组“从太初就有”是 מימי עולמ , mîmê ‘ôlām】。”
在这个关乎祂的出生地的预言里,表示“年代久远”的词是用在耶稣身上的(参见马太福音2:6和约翰福音7:42预言的应验)。这些词跟地球有上亿年的历史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表达弥赛亚在永世里已经存在(约翰福音1:1-3,8:58)。这是“信仰的理由”(罗斯的机构)也接受的教义。Kiel和Delitzsch总结得很好:“... קדם 和 מימי עולמ 都是用来表示远久的古代;如在7:14和20 (「....古老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用于列祖的时代”。
“古老”的原文是 עד (‘ad),可以有多种含义。在这段经文里,HALOT把הררי עד
翻译为永久的山;与“古老”的含义略不同。“古老”是往回看,而这里更含有“无穷尽”的意思,所以不能作为已过历史年代久远的证据。
而且,圣经还有其它多处用到 עד 的例子,很清楚是指几千年而不是几十亿年前的事件。比如,约伯记20:4,עד 是译为亘古:“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希伯来文是‘亚当’】生在地?”
罗斯也承认,人类的起源是在几万年前,而不是几亿年前。再一次,“长存的”原文是ôlām。甚至在创世纪6:4(“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它也是用在人身上,表明它与几千年是相容的。
彼得后书2:3
“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
“太古”在希腊原文是 έκπαλαι (ekpalai)。它在圣经其它地方只出现过一次,即彼得后书2:3讲到假师傅,“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这里没有提到这刑罚存在多久了,所以不能用来证明几十亿年的时间。2
另外,ekpalai是字根palai (“古老”的意思)加上前缀ek(“自”或“从”)组成的。再一次,这是一个相对性的词;圣经有没有给出任何线索,“古老”有多老呢?Palai 在新约中出现过六次。一次是在犹大书1:4,如彼得后书2:3“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一样,是指假师傅。这里也没有给他们被定受刑罚是多久以前的数据。但另外的五次很清楚是指人类历史中发生的事件:
- 马太福音11:21 -“哥拉汛哪,你有祸了!伯赛大阿,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 马可福音15:44-指耶稣死后不久,“彼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
- 路加福音10:13-与马太福音11:21完全相同
- 希伯来书1:1-“神既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
- 彼得后书1:9-“....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为何《创世记》第一章没有用漫长年龄的词?
罗斯举出的圣经,表面上支持漫长年龄;但在另一个方面,却反击了他自己的论据。他无保留地坚持圣经其他地方使用了表示漫长年龄的词,并以此“证明”上亿年的时间;即使这些词有两可的意思。 但是,要是这样的话,为何神在《创世记》第一章没有用这些词来表达创造用了一段长久的时间呢?如果这是祂的本意的话。为何反而用编号的天,加上有晚上和有早晨呢?这样的用法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是指每天24小时。
诚然,罗斯在《创世记的问题》(The Genesis Question, 以下简称GQ)第65页的争辩,似乎忘了他自己对年老地球的“证明”。他说:“在圣经里用的古希伯来文(不是在摩西和大卫之后的希伯来文),除了yôm之外,没有别的词带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含义”;而且引用了他自己的书(C&T)和《旧约神学词录》(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 以下简称TWOT)。罗斯早期的书 C&T这样宣称(第47页):
“年轻地球论者也持这样的观点,即希伯来文中עולמ (‘ôlām,与 yôm相反)是用来表示一段长的时间。不过,希伯来文词典显示,只有在圣经以后的著作里‘ôlām 才表示一段长的时间。在旧约圣经的时代,它的含义是“永远”、“不休止”、“长存的”、“总是”、“古时”或“遥远的过去、未来、或两者”。它的范畴不包含一段确定的时间。”Van Bebber和Taylor (VB&T:76–77)指出,罗斯所引用的书(TWOT)又一次与他自己相矛盾。他们说明希伯来文的‘ôlām和与之对应的希腊文的 αιων (aiōn) (英文的eon就是从这衍生出来的)通常的含义是“长久的时间”。
TWOT 2:673 说明,这个词“....不只限制在将来”,还可以用来描述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极少,如果有的话,指一个无限的过去”,而且这个词本身没有“无穷尽”的意思。这“由两个事实可以显明:它有时是用于发生在过去一个确定的时间点的事件或状况;有时有必要重复该词,不只是说‘永远’,而要说‘永永远远’”。
BDB的词典也是这样解释的。它给的定义是“一段长时间,古代或未来”。HALOT也说明‘ôlām 的意思是“长时间,时间段”。它还加上,“常指永恒、永久,但不是哲理上的”(数学的无限长的一段时间)
在诗篇139:24,大卫求耶和华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 דרך עולמ derek ‘ôlām) ”。‘ôlām这个词是处于构建状态,常常是指过去的一个时候。诗篇139:1-1表明‘ôlām是指诗人一生中的早年,不是上亿年前。3
如果神想要表达很长的一段时间,祂可以有很多的词使用。4 例如:
- יומים (yāmîm, yôm的复数) 独用或带“晚上和早晨”,意思就是“那是有晚上和早晨的许多天”。这是教导创世是在过去,用了一段时间完成的最简单的方法。它表示许多天,有可能是一段漫长的时间。
- דר /דיור (dôr/dōr) 意思是“一代”或“一段时间”,可以很理想地用来表示一连串的时代,如果这真是神想要表达的。
- עד (‘ad) 是我们前面见过的词,意思是“古老”甚至“永远”,总是与介词一起使用。仿照伯20:4,如果祂有这样的意愿,神完全可以告诉亚当,太阳、星宿、动物等等是“亘古以来的”。
- קדם (qedem) or קדמה (qedmah) 有时被译为“亘古的”或“古老的”。
- נצח (netsach) 表示“总是”,“永存”或“永远”。
- תמיד (tamîd) 意思是”不断地”或“永远”。
- ארך (‘orek) 与 yôm 一起用时译为“许多日子”。
- עת (‘et) 意思是一般的“时间”,可以用来表示不明确的一段时间。
- מועד (mô‘ ēd) “时间”, 也用来表示“季节”
- זמנ (zemān) 表示一个“季节”或“时间”。
要教导上亿年的时间,神还可以用这样的词语:“无数无数年以前”。再不精确一点,神可以用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来比拟巨大的年数。然而神没用,反而强调字面上的几天。
神是一个巨匠,所以祂需要很长的时间吗?
当曲解圣经达不到目的时,罗斯便诉诸一个极其主观的论点(C&T:142): “观察技艺高超的雕塑家、画家、诗人,或任何的艺家,你会发现他们创作杰作时,会比其它一般作品多花更多的时间。从每一件杰作,可以看见融入了他们快乐的辛劳,艺术家还常常停下来欣赏、评估还未完成的作品。”
很很难相信罗斯是认真的。人类的艺术家花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是有限的;但是全能的造物主是无限的。理所当然,越有能力和技艺意味着需要越少的时间,所以有无穷能力和技艺的就不需要时间!如果我们意识到时间也是神创造的,这一点就更显而易见了。
值得注意的是,神迹的一个特点就是快;比如,一瞬间变水为酒。更进一步,若按照罗斯的“巨匠”类比,将来新天新地的受造也需要上亿年的时间,想必也会有无数的死亡和痛苦发生。无论如何,罗斯的前题设想都是错的。很多杰作是很快完成的;比如,亨德尔的《弥赛亚》就只用了三周的时间(1741年8月22号至9月14号)。
“对百万的恐惧”
罗斯宣称:“反对上亿年的主要动机,是害怕它使进化成为可能”,于是GQ:92有“对百万的恐惧”这样的标题。这样的宣称,显露他对创造论文献和前面讲的进化/变异的故意无知。在罗斯开始写书之前的很多年,像德恩∙格西博士(Duane Gish)等创造论先锋们,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他们相信根据圣经和科学,地球只有几千年的年龄。同时格西也有力地指出,即使有上亿年的时间,进化也不可能;如:所以,不管地球是一万年,一千万年,还是一百亿年,化石记录都不支持广义的进化论。”5
例如,一个含100个氨基酸的酶,这样简单的分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五十亿年的时间里出现。6
再者,创造论者已经多次证明生物遗传变异的过程是一个信息损失的过程;越长的时间对进化论更是不利,而不是有利。突变带来的基因复制误差的累积,自然选择带来的信息损失,都导致物种更趋向灭绝,而不是向上的进化。因此,如果我们的论述从逻辑上表明漫长的时间是进化论的阻碍,我们怎么还会害怕上亿年“有利于进化论”呢?
结论
罗斯的错误,在于他用来证明“古老”的词,实际上都是相对性的词。这些词代表的年老,只是以人类的历史为尺度,完全可以与几千年的年龄相容。如果解经方法正确,这些词都不能用来证明罗斯所说的“古老”,而必须按照圣经清晰的教导来解释,比如,《创世记》第一章,带有晚上和有早晨、并编号第几天,还有家谱,记载了年数。罗斯的做法与此相反—— 他决意把“年老地球科学”当作他的权威,并以此来解释年老的词。这对圣经的作者和读者而言,完全是外来的。
既然有这些表示古老久远的词,就说明如果神想要告诉我们在人类之前已有漫长的时间,祂确实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但讲到创世,祂没有用任何一个那样的词。祂反而特意注明,亚当是在一个“寻常”的创世周的第六天受造的。《创世记》第一章,完全没有出现表示古老久远的词。这是对“一日一时代论”的一种强有力的反驳。
罗斯其他的论点完全是主观的,或出自对创造论者写作动机的不公正解读。
参考文献
- 申命记2:10,12,20;约书亚记11:10,14:15,15:15;士师记1:10,11,23,3:2;路得记4:7;撒母耳上9:9;列代志上4:40,9:20;列代志下9:11;尼希米记13:15;约伯记17:6,42:11;耶利米书7:24.
- BDAG says: “ekpalai … 1. pert. to a point of time long before a current moment, long ago II-Pet. 3:5. 2. pert. to a relatively long interval of time since a point of time in the past, for a long time II-Pet. 2:3”.
- D. Graves, Psalm 139, paper for Old Testament,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2001, p. 19. He also believes that there is an aspect of eschatological fulfilment.
- R. Grigg, “How Long Were the Days in Genesis 1? What Did God Intend Us to Understand from the Words He Used?” Creation 19(1):23–25 (1996). J. Stambaugh, “The Days of Creation: A Semantic Approach”, J.Creation 5(1):70–76 (1991).
- D.T. Gish, Evolution: The Fossils Say No! 2nd edition (San Diego, CA: Creation-Life Publishers, 1973), p. 43. This book has been superseded by Evolution: The Fossils STILL Say NO!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5), but the 1973 book shows that Ross’s claim has no basis whatever.
- D.T. Gish, “The Origin of Life: Theories on the Origin of Biological Order”, ICR Impact 37:iii (1976).
美国宇航局(NASA)

许多进化论者们痴迷于一个概念:生命莫名地起源于另一个行星又通过外太空来到地球上。原因是:
- 他们无法解释地球生命的起源,众所周知,就连最简单的活细胞都有着难以想象的复杂性。
- 随着人们在化石记录中越来越深的岩层里(根据进化论的教条,也就是越来越古老的岩层里)发现生命的迹象,1许多人开始主张::地球上没有足够的时间让生命进化;因此需要一个更古老的行星。
当然,假设生命起源于另一颗行星,这也解决不了进化论者面对的问题:即无生命的化学物质怎么转变成一个活细胞——它只是将问题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已。
悬赏——一个类似地球的行星
生命需要的条件
美国宇航局(NASA)

根据我们对地球生命的知识,太空中最适宜生命存在的地方将是与地球各方面都相似的行星。2这包括:要有一颗与我们的太阳很相似的、异常稳定的恒星3,与之保持恰当的距离4,恰当的公转轨道5和自转速度6,以维持一个适宜的温度范围,达到一个不能太热、不能太冷、恰到好处的黄金标准。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存在液态水——在活细胞内,水提供了氨基酸和其他有机分子混合和反应所必须的液体介质。7
还需要一个无毒的大气层,8可以吸收或者反射足以致死的紫外线、x射线、伽马射线,还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磁场以折射太阳风(一股高能带电粒子流)。9复杂的生命形态还需要适当比例的氧气。地球刚好适合生命生存。10
火星
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火星曾经满足过生命存在的这些条件。然而,许多科学家已经不再接受这种观点了。比如,现在大多数科学家都反对1984年在南极发现的“火星陨石” 含有微生物化石的主张。11,12虽然有人声称火星上曾出现过灾难性的洪水,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火星是不是曾经像人们想的那样温暖湿润。
进化论的“虔诚信从者”所遭遇的最新挫折,是对(据信是)来自火星的陨石的分析,研究表明陨石内包含的硫同位素来自大气化学反应,而不是细菌。13令人更失望的是美国宇航局最近两次火星探测任务都以失败告终,而且损失了火星登陆飞行器。
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生命起源于火星。同样,在木星的一颗可能存在液态水的卫星——木卫二星上,生命所必需的其他条件却几乎没有。
寻找其他行星14
最近,研究者们发明了两项技术以寻找系外行星,也就是那些可能在我们太阳系之外环绕着其他恒星的行星,这给天体生物学(太空生物学——对外星生命的研究/搜索)打了一针强心剂。
技术
行星不会自己发光,而是反射它们环绕的恒星所发出的光。因为这种反射的光线太弱,也许只有主星亮度的十亿分之一,所以人们设计一种技术来间接“观察”这种行星。
一个行星围绕它的恒星公转时,二者会以一种大小一致、方向相反的引力互相牵引。当行星接近恒星时,质量大的恒星受行星的牵引,会向着行星稍微移动。从地球上观察,可能看到恒星发生周期的地摆动。15,16
另外一个技术是,当一个行星从恒星前方经过时,会轻微地但周期性地使恒星的黄白光晕变淡。在地球上的观察者需要置身于行星运行轨道的同一平面时才能观测到这个现象。
发现了什么?
研究者通过使用特殊软硬件侦测恒星摆动,并应用“摆动说明有行星” 的理论,声称已经发现了573个系外行星(编者注:截至2011年8月9日),包括首次发现的三行星系统(环绕着仙女座Upsilon,距离地球大约44光年)。17
在已经发现的系外行星中,没有一个能满足支持生命存在的任何条件,所以人们仍在继续寻找大小与地球相仿的行星(我们所知道的最适宜生命的行星体积)。由于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18倍,所以一个大小与地球相仿的行星,其引力只有木星的1/300(在同等的距离上),因此任何一个大小与地球类似的行星所造成的摆动也许太小,以至于靠着目前的设备无法侦测到。进一步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更多的问题
即便发现了一个能够支持生命的系外行星,也有几个主要问题会阻止携带生命物质的岩石到达地球,如:
1. 需要达到逃逸速度
一块石头(或者宇宙飞船)想要摆脱母星的引力,就必须达到逃逸速度。地球的逃逸速度是11.18千米/秒,即每小时40248公里(每小时25009英里)。火星的是5.02千米/秒,即每小时18072公里(每小时11229英里)。因为火山熔岩的喷射达不到以上的速度,科学家们猜测岩石是被巨大的小行星撞击溅出行星,进入太空的。
2. 距离的阻隔
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距离我们4.37光年,这意味着光——以每小时30万公里(186000英里)传播——耗时4.37年才能来到我们这里,总距离为40万亿公里。如果有一个大小与地球类似的行星(最适宜的体积)环绕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运行,它上面有一块岩石以地球的逃逸速度被抛出,它需要115000年才能到这里。18
即使一个大小跟地球相仿的行星距离我们不是太远,只有40光年(银河系直径的二千五百分之一),从那个行星出发的任何一块岩石都需要超过100万年才能达到地球。
 一系列时间推移图像显示木星表面受到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碎片的撞击。从这个巨大的气体行星被撞击后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开裂的冲击带,有些比地球还大。 |
3.其他问题
美国宇航局休斯顿约翰逊航天中心的的弗朗西斯·库欣克塔说:“DNA会在星际旅行中被辐射破坏。”19 其他的危险包括:太空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没有宇航服的保护)、太空中缺乏营养和氧气(没有宇宙飞船的补给)、进入地球大气层(没有隔热板,已证明细菌也会被烧灭20)、与地球撞击(没有降落伞)。
1994年7月16日至22日,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的20块碎片与木星发生灾难性碰撞,借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到这种碰撞的力度。(见图)
总而言之,星际旅行对生物体来说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圣经的观点
神在创造周的第四天创造了太阳系(创世记1:14-19),我们没有圣经上或道德上的理由认为他当时没有创造其他的行星。
至于在地球之外的行星上是否存在生命,则是另一回事了。圣经告诉我们,生命起源于地球上,是经上帝命定的创造过程(创世记 1:27)。圣经还告诉我们,神的目的集中在地球上。于是神在第一天创造了地球,然后在第四天才创造了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的“光体” (创世记11:4),也就是说这些是为了人类的益处。
男人和女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创世记 1:27)。这一点,再加上人的堕落、道成肉身、神通过耶稣基督的一次性受死和复活而拯救人类、基督还要再次回到地球、还有对全人类的最终审判等因素,表明了地球在亿万群星的宇宙中特有的重要性。这与进化论者常持的地球无足轻重的观点相反。
以上所述也意味着神没有在宇宙中其他地方创造其他生命形式。21
然而,如果有一天在火星、木卫二或者太阳系内其他地方上发现某种形式的微生物,这并不证明它是在那里进化(或是创造)出来的。这样的生命很可能来自地球,因为:
- 正如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提到的:如果岩石可以从火星崩到地球了,这个过程也有可能从地球到火星。22
- 相比星际旅行来说,细菌孢子可能在相对较短的旅行中存活。
- 在地球大气上层的孢子可能会被推入太空,然后被太阳风吹到另一个行星或卫星。
- 每当人工航天器到一个行星或卫星上登陆并采样,这些天体的表面就有被地球细菌污染的风险。
太空生命的热衷者喜欢说,“没有证据不是没有的证据”。或许如此,但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回答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关于宇宙中所有的所谓其他文明的著名问题:“那么,人都在哪里呢?” “寻找外星智慧计划”已经实施50 多年了,目前使用的设备能够每秒扫描2800万个无线电频率,但还未捕捉到一个来自外太空的“智慧”信号。
|
美国宇航局(NASA) 
我们从“海盗”号拍摄的这张图片可以看到火星表面的荒凉情景。研究者希望能在冰冷的火星尘土中找到生命的痕迹,但是一无所获。 为什么如此狂热于在其他星球上搜寻生命?
|
2000年4月,美国宇航局艾姆斯研究中心举行第一届太空生物科学会议,600名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聚集加州23,从生物学的角度对现有证据进行评估,讨论我们在宇宙中是否是独一无二的。悲观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英国古生物学家S. C. 摩利斯(Simon Conway Morris)一语道破: “我认为除了我们自己,再无生命。”美国宇航局帕萨迪纳喷气推进实验室负责火星项目的科学家丹·克里斯(Dan Cleese)也说,现在是 “降低期待”的时候了。24
结论
为了验证“天体生物学”而进行的狂热搜索已经获得了很多数据,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不过(如果有任何用处的话)进一步证实了《创世记》的记载,既生命是在地球上创造。尽管有进化论者的宣称,尽管有许多好莱坞大片(如《外星人》、《星球大战》、《独立日》等等)富有想像力的描述,外星人从太空造访地球的事情将永远停留在科学幻想的范畴。
编者注: 本文最初发表于2000年,“寻找其他行星”部分已经更新,2000年以后的相关文献已经包含在注释里。《外星人造访地球?》(下文)由萨法提(Jonathan Sarfati)博士慷慨提供。
外星人造访地球?面对严重的能源短缺和百万吨级尘埃炸弹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一些涉及其他星球上智能生命的电影已经成为最好的吸票机,比如《阿凡达》、《星球大战》、《星际迷航》电影和《独立日》。这些都是文化标志。但是正如我们多次指出,其他星球存在智慧生命的说法,是与《圣经》上的教导相矛盾的。25这种思维的前提是化学进化26,即生命是由无生命化学物质演变而来。正如下文即将说明的,星际旅行的想法有巨大的科学难题,包括能源的严重缺乏。 恒星之间的距离着实是天文数字。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是4.37光年之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也就是说,尽管光速高达300,000千米/秒(186,000公里),但阿尔法星的光需要4.37年才能到达我们这里。一光年将近10万亿公里(约6万亿英里)。此外,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告诉我们,当物体越接近光速时,其质量就变得越大,推动其加速就需要更多的能量。但先不论这些问题,早在遇到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假想的外星人需要首先解决其他难题。27 NASA 
假设外星人宇宙飞船的质量只有10吨或10,000公斤(只能运载两个人的阿波罗登月舱重约15吨)。那么,加速到100,000公里/秒(光速的三分之一)需要多少能量呢?根据普通经典物理学公式近似得出(无论需要多少时间逐渐达到这个速度)必需的总能量:
这相当于全世界超过一个月的能源消耗!28 有什么燃料可以产生如此庞大的输出?还需考虑燃料本身的质量,起飞时燃料要随着飞船一起加速。 反物质是唯一有可能实现的解决办法,因为根据爱因斯坦著名的公式,E = mc²,它可以湮灭普通物质并完全转换为能量。假设完全地湮灭了(当然这是最不可能的)500公斤的反物质和物质会产生:1000 kg × (3 × 108 m/s)² = 90 艾焦。这看起来似乎够了,但这还远着呢!外星飞船到达地球时还需要大约等量的能量才能使飞船减速,而此时燃料已经耗尽了。并且这只是一艘小飞船,电影里高速运行、精细操作的大型飞船需要多少能源……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幻想。值得注意的还有:我们还没有生产出反原子(也许已经造出了大约十万个反氢原子,这是一个超微数量)。29 沙粒变成炸弹
能源短缺不是外星人唯一需要担心的。他们也需要避免细小的沙粒,甚至一片脱落的涂料。我们自己的航天器,尽管速度只有10公里/秒(22,000英里/小时),也因碰撞而造成严重损坏——见图。这些假设的外星飞船的行驶速度比“挑战者”要快一万倍,所以撞击的能量会高一亿倍。在这样的速度下,甚至一片雪花所携带的动能也相当于4吨TNT,30这些能量必须释放在船体上,否则它将穿透一切结构。31 如果撞上一个1公斤的物体,碰撞所释放的全部能量就相当于一个百万吨级的氢弹。一群小陨石或一群小行星将是灾难性的。因此,飞船必须配备某种转向器,并耗费大量的能量回避撞击。 结论因为许多人相信生命是从其他行星上进化而来的,而且外星人可能比人类早几百万年,所以他们也相信外星人有时间开发那些如科幻小说描绘的难以置信的技术。然而,再多的先进技术也不可能否定或“消除”支配我们宇宙的物理定律。对于接近光速的旅行来说这都是必要考虑的问题,更不用说以更快的速度了。以上这些都是无法克服的难题。 正如《圣经》的“大概描述”所显示的25,没有外星人会从其他行星上来访问地球。以上的简单物理学表明这个想法是多么地荒谬:即使听起来保守的“亚光速”旅行所需的能量也超过全人类一个月的消耗,即使微小物体的撞击也像核爆炸。所以如果你喜欢科幻,尽管好好享受;但如果你要事实,请回到神的话语。 |
参考与注释:
- 比如,在西澳大利亚,琥珀中所发现的据说有2.3亿年之久的微生物化石,见 Creation 15(4):9, 1993, commenting on Science 259(5092):222–224, 1993.
- 即以DNA为基础的生命。这排除了那种“基于硅的生命”和“基于硫的生命”的理论幻想。
- 参见 Sarfati, J., The sun: our special star, Creation 22(1):27–30, 1999; creation.com/sun.
- 日地平均距离为1.5亿千米(9300万英里)。这个距离刚好保证了太阳到达地球的光能让地球的平均温度保持在零度到40摄氏度之间(华氏32度到100度),在这个狭窄的温度范围内才能维持(地球上的)生命。某些微生物能够在低于或者高于这个温度范围内生存,但是这些微生物是少有的特例。
-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日地轨道)是一个非常接近圆形的轨迹。如果日地轨道是一个扁长的椭圆形,那地球在这个椭圆形轨道的近日点时会变得非常热,而移动到远日点时会非常寒冷。
- 如果地球自转速度非常缓慢,那昼夜温差的变化差异会非常明显。但是如果自转速度非常快,那强大的自转离心力会将大气层抛入太空。
- 参见 Sarfati, J., The wonders of water, Creation 20(1):44–47, 1997; creation.com/water.
- 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含量过大时对生物是有害致命的。在地球上二氧化碳的含量为0.03%,而在火星则达到95%。
- 地球拥有恰到好处的大气密度和磁场来达成这些目标。
- 这一节参照以下文献改编: Gitt, W., Stars and their Purpose, Master Books, Arizona, pp. 141 ff., 1996.
- 参见 Sarfati, J., Life on Mars? Separating fact from fiction, Creation 19(1):18–20, December 1996; creation.com/life-on-mars; see also Sarfati, J., Life from Mars,J. Creation 10(3):293–296, 1996; Mars: The red planet, Creation 32(2):38–41, March 2010; creation.com/marsred; see also creation.com/mars.
- Creation 20(2):8, 1998; Nature 390(6659), 454–456, Dec. 4, 1997; Science 278(5344): 1706–7, Dec. 5, 1997.
- New Scientist 165(2228):21, March 4, 2000.
- 更多信息,参见 Spencer, W., Planets around other stars, Creation 33(1):45–47, 2011.
- 就地球上的观察者而言,恒星忽近忽远的位移使到这颗恒星上的光波波长一时蓝移,一时红移又一时蓝移。研究人员在恒星的光谱中寻找这些变化称之为多普勒频移。根据这些变化,他们计算出其行星轨道周期以及与该恒星的距离。
- 行星(质量)越大,其引力就越强。这种方法特别适合应用于寻找那些太阳系以外、跟我们(太阳系内)的大型气体行星体积相当或者更大的行星。
- Lissauer, J.J., Nature 398(6729):659–660, April 22, 1999.
- 这表明: 那些人类在空间探索其他恒星(和星际战争)的故事不过是科幻而已。Gitt, W., God and the extra-terrestrials, Creation 19(4):46–48, 1997. Also Bates, G., Did God create life on other planets? Creation 29(2):12–15, March 2007; creation.com/lifefromplanets.
- New Scientist 165(2221):19, January 15, 2000.
- Sarfati, J., Panspermia theory burned to a crisp:bacteria couldn’t survive on meteorite, creation.com/panspermia, 10 October 2008.
- 我们在这里并非讨论天使的生命或者魔鬼的生命。请注意: 罗马书8:22 讲到:“一切受造之物”都因亚当的叛逆而受到诅咒。彼得后书3:12,说到“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化”。还有在启示录6:4 暗示“在重新创造万物前,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沃纳.吉特(Werner Gitt)写道:“如果有另外一个的受造的种族,不是亚当(罪)的后代,他们为什么会一同受到诅咒的影响,然后又随基督(最后一个亚当)一起复活呢?所有这些(说法)是非常古怪的。”那些猜想耶稣在另外的星球(世界)为救赎其他外星文明而死的人,要注意:在地球上得救的人类被形容为永远做“基督的新妇”,基督是不可能有多个新妇的。
- 澳大利亚悉尼Radio 2GB广播电台1996年2月1日的访谈, reported in Creation 18(3):7, 1996.
- 结果就是“美国宇航局管理局的丹.戈尔丁(Dan Goldin)要求让探寻地外生命成为他这个部门的中心课题之一”, Nature 404(6779):700, April 13, 2000.
- Boyd, R., “Sorry, but we are alone”, The Courier-Mail, Brisbane, Australia, April 14, 2000, p. 10.
- 见 Bates, G., Did God create life on other planets? Otherwise why is the universe so big? Creation 29(2):12–15, 2007; creation.com/did-god-create-life-on other-planets; and his book Alien Intrusion: UFOs and the evolution connection, CBP, 2005.
- 见 Sarfati, J., By Design: Evidence for Nature’s Intelligent Designer—the God of the Bible, CBP, 2008 (available from addresses on p. 2); creation.com/origin.
- 质量增大的程度服从洛伦兹因子γ = 1/√(1-v²/c²),。这里的v是指物体和以太的相对速度,c是指光速。该因子在90%光速时为2倍,99%光速时为7倍,而99.9%时则是22倍,之后当v继续接近光速时,其值则趋于无限大。
- 维基百科(对于并无争论性的东西而言是个不错的信息库,但是对于保守的或者是基督教的话题而言则是不太可靠)报道: “在2008年,在全球范围的能源消耗到达474艾焦,其中80%-90%是来自矿物燃料。”
- 氢原子的质量和反氢原子的质量均为1.66 × 10−27 kg
- 一片雪花的质量为3毫克,所以其动能为1.5 × 1010 焦耳 (E = ½mv², is ½ × 3 × 10–6 kg × (108 m/s)² = 1.5 × 1010) 1克TNT(炸药)在爆炸时释放的能量大约为980-1100卡路里,但在这里按1000卡路里换算,为4.184千焦。所以1吨TNT炸药算作4.184 × 109焦耳,意味着其(撞击)力为3.6吨。
- E = ½mv², is ½ × 1 kg × (108 m/s)² = 5 × 1015 焦耳; 百万吨的TNT释放的能量为 4.184 × 1015 焦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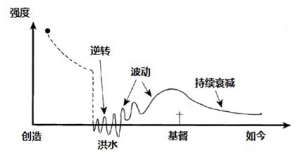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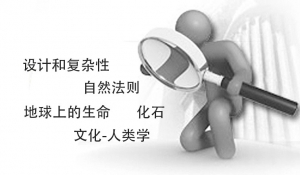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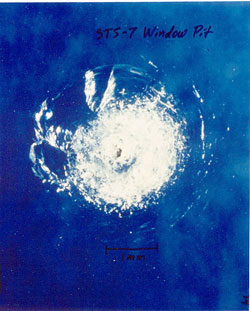 一片脱落的涂料在“挑战者”飞船STS-7前方视窗上造成的破坏,损伤像火山口。
一片脱落的涂料在“挑战者”飞船STS-7前方视窗上造成的破坏,损伤像火山口。